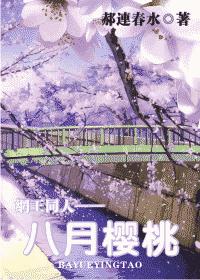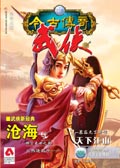八月炮火-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天星期一是公假日,天气晴朗,是个和丽的夏日。上半天,大批度假人群并没有去海滨,而是被危机所吸引,蜂拥到首都伦敦。中午时分,白厅门前人群拥塞,车辆难以通行;熙攘之声,内阁会议室内清晰可闻。室内几乎连续不断地在开会,大臣们正在力图拿定主意,决定是否要为比利时问题开战。
陆军部那边,霍尔丹已经发出动员的电令,召集后备役士兵和本土军。11时,内阁得到消息,比利时已经决定将其六个师投入战斗,抗击德意志帝国。半小时后,他们又收到保守党领袖们在获悉德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之前所拟就的一份声明。声明指出,对法国和俄国的援助如果犹豫不决,就会“使联合王国的信誉和安全化为泡影”。俄国成为盟国,对大多数自由党大臣来说已是难于接受。现在又有约翰·西蒙爵士和比彻姆勋爵两位大臣辞职,不过比利时的事态则决定了中枢人物劳合…乔治的留守。
8月3日下午3时,格雷预定要就这次危机向议会宣布政府的首次正式公开声明。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在引领以待。格雷的使命是要使国家投入战争,而且要朝野一致,举国团结。他必须得到向以和平主义为其传统的本党的支持。他必须向世界上历史最久而又最讲实际的议会说明,为什么英国并非由于承担义务而要援助法国。他必须说明比利时是缘由而又不隐瞒法国才是根本缘由;他必须唤起英国的荣誉感,同时又要直言不讳地指出英国的利益才是决定性因素;他必须面对的场所乃是一个就外交问题进行辩论的传统已发扬了三百年之久的场所,而他既无伯克的才气又无皮特的威力,既无坎宁的练达又无巴麦尊自信的勇气,既无格莱斯顿的辩才又无迪斯累里的机敏,可却必须证明在他掌管下的英国外交政策是正确的,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他必须使同代人心悦诚服,必须无愧于前人,同时又必须为后人所理解。
他没有时间准备讲稿。临到最后一小时,正当构思几个要点的时候,有人通报德国大使来访。利希诺夫斯基焦虑不安地走了进来,打听内阁决定如何,格雷将对议会说些什么。是宣战吗?格雷回答说,不是宣战,而是“说明条件”。利希诺夫斯基问道:“比利时的中立是否条件之一?”他“恳请”格雷不要将此提作条件。他对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毫不知情,但他并不认为计划之中要“严重”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虽然德国军队有可能越过比利时领土的一个小角。利希诺夫斯基这时用了人在无可奈何时常说的一句话,他说:“既已如此,那也无可挽回了。”
他们是站在门口谈的,各自心急如焚,格雷急于离开,争取最后几分钟的清静,准备一下他的演说,利希诺夫斯基则是竭力想要推迟公布这一挑战的时间。他们终于分手,从此再也没有作过官方会晤。
下院开会时,议员无一缺席。自从1893年格莱斯顿提出国内管理法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为了容纳全体议员,过道上安排了加座。外交使团席上除德、奥大使缺席留有两个空位外,座无虚席。上院客人挤满了旁听席,长期主张义务兵役制而不见采用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也在其中。会场一片紧张的沉寂,没有人走动,没有人传递纸条,也没有人在座位上俯身探头窃窃私语。可是就在此刻,突然卡嗒声响,议院牧师从议长身边后退的时候在通道上加座的椅子上绊了一脚。全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内阁大臣席上,阿斯奎斯温文尔雅的脸上毫无表情,劳合…乔治蓬头散发,面无血色,象是突然老了几年。他们两人之间,坐着一身轻便夏装的格雷。
显得“苍白憔悴、心力衰竭”的格雷,此时站立起来。他虽任下院议员已经二十九年,跻身大臣席上也已八载之久,可大体说来,他指导外交政策的方针,议员知之甚少,而国人则是知之更少。这位外交大臣,不论向他提出什么问题,都很难使他落入圈套,作出明确或肯定的回答。若是换了一个冒冒失失的政治家,这种闪烁其词的作风是会引起责难的,可是对他,却无人疑忌相视。他毫无世界主义倾向,而是坚守英国本色;他乡土气息如此之浓,一言一行又如此谨慎,因而无人认为他会惹是生非,卷入其他国家的纷争之中。他对外交业务并不爱好,对于自己的职务也无乐趣可言,只是无可奈何地把它作为应尽之责而已。逢到周末,他从不跑到彼岸大陆度假,而是隐身本国乡村。他的法语仅及学童水平,除此之外,他不会任何外语。他五十二岁,是个鳏夫,无子无女,不好交际,人常有之的情欲爱好,在他也象对他所任公职一样,感到索然无味。他的性情,厚墙四堵,如果还有什么爱好能够突破这堵围墙使他动心,那就是鳟鱼戏游的溪流,还有百鸟的啾鸣。
格雷讲得从容不迫,但却富有感情,他要求下院能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荣誉和英国的责任”出发来看待这次危机。他叙述了与法国军事“会谈”的经过,说明没有任何“秘密协定”束缚议院或限制英国决定其行动方针的自由。他说,法国卷入战争是出于它对俄国所负“荣誉上的义务”,但是“我们不是法俄联盟的成员;我们甚至对于这一联盟的条款也不清楚”。为了说明英国并未承担义务,他似乎有些过于推托其词。一个保守党人,德比勋爵,不禁愤愤然对他邻座低声说道:“天哪,他们要抛弃比利时啦!”
格雷接着透露了与法国的海军安排。他告诉下院,根据与英国的协议,法国舰队都集结在地中海,以致法国北海岸和西海岸“毫无防御”。他说他“感到”,“如果德国舰队开进海峡,轰击法国未加防御的海岸地区,我们不能视若无睹,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不采取任何行动!”反对党议席上爆发出一阵喝彩声,而自由党议员则是听着,“垂头丧气,不吱一声,默然认可”。
为了说明他何以会使英国早就承担了保卫法国沿海峡地区的义务,格雷谈起了“英国的利益”和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通道。这是个复杂的论题,好比一团乱麻,于是他匆匆掠过,转到比利时中立的问题,“一个更为严重,并且每时每刻愈趋严重而必须考虑的问题”。
为了充分阐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格雷颇为明智,他不是凭借自己的辩才,而是借助格莱斯顿1870年的如同棒喝之言:“我们国家能够袖手旁观,熟视这种玷污历史的前所未有的可怕罪行,从而成为这一罪行的帮凶吗?”他还援引格莱斯顿的另一句话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英国必须采取“反对任何大国扩张无度的行为”的立场。
他接着用自己的话说:“我要求下院能从英国利益出发,考虑这个存亡攸关的问题。如果法国战败投降……如果比利时落入同一统治势力之下,继而荷兰,继而丹麦……如果在这样一场危机之中,我们逃避根据比利时条约所承担的事关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我简直不能相信,在战争结束时,即使我们持旁观态度,能够把战争中所已经发生的情况改变过来,防止我们对面的整个西欧陷于独一无二的大国统治之下……我相信,我们也将在全世界面前丧失别人对我们的尊敬,丧失我们的名誉和声望,我们将无法逃脱最严重和最严酷的经济后果。”
他把“问题和抉择”摊在下院面前。下院“沉痛而专心地”听了一小时又一刻钟,最后爆发出一片掌声,表示响应。一个人能够驾驭整个国家的时刻是令人难忘的,事实证明,格雷的演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时刻,以后被人们奉为重大事件。但是依然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下院不同于大陆国家的国会,不必做到全体心悦诚服,完全一致。拉姆齐·麦克唐纳代表工党议员发言说,英国应保持中立;基尔·哈迪扬言他将唤起工人阶级反对战争;后来一群没有诚服的自由党议员在下院会客厅里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格雷没有道出参战的理由。但是阿斯奎斯深信,总的说来“我们那些极端的和平爱好者已经哑口无言,虽然他们不久之后还会说话的”。上午辞职的两位大臣晚上被劝了回来。普遍的看法是,格雷获得了举国支持。
“现在怎么办?”丘吉尔在和格雷一道离开下院时问他。“现在嘛,”格雷说道,“我们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停止对比利时的侵犯。”几小时之后,他又对康邦说:“如果他们拒绝,那就是战争。”虽然他差不多又等了二十四小时才发出最后通牒,但利希诺夫斯基担心的事情已成事实:比利时果真成了条件。
德国人之所以冒此风险,是因为他们以为这将是一场速决战,尽管那些文官领袖们到最后一刻还在唉声叹气,担心英国不知会采取什么行动,而德军总参谋部则已考虑了英国的参战问题,并且对此毫不介意。他们认为,这对一场他们相信四个月就会结束的战争不会有什么影响,或是根本没有影响。
克劳塞维茨,一位已经过世的普鲁士人,还有诺曼·安吉尔,这位虽然在世却为人所误解的教授,已不约而同地用速决战观念束缚了欧洲人的思想。速决取胜,这是德国的传统观念;一场持久战在经济上不可能也不胜负荷,这是人人皆有的传统观念。“你们在叶落之前就会凯旋回家,”德皇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对出征将士就是这么说的。德国宫廷社交活动的一个记事人员8月9日有这么一段记载:那天下午,奥佩尔斯多夫伯爵走进来说,战争不会打上十周之久;而霍赫贝格伯爵认为只需八周,尔后还说:“你我将在英国聚首。”
一名即将开赴西线的德国军官说,他预期可于色当日(9月2日)'注:色当日是纪念普法战争中法皇拿破仑三世率师在色当投降(时在1870年9月2日)的日子。——译者'在巴黎和平咖啡馆早餐。俄国军官也预期在大约相同的时间进入柏林;一般都认为六周时间足矣。一名御前近卫军军官征求沙皇御医的意见时,就曾问他是把大礼服随身带上以便开进柏林时穿着,还是留待下一班信使带往前线?一名曾任驻布鲁塞尔武官并被认为是一名知情人士的英国军官,在重返他的团队时,有人问他对战争可能打多久的看法。这位军官回答说,他可不知道,但他知道存在着“财政上的原因,大国因此不可能把战争拖长下去”。这是从首相那儿听来的,“首相对我说,霍尔丹勋爵是这么对他说的。”
在彼得堡,问题不是俄军能否取胜,而是需要打两个月还是打三个月;态度悲观认为需要打六个月的人就被视为失败主义者。“瓦西里·费多罗维奇(弗雷德里克的儿子威廉,亦即德皇)盘算错了;他是坚持不了的。”俄国司法大臣就是这么一本正经地预料的。这倒也不是什么谬误之见。德国没有作需要长期打下去的打算,所以在进入战争时,制造火药的硝酸盐储存仅敷六个月之用。只是后来发明了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方法,才得以继续打下去。法国人则是孤注一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速战速决上,竟然出此险着,不派军队驻守难以守卫的洛林铁矿区,听任德军占领。他们的理论是:胜利之时,这个地方也就会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