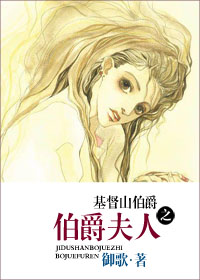基督山伯爵 作者:大仲马-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走廊里,她遇到了一个后退的黑影,那是尤莉,她也心中不安,比她的母亲先来了一步。那年轻姑娘向莫雷尔夫人走过来。“他在写东西。”她说道。她们不必说话就都已互相了解了对方的心思。莫雷尔夫人再从钥匙孔里望进去。莫雷尔果然在写东西,但莫雷尔夫人却注意到了一件她女儿没注意到的事,就是她的丈夫正在一张贴着印花的纸上写字。一个恐怖的念头闪过了她的脑子:他正在写遗嘱。她不禁浑身打了个寒噤,可是却没有力气说出一个字来。第二天,莫雷尔先生似乎象往常一样的平静,照常走进他的办公室,按时来用早餐,但在午餐以后,他就把女儿拉到了自己身边,抱住她的头贴在自己的胸前,拥抱了她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晚上尤莉告诉她的母亲,说他在外表上虽然是这样的平静,但她注意到父亲的心跳得很剧烈。以后的两天也是这样地过去了。到了九月四日晚上,莫雷尔向他的女儿要回了他办公室的钥匙。
尤莉一听到这个要求立刻就发抖了,她觉得这是一个恶兆。这把钥匙一向是由她保存着的,只有在她童年的时代,有时向她讨回只不过当作一种惩罚罢了,而现在她的父亲为什么要讨回这把钥匙呢?那年轻姑娘望着莫雷尔。“我做错了什么事,父亲?”她说,“你要向我讨回这把钥匙?”
“没什么,我的宝贝,”那不幸的人回答道,一听到这个简单的问题,泪水便盈满了他的双眼改革。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为之作序。另有1936,“没什么,只是我要它。”
尤莉假装在身上摸钥匙。“我一定把它掉在我的房间里了。”她说道。于是她走了出去,但她并没有回她的卧室,却赶快去和艾曼纽商量。“这把钥匙不要给你的父亲,”他说,“明天早晨,要是可能的话,一刻都不要离开他。”她问艾曼纽是怎么回事,但他也什么都不知道,或许是不肯说,在九月四日到五日的那个晚上,莫雷尔尔夫人留心倾听着每一个声音,她听到自己的丈夫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直到早晨三点钟。他是在三点钟才躺到床上去的。那一夜母女两人厮守着挨了过去。她们也在期待着马西米兰,他本该在傍晚时就到的。早晨八点钟,莫雷尔走进了她们的房间。他很平静,但在他那苍白和忧伤的脸上,显然可看出那一夜的焦虑。她们不敢问他睡得好不好。莫雷尔一生中从来也没象今天这样对他的妻子如此温柔,对他的女儿如此充满了父爱。他不断地凝视着娇美的姑娘,不断地吻她。尤莉没忘艾曼纽的话,当她的父亲离开房间的时候,就跟着他一起出去了,但他却急忙对她说,“去陪着你的妈妈吧。”尤莉想陪他。“我要你这样做。”他坚持说。这是莫雷尔生平第一次对女儿说,“我要你这样做。”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中仍满带着父亲的慈爱,尤莉不敢不从命。她站在老地方,哑口无言,一动也不动,片刻以后,门开了,她觉得有两只手臂抱住了她,两片嘴唇亲到了她的前额上。她抬头一望,发出一声惊喜的喊声。“马西米兰!哥哥!”她喊道。
听到这几个字,莫雷尔夫人站起身来,扑入她儿子的怀抱。
“妈,”青年叫道,他望望莫雷尔夫人,又望望他的妹妹,“怎么啦?你们的信吓了我一跳在的东西。主张社会改良主义,认为人类的天职在于创造一,所以我尽快赶回来了。”
“尤莉,”莫雷尔夫人边说,边对那青年作了一个表示,“快去告诉你父亲,说马西米兰回来了。”那年轻姑娘急忙冲出房间,但在楼梯口,她碰到一个人手里正拿着一封信。
“你是尤莉·莫雷尔小姐吗?”那人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问道。
“是的,先生,”尤莉吞吞吐吐地答道,“你有何贵干?我不认识你呀。”
“请读一读这封信吧,”他说完就把信交给了她。尤莉犹豫了一下。“这封信对令尊大有好处。”信差补充道。
年轻姑娘急忙接过信赶紧拆开,读道:
马上到梅朗巷去,走进门牌是十五号的那座房子,向门房要六楼上的房门钥匙。走进那个房间,在壁炉架的角落里有一只红丝带织成的钱袋,拿来给令尊大人。注意,他必须在十一点以前收到这只钱袋。你答应过要照我说的去做的。要履行你的诺言。
水手辛巴德上。
年轻姑娘发出一声欣喜的呼喊,抬起头来,四顾寻觅那信差,但他已经不见了。她的目光又回到了那封信上,又读了第二遍,发现原来还有一小段附言。她读道:“记住,你必须亲自去完成这项使命,而且必须单独去。要是让别人去,或由别人陪你去,则门房就会回答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这段附言使年轻姑娘的欢喜打了个折扣。她可以毫无担心地去吗?那儿会不会有某种陷阱在等待着她呢?她还很天真,不知道象她这种年龄的年轻姑娘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但对于危险的恐惧是不必事先知道的,真的,说起来,常常是不可知的危险会使人产生极大的恐怖。
尤莉心里犹豫不决,决定找人商量一下。可是,由于一种奇特的情感,她所要商量的对象既不是她的母亲也不是她的哥哥,而是艾曼纽。她急忙下楼去,把汤姆生·弗伦奇银行代表来见他父亲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把楼梯上的那幕情形讲给他听,并说她当时已答应过他,然后又把那封信拿给他看。
“那么,你一定得去,小姐。”艾曼纽说道。
“到那儿去吗?”尤莉问。
“是的,我可以陪你去。”
“但你没看到上面要求我一定要一个人去吗?”尤莉说。
“你是一个人去,”青年答道。“我可以在穆萨街的拐角上等你,假如你去得太久了,使我感到了不安,我就赶去接你,谁要是找你麻烦,我就要他好看!”
“那么,艾曼纽,”年轻姑娘吞吞吐吐地说道,“你的意见是我应该服从这个命令了?”
“是的,那送信人不是说这关系到你父亲能否得救吗?”
“他倒底有什么危险呀,艾曼纽?”
艾曼纽犹豫了一会儿,但为了使尤莉立刻做出决定,他不得不把实话说出来。
“听着,”他说,“今天是九月五日,是不是?”
“是的。”
“那么,在今天十一点钟,你的父亲差不多有三十万法郎要付。”
“是的,那我知道。”
“但是,”艾曼纽又说道,“我们公司里的现款还不够一万五千法郎。”
“那可怎么办呢?”
“所以,假如在今天十一点钟以前,你父亲找不到人来帮他,则到了十二点钟他就不得不宣布破产啦。”
“噢,来吧,来吧!”她大喊一声,急忙拖了那个青年就跑。
这时,莫雷尔夫人已把发生的一切都讲给她的儿子听了。
那青年已知道得很清楚了,自从灾祸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他的身上以来,家里的生活已起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不知道事情竟会发展到这步境地。他吓得呆如木鸡。然后,他冲出房间,奔上楼梯,想在办公室里找到父亲,但他敲了很长时间门,里面毫无动静。当他还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听到卧室的门开了,转过身来,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原来莫雷尔先生并没有直接到他的办公室去,而是回到了他的卧室,直到这时才出来。
莫雷尔一看见自己的儿子,就发出了一声惊喊,他根本不知道他会回来的。他一动不动地站在老地方,用左手紧按着一件藏在他衣服底下的东西。马西米兰三步两步跳下楼梯,扑上去搂住了他父亲的脖子,突然他缩回了身子,用右手按在莫雷尔的胸膛上。“父亲!”他喊道,脸刷地变成死灰色,“你衣服底下藏着这对手枪干什么?”
“噢,我也害怕这东西!”莫雷尔说道。
“父亲,父亲!看在老天的份上,”青年惊喊道,“告诉我,您究竟拿这些武器要做什么?”
“马西米兰,”莫雷尔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的儿子回答说,“你是一个男子汉,而且是一个爱名誉的男子汉。来,我解释给你听。”
于是莫雷尔跨着坚定的步子向他的办公室走去,马西米兰跟在他的后面,一路走,一路发抖。莫雷尔打开门,等他的儿子进来以后就把门关上了,然后,穿过前厅,走到他的写字台前,把手枪放在上面,手指一本摊开的帐簿。这本帐簿准确无误地记录着公司的财务状况。半小时后,莫雷尔就得付出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而他现在仅有一万五千二百五十法郎。
“看吧!”莫雷尔说道。
青年读着,感到愈来愈绝望。莫雷尔一言不发。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这样一个绝望的数字面前,还要什么解释呢?
“父亲,你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了吗?”青年过了一会儿问道。
“是的。”莫雷尔答道。
“你再没有可收回的钱了吗?”
“一点也没有了。”
“你在各方面都搜尽了吗?”
“都搜空了。”
“这么说半小时之后,”马西米兰用一种阴沉的声音说,“我们的名誉就要蒙受耻辱了。”
“血可以洗清耻辱的。”莫雷尔说道。
“你说得对,父亲,我了解你。”于是他伸手去拿手枪,说道,“一支给你,一支给我,谢谢!”
莫雷尔拉住了他的手。“你的母亲!你的妹妹!谁去养活她们呢?”
一阵寒颤流过青年的全身。
“父亲,”他说,“你想好了是要我活下去吗?”
“是的,我要你这样做,”莫雷尔答道,“这是你的责任。马西米兰,你有一个冷静坚强的头脑。马西米兰,你不是普通人。
我什么都不希望,我什么命令都没有,我只想对你说,你设身处地仔细为我想一想,然后你自己来作出判断吧。”
年轻人想了一会儿,他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崇高的听天由命的表情,用一种缓慢的,悲伤的姿势扯下那表示他的军衔的两个肩章。“那么,好吧,父亲,”他伸手给莫雷尔说道,“安心地死去吧,父亲。我会活下去的。”
莫雷尔几乎要跪到儿子的面前,但马西米兰抱住了他,于是这两颗高贵的心在一霎间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你知道,这不是我的错。”莫雷尔说道。
马西米兰微笑了一下。“我知道的,父亲,你是我生平所知道的最可尊敬的人。”
“好了,我的儿子,现在一切都说明白了,现在回到你母亲和妹妹那儿去吧。”
“父亲,”青年跪下一条腿说道,“祝福我吧!”
莫雷尔双手捧起他的头,把他拉近了一些,在他的前额上吻了几下,说道:“噢是的,是的,我以自己的名义和三代无可责备的祖先的名义祝福你,他们借我的口说:‘灾祸所摧毁的大厦,天命会使之重建。’看到我这样的死法,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怜悯你的。他们拒绝给我宽限,对你,或许会给的。要尽量不说出有失体面的话。要去工作,去劳动,年轻人,要热忱而勇敢地去奋斗,要活下去,你,你的母亲和你的妹妹,都要克勤克俭地生活下去,这样,你的财产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