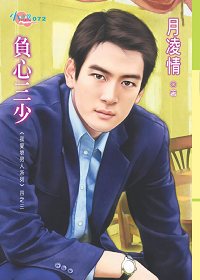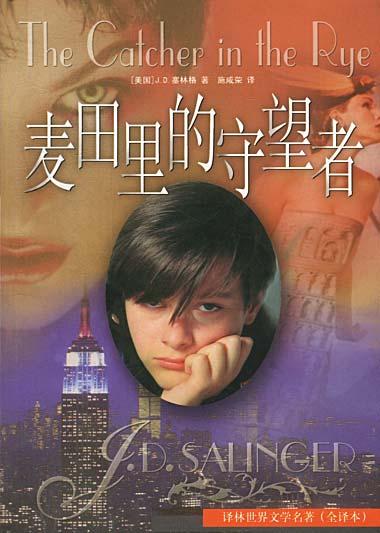城堡里的男人 [美] 菲立普·狄克-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电梯把奇尔丹撇在第二十层,他已经在心里点头哈腰,做好了进塔格米先生办公室的准备。
第三章
日落时分,朱莉安娜·弗林克翘首仰望,亮点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光,渐渐消失在西天。她自言自语道,又是纳粹火箭飞船,朝太平洋西岸飞去,满载着炸弹。而我就站在它底下。她走开去,尽管火箭飞船早飞远了。
落基山脉拉长了身影,蓝色的峰顶迎来了夜色。一群候鸟贴着山脊,缓缓地飞着。不时有车灯射过来,她看见高速公路上有两个亮点,也许是加油站的灯光,房子的灯光。
她在科罗拉多州的大峡谷城已住了好几个月,她在这儿当现代柔道教练。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她正打算去洗个澡。她觉得很累,所有的浴室都有人,都是雷思体育馆的顾客,所以她站在外面,在寒气中等着,享受着宁静和大山的气息。她现在只听到高速公路边的岔路上汉堡包停车场传来的细弱声音。两台庞大的柴油拖拉机停了下来,朦胧中可以看见两个司机在走动,他们穿上了皮夹克,走进了汉堡包停车场。
她想,戴塞尔不是从卧舱的窗户跳出去的吗?在航行途中跳海自杀?也许我也该那么做。但这里没有海,只有路。就像莎士比亚故事里说的,一根针扎透你的衬衫前襟,再见吧弗林克。从荒漠里来的姑娘无家可归,根本无需害怕抢劫。径直走小路会有许多令人不快的可能性,会遇到焦躁不安的魔鬼。死倒没什么,就怕穿过了漫长空旷的草地,在路边小镇抛锚。
她想,这是从日本人那儿学来的。以心平气和的态度来面对死亡,连同这赚钱的现代柔道一起。怎么自杀,怎么死。阴阳之间。现在都过时啦。这里是新教的国土。
看着纳粹火箭从头顶上飞过、不停下来,它对科罗拉多大峡谷城的东西都不感兴趣,这是件好事。在犹他州或怀俄明州或内华达州的东部也不停留,开阔的沙漠州或农牧州没什么东西。“我们不值钱,”她自言自语,“我们可以微不足道地活下去。如果我们想活下去的话,如果这关系到我们的话。”
有个洗澡问的门打开了。传出了吵闹声。一个身影出现了,那是大个子戴维斯小姐,她洗完了,穿戴好了,腋下夹着手提包。
“哦,弗林克太太,你还在等吗?对不起。”
“没什么。”朱莉安娜说。
“我想告诉你。弗林克太太,我从柔道当中获益匪浅,甚至比禅宗的打坐还要得益多些。”
“禅宗打坐可以使你的双臀苗条,”朱莉安娜说,“通过毫无痛苦的修炼就能减掉几磅。戴维斯小姐,对不起,我是在胡说八道。”
戴维斯小姐说:“他们伤你伤得厉害吗?”
“谁?”
“日本佬。在你学会防身之前。”
“可怕极了,”朱莉安娜说,“你从未到过那儿,在西海岸。他们在那儿。”
“我从未去过科罗拉多州。“戴维斯小姐说,她的说话声有点打颤。
“这儿也会发生的,”朱莉安娜说,“他们可能决定要占领这个地区。”
“不会这么快吧!”
“你绝对弄不清楚他们想干什么,”朱莉安娜说,“他们隐藏了真实意图。”
“他们要你干什么?”戴维斯小姐把手提包挪到胸前,双手紧抱着,在夜色笼罩中凑上前来倾听着。
“什么都做。”朱莉安娜说。
“哦,上帝。我会斗争。”戴维斯小姐说。
朱莉安娜说了声“对不起”就走进了空着的洗澡间。又有个人胳膊上搭着毛巾朝这儿走来。
稍后,她坐在塔斯迪·查利烤汉堡包店的小间里,懒洋洋地看着菜单。自动电唱机播放着美国南部山区的乡村歌曲;钢吉他情绪激动、哽咽的呜咽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油烟味。然而,这地方温暖、明亮,使她愉快。柜台边有卡车司机们的身影、侍者的身影。那个大个子爱尔兰厨师,穿着白制服,在出纳机前找零钱。
查利一看见她,就亲自迎上前来为她服务。他咧嘴一笑,慢吞吞地说:“小姐现在要菜吗?”
‘‘咖啡。“朱莉安娜忍受着这个厨师不地道的幽默。
“哦,是这样。”查利点点头说。
“还有热牛排三明治加肉卤。”
“不来碗汤吗?或者橄榄油煎山羊脑子?”那两个卡车司机,也转过身来,笑眯眯地插科打诨。他们满心欢喜地注意到了,她该是多么吸引人哪。即使那个厨师没有跟着起哄,她也会发现那两个司机在仔细打量她。几个月下来的柔道训练,使她的肌肉有不同寻常的弹性。她懂得怎样把握自己,展露自己的体形。当她面对他们的凝视时,她想这都与她肩部的肌肉有关。跳舞的人也是这样,跟身材没多大关系。把你们的老婆送到体育馆去,我们会教她们的。而你对生活也会更加满意。
“离她远点,”厨师使了个眼色警告那两个司机,“她会把你们扔进茅坑。”
她问那个年纪轻点的司机:“你们从哪儿来?”
“密苏里。”两个男人同时回答说。
“是美国人吗?”她问。
“我是,”年纪大的说,“费城人。有三个孩子。最大的11岁。”
“请问,”朱莉安娜说,“回那儿去找份好工作容易吗?”
年轻的货车司机说:“当然。如果你的肤色对路的话。”他的脸黝黑黝黑,一头黑色的鬈发。他的表情黯淡而又苦涩。
“他是个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年纪大的说。
“对呀,”朱莉安娜说,“不是意大利打赢了战争吗?”她笑容可掬地冲那个年轻的司机说,但他并没有报以笑容。相反地,他忧郁的双眼更加阴沉,突然他掉头走开了。
我很抱歉。她想。但她什么也没说,我没办法使你或别的什么人不变黑。她想起了弗兰克。我搞不清楚他是否还活着。说错了话,说漏了嘴。不,她想。不管怎样他喜欢日本佬。也许他已和他们打成一片,因为他们很丑。她常对弗兰克说他很丑。粗毛孔,大鼻子。她自己的皮肤细腻光滑,不同一般。没有我他会死掉吗?一个讨厌的家伙就是个雀子,一种鸟。他们说鸟会死掉。
“你们今天晚上返回吗?”她问那个年轻的意大利卡车司机。
“如果美国不舒坦,你们干吗不一劳永逸地横穿过去呢?”她说,“我在落基山脉住了好长时间,还不坏。我在西海岸的旧金山也住过。那儿也有肤色的问题。”
那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弓起背坐在柜台边,打量了她一眼说:“小姐,要在这样的小镇呆上一天或一夜那是糟透了。就在这儿?上帝啊,要是我能找到一份别的工作,不要在路上在这样的地方吃饭……”看见厨师的脸红了,他没再说下去,端起了咖啡。
年纪大的卡车司机对他说:“乔,你是个势利眼。”
“你可以住在丹佛,”朱莉安娜说,“在那里好多啦。”
我知道你们这些东海岸的美国人,她心想。你们喜欢天赐良机,梦想着远大计划。这就是你说的落基山脉各州的小镇。战前至今这里没发生什么事。退休的老人、农民,他们感觉迟钝、行动缓慢、贫穷……那些活跃的男青年都成群结队地往东去,到纽约去,合法或不合法地跨过了边界。她想,因为那是有钱的地方,大工业的钱。扩张。德国投资起了大作用……他们没花多长时间就把美国重建起来了。
厨师嘶哑着嗓子,生气地说:“伙计,我不喜欢犹太人,但49年我看见有些犹太难民逃到了美国。你有你们的美国。如果说那儿有许多建筑,有许多容易到手的钱,那是因为他们把犹太人踢出纽约时偷来的,该死的纳粹纽伦堡法令。我从小就生活在波士顿,我并不怎么喜欢犹太人,但绝没想到我目睹了纳粹的种族法能在美国通过,就算我们确实战败了。我很惊讶你们怎么不在美国军队里,作为侵入某个南美小国的准备,把它作为德国人的前沿,这样他们就能把日本人撵回去些。”
两个卡车司机都站起身来,满脸铁青。年纪大的从柜台上抄起一个装番茄酱的瓶子,举到了肩头。厨师依然面对着他们没转身,把手伸到背后摸到了一把又肉的叉子,举了起来。
朱莉安娜说:“丹佛正在建一个抗热跑道,汉莎公司的火箭可以在那儿降落了。”
这三个男的没一个人动弹,也没人讲话,其他的顾客都静静地坐着。
终于厨师开了口:“日落时有一架飞过去了。”
“那不是去丹佛的,”朱莉安娜说,“那是往西去的,去西海岸。”
慢慢地那两个卡车司机又坐了下来。年纪大的嘀咕道:“我总是忘记,离开这里他们有点胆怯。”
厨师说:“日本佬没杀犹太人,战时战后都没杀。日本佬没建焚尸炉。”
“他们没这么做才糟糕呢。”年纪大的司机说。他又端起咖啡,重新喝了起来。
胆怯,朱莉安娜想。是的,我猜那是真的。我们希望日本佬离开这里。
“你们打算在哪儿过夜?”她问道,问那个年轻的卡车司机乔。
“我不知道,”他答道,“我只是钻出卡车进来啦。我不喜欢这儿,也许我就睡在车里。”
“蜜蜂汽车旅馆还算可以。”厨师说。
“对,”年轻的卡车司机说,“也许我就住那儿。要是他们不介意我是意大利人的话。”他的口音很重,掩盖也没用。
朱莉安娜琢磨着他。是理想主义害得他这么怨天尤人,对生活的要求太多,总是动荡不安、浮躁不安、满腹牢骚。我也是一样的,我在西海岸呆不住,最终在这儿也呆不长。老辈人不也这样吗。她想,不过现在这里不是前线了,前线在别的星球。
她认为,我和他可以签约,为那些开拓殖民地的火箭飞船服务。但德国人会因为他的肤色和我的头发拒绝我的。那些漂亮的、白皮肤的北欧姑娘都在巴伐利亚的城堡里受训。这个叫乔什么的家伙甚至连面部表情都不对头。他应当持有那种冷酷而又热情的面容。好像什么都不相信而又有坚定的信仰。对,那就是他们的样子,他们不是像我和乔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讲信仰的犬儒主义者。那是一种大脑的欠缺,就像做了脑叶切除手术一一那些德国精神病医生残害这些人。将他们当作心理疗法可怜的实验品。
她断定他们的麻烦与性有关,他们在30年代就干了些与性有关的肮脏事,而且愈演愈烈。希特勒的性是与他的——什么人?他的妹妹?姑妈?侄女?他的家庭就是近亲繁殖的,他的母亲和父亲是表兄妹。他们都犯了乱伦的傻事,按原罪的说法,他们是色恋自己的母亲。难怪那些杰出的金发碧眼白皮肤的漂亮姑娘,有天使般的微笑,有孩子般的天真。她们为了妈妈保全了自己,或者为了彼此的需要。
那么谁是她们的妈妈?她疑惑不解。是领导人赫尔·鲍曼吗?他不是要死了吗?抑或是个病夫。
老阿道夫,据说在什么地方的疗养院里,过着老年性痴呆的生活。从他在维也纳当流浪汉的穷苦日子起就患了脑梅毒,黑色长大衣,脏兮兮的衬衣,住在廉价的小店里。
很显然,这是上帝讥笑的报复,就跟某部无声电影一样。那个可怕的人被内心的污秽所打倒,这是人类邪恶的历史性灾难。
令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