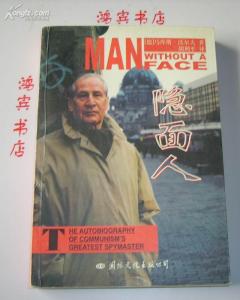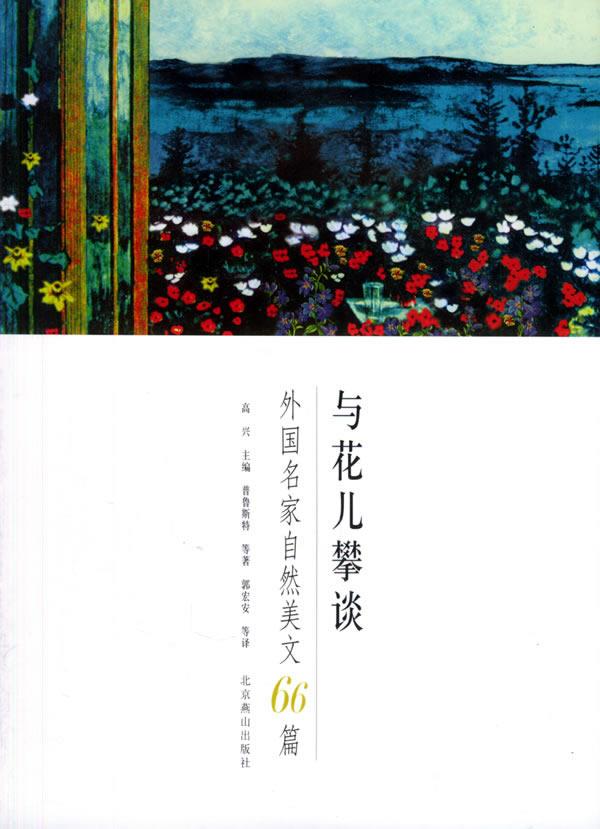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四辑)-第15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萨利!”鲍森医生说道,并把她扶住。“萨利,你不可能一下子做全部的事儿。你病了这么长时间。葛拉底,放下香水。喔,天哪,太荒谬可笑了。”
“她是什么意思,偷我的香水?”
“你让她生气了,”医生小心翼翼地让她躺在椅子上,在她脑后放了一个枕头。她微笑着,轻轻地拽住他的领带。
“你生我的气吗?你能原谅一个调皮的女孩吗?”
“喔,他妈的,”葛拉底说。
“梅森小姐不是佣人,”鲍森医生说道。“她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受人尊敬的护士。她不喜欢被唤来唤去的。你那个时代的事情已变了。黑人和白人一样受到尊敬。
“她说了一句脏话,”萨利道。
“她恼火了。我想让你俩都注意:梅森小姐要受到尊敬,萨利有病要受到照顾。都听到了吧。”
“是的,头儿,”葛拉底说道。
“行,当然可以,”萨利说。“梅森小姐,你心肠那么好,能否把衣服从地板上收起,挂在衣橱里的一个衣帽架上?”
鲍森医生迅速抓起衣服,把它重新穿上。“我要给你打针,然后离开,由梅森小姐带你去锻炼身体。”
“我真受不了那些针!你得先抓住我的手,否则我的心就会停止跳动了。”
鲍森医生握住萨利的手时,没有去看葛拉底,她把金黄色的头放在他的胸前。
“现在还是以后要我把Geritol 给你的女朋友?”葛拉底说道。
“别嫉妒嘛,她都七十岁了,”鲍森医生说。午后的阳光斜映在玫瑰园中,玫瑰花蕾被映得血红,草坪洒水机喷出的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她看起来不像那么大岁数的人。她行起事儿来也不像。
你什么时候告诉她的年龄?“
“我不知道,”鲍森医生说。“一方面我想她知道。另一方面……她才醒来一周,而且一切似乎还很顺利……我不知道。”
“你谈的是萨克医生病人的情况。”葛拉底坐在花园的长凳上,歇了歇脚。整个下午,萨利都不停地传唤她,一会要小吃,一会儿要书,要么是让她塞枕头。萨利总是小心翼翼地称她梅森小姐,甚是礼貌。
“他所有的病人最初恢复都很迅速,但不久就旧病复发。
有的轻微犯病,但其他人的情况比治疗前还糟。有些人,“鲍森医生坐在葛拉底身边,他注视着暮色中深绿色的草坪。”有些人死了。“
“为什么?”
“他认为他们的死是由于绝望。”一只蓝色的鸟嘴里叼着个蚱蜢,在花园和玫瑰花上空盘旋。它飞到了疗养院砖瓦屋顶上,把蚱蜢吞下了喉咙。它警惕地注视着那些花,晚霞的余光映得它的羽毛闪闪发亮。“我想用强力维他命,锻炼疗法和……休息。我要救救萨利。”
“你的意思是不打算告诉她真相,”葛拉底说。
“还没。我不知道。”
突然附近的房子里传来一声尖叫。鲍森医生和葛拉底立即站了起来,他们冲到萨利的房间,看到她背靠着墙,手里拿着台灯,高高举过头顶。她龇牙咧嘴,像个野兽一般。
“出去!出去!”她尖叫着,把台灯扔了过去;台灯撞到墙上摔得粉碎。玻璃的碎片散落在地板上的老妇人衣服上,但她根本没在意。
“你是我的一切,我爱你。”她啜泣着。
“把这个丑八怪轰出去!”萨利尖叫着。葛拉底扶着老妇人走出了房间。她把她带到花园的长椅上坐下。老妇人伏在她的胸前啜泣不止。葛拉底轻轻地抚摸着她稀疏的头发。
鲍森医生把萨利扶到床上。“她不是我妹妹!”她喊着,扑在他的怀里,嚎陶大哭。
萨利知道了谁为那次令人震惊的事件负责了。如果她是医生,她就会把那个傲慢的黑人遣送回非洲;但是当然鲍森不会这么做。她了解她的一切。父亲的一个朋友在哈莱姆养了一个女人,此事成了大家的笑柄。但是那女人确实住在哈莱姆。一次,萨利和汤姆在夜总会看见过她。她们走过许多恐怖的楼房;那些地方白给她贮存煤球她都不会要。成群的黑鬼站在路上,嚷个不停,好像没有他处可去一样。但这也很让人兴奋。萨利知道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她想彻头彻尾地了解生活。她真想挣脱汤姆爱的羁拌,让自己自由自在地沐浴在这种吵闹和笑声中。而汤姆却说这儿全是些扒手。
他们在夜总会时,正赶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绝妙的爵士乐表演。不断有许多长腿女人被扶出出租车。接着萨利便一眼看见了她。她穿着一件白色的丝裙,带花边的衣领,那顶可爱的带细绳的帽子盖住了耳朵。但是她体瘦如柴。虽然她看起来神采奕奕,但那深陷的眼窝,皮肤下凸出的骨骼都让萨利浑身震颤。她想这一定是罪孽的报应。
她的瘦弱半点儿都不像葛拉底——梅森小姐,萨利马上自我纠正道。她就像一头害相思病的母牛在医生周围转来转去。当然,他会保护她的。难道像犹太人一样吗?除了钱外,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是布尔什维克。但他很帅,并且更有趣的是让他在她周围忙碌,观看葛拉底——梅森小姐——生气地想着心思。
因此理所当然她想使自己平静下来,让那个丑八怪像她妹妹一样在她头脑中彻底消失吧。梅森小姐把她带进屋来并作了引见;梅森小姐坐在花园的长凳上,安慰着那个老骗子。
但是这个诡计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一天中剩下的时间鲍森医生都呆在萨利的房间里,而且她向他讲述了上流社会的一切,因为他是不会知道这一切的。而他听得也很着迷。
当他靠她很近时,她闻到他的皮肤气息,使她头晕目眩。
她感到像埃莉诺。格林作品中的一个女主角,碰上了一剂有威力的诱惑。某些不合适的男人就有这种诱惑。
“我和你谈话时,萨利,”他说,“我感觉现在仍是1924年。
我的意思不是我们在伪装或是看电影——但这个房间里的确是1924年。有时候我搞不清楚时间的意义了。“
“你这高明的谈话真要杀了我了。”萨利说。她把头转向一边以便他能仔细审视她美丽的脸颊。“不管怎样,说起电影,尽管鲁道夫。华伦天奴的眼神过于夸张,但我仍喜欢再次看到他。他把安格斯。爱尔斯扔到床上的镜头难道不吸引人吗?”
“华伦天奴早在1926年就去逝了,”医生说。这是他第一次谈及日期。
“太糟了(”萨利惊呆了。“是病死的?还是车祸?噢,天哪,我真想哭——他,他是那么英俊潇洒!”
“我想他是死于阑尾炎。”
“大可怕了!我就好像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别再告诉我这种悲伤的事了。我还想他曾骑马穿越沙漠与贝督因人作战,马背上坐着安格斯。爱尔斯。现在他还在,是的。不过是在影片里了。这也是一种永生,不是吗?”她现在抑制不住地放声大哭了。
“是永恒,”鲍森医生说。“对不起,我不该告诉你这些——”
“只要电影还在,华伦天奴就永远活着,永远年轻,他永远不会死,不会死——”
“他永远不会死。”
“那么这间屋里就永远是1924年,”萨利坚定地说。
“我发誓。”医生答道。
“那是什么?”萨利边问边拉动着鲍森医生扣紧的袖口的开口处。那看起来像用蓝黑水笔记的数字。“你一直在皮肤上作纪录,这是什么?关于我的吗?”她使劲拽着他的袖子。
“这些人不属于这间屋子,”他说道,“坚决地抽开他的胳膊。”萨利,我们是在水面上行走。我们俩儿,只要我们朝前看,永葆信心,我们就会没事儿。你懂吗?“
她想她是懂的。在水面下的是她的父母,朋友和她时而有的病症:她无法抑制的怪相以及时间的长期静止。他们全想淹死她,但她可以把他们抛在脑后。她能做到,医生的语气让她诧异。他似乎和她一般绝望,可能这是因为出于关心吧。对,不错。他是爱上她了,但为什么不呢?萨利曾经有过太多的情人,他们全都渴望得到她的垂青。即使医生老得像她父亲,但他毕竟笑容可掬,还有那玩意儿。
梅森小姐走进屋来说该锻炼了。萨利以一种最文雅得体的语调请她收拾一下梳妆台,并请她无论什么时候喜欢,就可以用乔伊牌香水。梅森小姐使劲推掇着那些瓶瓶罐罐,萨利觉得它们可能得碎了。鲍森医生告诉梅森小姐小心点儿干,而她却回了一句粗话。
“她的情况更糟了,不是吗?”葛拉底问道。
“是的,但在所有接受这种治疗的人中,她是疗效最佳的。
已经三个月了,虽然她时而会控制不住地产生臆想,但她时而还是很理智的。再加点咖啡吗?“鲍森医生往机器里投了些硬币。他按出了一些奶油和咖啡,但是尝起来仍然像地板上的垃圾一样。”在萨利的时代,他们可没有这样糟糕的东西。
他们在一个瓷杯里盛上真正酿制的咖啡,并给你一只用来搅拌的小匙,而不是压舌器“。
“我不会知道这些。那是我生下来之前的事儿,”葛拉底说,美美地呷了一口热咖啡。
两个护士坐在疗养院工作室的一边正热烈地谈论着发生在旧金山的一个可怖的谋杀案。“她的脑袋几乎被大砍刀砍断了,”其中一个说。
“他们砍掉了她的两个手指,没人能找到它们了,”另外一个兴奋地说。
“现在的人总是谈这个,”鲍森医生说。“萨利和他们这些专讲恐怖故事的家伙相比简直像一头纯洁的羔羊,而她谈及包女人时,还觉得自己无耻至极呢。”
“纯洁的羔羊,这又是她用的词吧?”
“我想是。这段日子一直在她左右,我已开始受了她的感染。”
“我说,你回家连枕头都没碰吧。”
葛拉底说。
又有一个护士走过来,描述了那个受害者胸脯上的啮痕。
“瞧瞧这些畜生!”鲍森医生又道。“他们是同样的一群人,也曾经排队欢呼德国纳粹党突击队队员们。你不跟萨利这样的人交谈就无法了解人类生活这五十几年来的堕落沉沦。她对罪恶的见解早就老掉牙了。”
“二十年代的罪恶也并不少哇。”葛拉底说。“只不过它们都是在羔羊们视力不及的黑暗中进行的勾当。鲁第,你莫不如收拾行装搬进去住算了。”她撕下一小块面包圈,在手上玩弄着。
“真他妈的奇怪。我在那屋里感觉完全不一样。连空气都不一样。”
“全是因为那些发霉的家具。”葛拉底说。
“那间房子还滞留在1924年,当时的世界和人们也存在于某个地方。我年轻的父母正在维也纳度蜜月。你不懂吗?这弥补了后来发生的事。如果当时的岁月永恒,我就会时常想象出他们还安全幸福地活着。否则,就哪儿都没正义了。一切都毫无意义。就是这样!”他的手猛地拍着桌子,葛拉底的茶杯被震翻了。几位护士都抬起头来好奇地看着他。
“我们有能力救她。”鲍森先生说。“我不知道以前我怎么没注意到这一点。不该让萨利适应现代生活。她就像一位刚动过移植心脏手术的病人。”
“我想他们是忘了做手术的后一半。”葛拉底说。
“我是当真的,心脏移植的人后半生必须抑制免疫系统,否则会抵触新器官。他无法抵御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