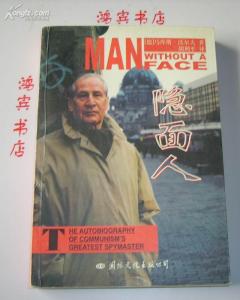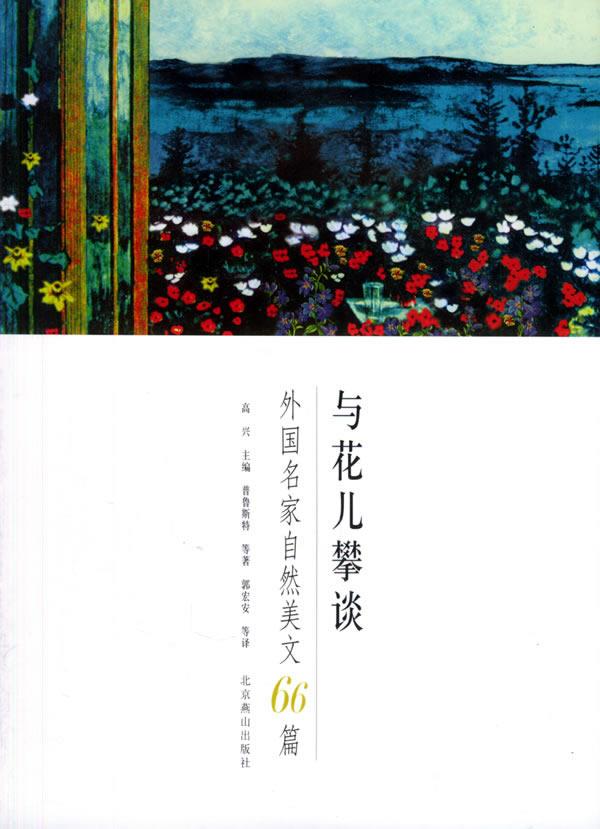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十辑)-第2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不能把他抛在这儿。”
“那怎么办,难道扛着他?”西蒙斯厉声说,“这对我们或他自己都没好处。你知道他在干吗?他只是站在那儿等着给淹死。”
“你说什么?”
“到现在你也该明白了。你不知道那个故事吗?他会一直站在那儿仰着头,让雨水冲进鼻孔和嘴巴。他会吸进雨水。”
“没听说过。”
“这是那次他们找到门德特将军时的情形。他坐在石头上,头向后仰,吸着雨水。
他的肺部全积满了水。“
中尉再次把灯转向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孔。皮卡德的鼻孔中发出微微的水响。
“皮卡德!”中尉给了他一个耳光。
“他甚至不能感觉到你,”西蒙斯说,“在这样的雨中呆上几天,你自己几乎都不能感觉到自己的脸或手脚的存在。”
中尉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他再也不能感觉到它了。
“但我们不能把皮卡德留在这里。”
“我来告诉你我们能做什么。”西蒙斯说着对他开了一枪。
皮卡德摔在了雨地上。
西蒙斯吼道:“别动,中尉。我的枪也为你上了膛。好好考虑一下吧,他只会或站或立地在那儿给淹死,这样死还快些。”
中尉冲着尸体眨了眨眼:“但你杀了他。”
“是的,要不这样,他会成为我们的负担,让我们也跟着去死。你刚才看见他的脸了,一脸的疯狂。”
过了一会儿,中尉点点头说:“好吧。”
他们又走进了茫茫的雨中。
天黑了,手灯昏黄的光只能穿透雨帘前不到几英尺的地方。半小时后,他们不得不又停下来,饥肠辘辘地坐着静候黎明的到来。拂晓时分,天灰蒙蒙的一片,雨一如既往地下着,他们又开始向前走。
“我们算错时间了。”西蒙斯说。
“没有,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大声点,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西蒙斯停下来,笑了笑,“我的天,”他说着,摸了摸耳朵,“我的耳朵,它们仿佛不属于我了。这倾盆大雨都快将我的骨头也弄麻木了。”
“听见什么了吗?”中尉问。
“什么?”西蒙斯一脸迷惘。
“没什么。走吧。”
“我想我要在这儿等会儿,你先走。”
“你不能那样做。”
“我听不见你,你走吧,我好累。我觉得太阳穹庐不在这条路上,就算在,也很有可能像上一个一样,屋顶上全是洞。我想我就坐在这儿吧。”
“你起来!”
“再会了,中尉。”
“你现在不能放弃。”
“我的枪告诉我,我得留在这儿了。我再也不想干什么了。我还没疯,但也快了。
我不想疯掉,所以当你走出我的视线时,我就用枪结束我的生命。“
“西蒙斯!”
“你叫了我的名字,我能从你的唇形上看出来。”
“西蒙斯。”
“喏,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我要么现在死,要么再过几个小时,等到了下一个太阳穹庐(如果能到的话),发现雨水从屋顶漏下时才死。那岂不是更惨?”
中尉又等了一会儿。之后,他又踏着雨向前迈动了步伐。他曾回头喊了一次,但西蒙斯只是手握着枪坐在那儿,等着他走出视野,并冲他摇摇头,挥手让他快走。
中尉连枪响都没听见。
沿途上,他开始吃路上的花。它们无毒,但不太能维持体力,只在他胃里停留了一会儿,也就一分钟左右,他便开始恶心得呕吐。
有一次,他摘了一些叶子来为自己做一顶帽子,尽管他以前已经试过,可惜雨水将叶子从他头上融化掉了。那些植物一旦被采下来便很快腐烂,在他指间化为灰白的一团。
“再过五分钟,”他对自己说,“再过五分钟我就会走进海里,并永不回头。这样的环境不适合我们,没有一个地球人能忍受,过去不曾,将来也不会。振作点,振作点。”
他挣扎着穿过一片烂泥和树叶的海洋,来到一座小山前。
远方冰冷的雨幕中,隐隐显出一个黄色的小点。
下一个太阳穹庐。
透过树林能看到远方有一座长圆形的金黄色建筑。他站在那儿,轻晃着看了好久。
他开始奔跑,接着又因担心而放慢了步子。他没有欣喜地大叫,如果这一个也是和上一个一样怎么办?如果这也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太阳穹庐,没有太阳在里面怎么办?他想。
他跌了一跤,跌坐在地上。就躺在这儿吧,他想,这穹庐没用。就躺在这儿。这没用。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但他仍设法支撑着再度爬了起来,横过了几条小溪。那金色的光芒越来越明亮。他又奔跑起来,脚步声像踏上了镜子和玻璃,手臂挥动着如宝石般的水珠。
他站在了金色的大门前,门楣上刻着太阳穹庐。他抬起麻木的手去触碰它。接着,他扭动了门锁,踉踉跄跄地跌了进去。
他站了一阵子,打量着四周。在他身后,雨点急旋着打在门上。面前的一张矮桌上摆着一满银壶热气腾腾的咖啡,旁边一个倒满咖啡的杯子上还有一块方糖;边上的另一个托盘上,厚厚的三明治夹着肥嫩的鸡肉、鲜红的西红柿和绿色的洋葱圈;眼前的横木上搭着一条厚厚的绿色土耳其大毛巾,一个放湿衣服的箱子;右边的小隔间里,热射线能立刻将人全身烘干,椅子上方有一套崭新的换洗制服,在等待着任何一位客人——他,或是一名迷途者——来使用它。更远些,有咖啡在铜壶里冒着热气,留声机静静地播放着音乐,书被红色或褐色的皮革装订得整整齐齐。书旁边有一张床,一张毫无遮蔽的温暖的床。一个人大可躺在上面,在占据了整个房屋的那个明亮事物的光线中尽情地吃喝。
他把手挡到眼睛上方,看见有人朝他走过来,但他没向他们说什么。片刻,他睁开眼睛看了看。制服上淌下的水在脚边积了一摊,他感到水正从他的头发、脸庞、胸膛、手臂和腿上渐渐蒸发开来。
金色的太阳挂在屋子正中央,巨大而温暖,它没发出一丝声响,整个房间鸦雀无声。门关紧了,雨对于他微有痛感的躯体来说仅是一场回忆。太阳高悬在屋顶蓝色的天空,温暖,晴朗。
他朝前走去,边走边脱下衣服。
《浴血战士》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我简直无法描述手术当时的这种剧痛,实在不能这样做,因为那是不可能用言词来刻画形容的。哪怕用再多的止痛药也无济于事,我之所以能承受下来仅仅是因为那些混蛋根本就没问一下我是否愿意,他们对我的意见不屑一顾。
当手术一切都结束后,我才睁开眼睛,望着那几个婆罗门的脸。他们总共有三个人,和往常一样穿着白色大褂,戴着面纱。一般人认为他们戴上面纱是为了不让我们认出,其实每个士兵都知道,这不过是挡挡而已。
我曾经被他们深度麻醉过,所以脑海中的记忆都是一片模糊,恍恍惚惚。我只记得很可怜的一点片断。
“我已经死去多久啦?”我问。
“10个小时多一些吧。”一个婆罗门答道。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难道你连这也想不起来吗?”长得最高的那人问。
“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
“那好吧。”那高个子说,“你们那个排原本据守在2645B-4战壕里,拂晓时你们奉令向2645B-5阵地发起进攻。”
“后来出了什么事情?”
“你被机关枪击中了。那是一种新型子弹,弹头是软的……难道连这也记不起啦?一颗子弹打在你的胸部,还有三颗打在腿上,卫生员把你抬起时你已经死了。”
“那个阵地被攻下了吗?”我问。
“这次还是没有能够拿下。”
“明白了……”
麻醉剂的作用在逐渐减弱.我又开始回想起另外一些事情:那是关于我们排里战友们的,2645B-4号战壕就像是我的故居——我们在它里面据守了一年多,敌人一直要占领它,这次我们在早上的出击实际上只是一种反击。我想起了子弹是如何击中我的——那时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轻松感,只有在那瞬间才能体验到……
这时我又想起一件事,于是急忙从手术台上坐了起来。
“等一等,伙计们。”我说。
“什么事情?”
“据我所知,再生手术的最大极限时间只能在死后的8小时内,是这样吗?”
“技术在不断完善啊。”婆罗门说,“现在就是过了12小时也还能使人死而复生呢,对任何伤员都一样,除非是大脑组织已受到严重的伤害。”
“原来如此,真棒!”我说。
这时我的记忆已完全恢复。
我想起了最后发生的那些情景,“不过这一次你们出纰漏啦。”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列兵?”他们中某个人用军官的口吻说。
“瞧瞧这个。”我把自已的证件递了过去。由于这时我能看见他的脸,所以他皱了一下眉头。
“真见鬼!”他扫了一眼证件后低声咕噜道。
“看来,我们已经取得一致意见了。”我指出了这一点?
“你知道吗?”他说,“当时战场上的尸体几乎是满山遍野,上头告诉我们,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命令我们治好所有的人。”
“这又怎么样?您没有看到我的证件吗?”
“你知道我们实在是太忙了!我当然非常抱歉,列兵,如果事先知道……”
“让您的道歉见鬼去吧。”我打断他说,“我要见总检察官!”
“你怎么啦?真的想要……”
“我的确这么想。”我再次打断他说,“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个懂法律的人,我要用比较合适的形式提出上诉,会见总检察官是我应有的权利,你们这群该死的!”
他们三人窃窃私语,而我则认真地检查了自已。应当承认这些婆罗门们的工作难度确实很大,当然并不是那么好,无法和战争初期的手术相比.皮肤移植得比较草率,有些内脏我也感到不大对头,右手竟比左手长出了两英寸——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凑合算了。
他们说完话以后,就把我的军服递给我,于是我穿上衣服。
“关于和检察官会见的事情。”他们中有一个人说,“那是有困难的,你也看见……”
艮长话短说吧,他们没有让我见到总检察官,代替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好心肠的中尉。是那种富有经验的老军人。他们和你谈活时会充满理解与同情,给你信心,让你感到你的事情根本不值一提。解决起来又那么简单,不费吹灰之力。
“有什么事情吗,列兵?”他问道,“据说,只是因为把您从死人变成可活人,您就胡缠蛮搅吗?”
“你说得对。”我回答说,“就是按照战时法律,每个普通士兵也都是有合法权利的,难道这也是无中生有吗?”
“邡当然不是。”中尉说,“为什么您要这么说……”
“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继续说,“我在部队有17年了,其中有8年是在前线度过的。曾经三次战死,又三次被复活。按照规定,战士在三次复活以后,每个人的尸体都有权不再受到骚扰。我正属于这种情况——您可以看看证件,上面一切都记着呢!而我却又再次被复活了!这些鬼医生干的全是些糊涂事,我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