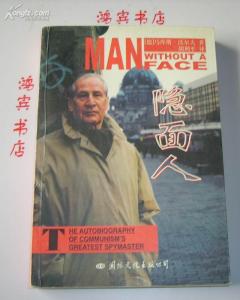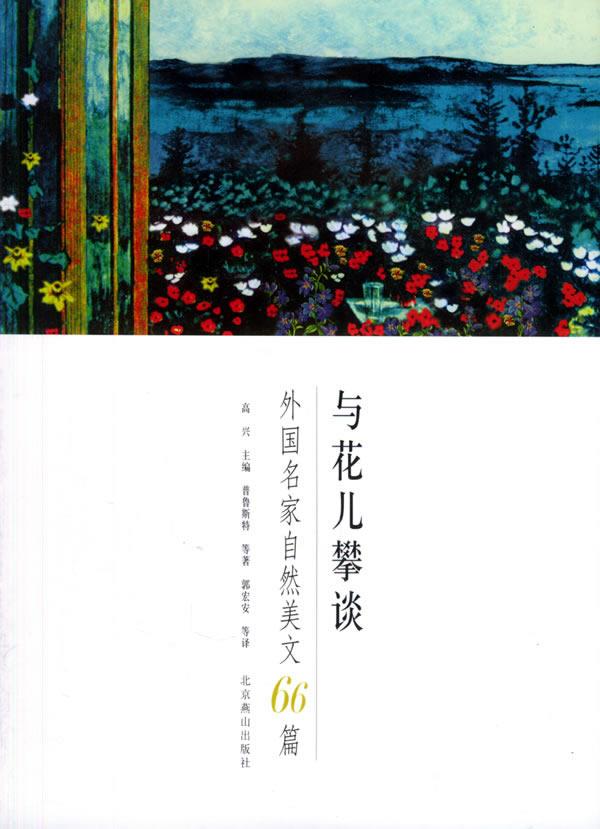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二辑)-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姐姐寄来的。”他说。
“你不是说你差不多一年没有收到她的信了吗?”
“自我收到这封信到现在已快一年了。”费尔顿答道,声音里含有一种感伤情调。“我还未曾开读过,她在密封的信里附有一个短札,上面只是说她健康愉快,并说明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开读这封长信。我姐姐就是那样;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我认为现在是必要的时候了,你说对吗?”
部长慢慢地点了一下头,但什么也没说。
费尔顿打开信,开始高声朗读起来。
亲爱的哈里: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离我们上次晤面时的交谈,22年已经过去了。对于我们俩这样互敬互爱的人说来,这是一段多么长的时间啊!既然现在你认为有必要开读这封信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再无相会的任何可能了。我听说你已经有了妻子和三个孩子——他们都是可爱的人。我想我将永远见不到他们或者和他们相识了,这是我万分痛心的事。
只有这件事使我悲伤。除此以外,马克和我都很愉快——我想你会理解的。
至于这道屏障——目前的确存在着屏障,否则你不会把信打开的——告诉他们,这个屏障没受到一点损害,并且谁也不会受到它的伤害。它不会突然发作起来,因为它是一种负动力而不是正动力,无代替了有。关于这点,我在后面还要多谈,但可能也解释不清楚。有些儿童可能会用容易理解的话说出,但我想把它作为我的报告,而不是他们的报告。
奇怪的是,我还把他们称为孩子,而且还认为他们是孩子——其实,这时在各方面都应当说,我们才是孩子,而他们则是成人。但他们还具有我们所熟悉的儿童品质,这就是在外部世界瞬息即逝的那种天真无邪和简单纯洁。
现在我们必须告诉你,我们的试验所获得的成果——或告诉你一部分。只能是一部分,我怎么能把人们经历过的最奇异的20年中发生的事全部记下来呢?这既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又是最平常的事。我们搜罗了一群超群出众的儿童,给他们以充分的爱、安全和真理——但我认为,最起作用的因素还是爱。在头10年间,我们废除了夫妇关系,把性欲减到最低限度,而把一切的爱都倾注到儿童们身上。他们也容易接受这种爱。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变成了我们的孩子——表现在各个方面。住在这里的夫妇所生的孩子也直接加入这个团体。谁也没有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我们是一个生气勃勃,各尽其职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所有男人都是全体儿童的父亲,所有女人都是他们的母亲。
不,这并不容易,哈里——在我们成年人中间,我们必须战斗和工作,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自身进行考核和彻底改造,把我们的心肝五脏全掏出来,以便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环境,表现出一种举世无双的公正、诚实和可靠的品质。
我该怎样告诉你一个5岁的美国印第安男童创作一曲壮丽的交响乐的故事呢?或有两个儿童,一个属班图人,一个属意大利人,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在6岁时造了一台光速测量仪呢?我们成年人静静地坐着听这些6岁孩童给我们解释:由于光速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常数,不管物体本身的运动状态如何;星球间的距离不能用光速表示,因为它不是我们这个生存空间里的平面距离。这些你能相信吗?还要请你相信,我是很不善于表达的。在一切事件中,我觉得像一个未受过教育的移民,他的孩子曾接触过千奇百怪的学业和知识。我虽了解一点,但很少。
假如我把这些事例和奇闻一桩桩,一件件,按六、七、八、九岁的年龄顺序喋喋不休地重复的话,你能想象出这些可怜的、备受折磨的神经质的小生命吗?他们的父母夸耀他们的智力商数达到160,同时都又哀叹命运没能使他们成为正常的儿童。是的,我们的孩子曾经是,现在依旧是正常的儿童。也许第一批正常的儿童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很长时间了,如果你听见他们笑过一次或唱过一次歌,你就会知道的。如果你能看见他们该多好啊,他们的身躯多么高大结实,体态多么匀称,举止多么文雅。他们具有一种我在儿童身上从未见过的品质。
是的,亲爱的哈里,我猜想关于他们的事情,多数都会使你震惊。他们大多数时候不穿衣服,性对他们说来永远是愉快而美好的,他们对于性生活和享受性的快乐像我们对待吃饭喝水一样的自然——也许比我们吃饭更自然,因为在我们这里没有色徒或饕餮者,没有胃溃疡或精神溃疡。他们互相接吻和抚弄,或做其他许多动作,这些在世界上都认为是不正当的、淫猥的,等等。但不论他们做什么,都做得得体,富于情趣。这一切是可能的吗?我告诉你,这是我最近大约20年来的生活状况。我和这些没有邪恶和病态的男女孩子们一起生活,他们都像异教徒或上帝一样——无论你做何想法。
但是,关于孩子们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故事,是要在适当的期间和场合讲一讲的。我这里记录的有关他们的一切表现,不过是要着意说明他们具有巨大的天赋和能力。马克和我对这结果从未有过丝毫怀疑;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控制了一个预示未来的环境,孩子们就会比外部世界的任何孩子学到的东西都更多。在他们生活的第七年,他们就能极其容易而自然地处理通常在外部世界的大学或更高的学样里讲授的科学问题。这是我们预料中的事,如果这类事情的某些方面没有得到发展,我们倒会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我们所希望的和密切注视着的事正是出乎预料的事——人类智力的发育,这在外部世界的一个人身上是受到阻碍的。
于是,便发生了下面的事情。原来,此事在我们工作的第五年开始于一名中国儿童,其次是一名美国儿童,然后是一名缅甸儿童。最奇怪的是,并没认为这是极不寻常的,直到第七年我们也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当时已经有5个这样的儿童了。
那一天,马克和我正在散步——我记得太清楚了,这是加利福尼亚一个晴朗、凉爽和迷人的日子——我们突然发现草地上有一群孩子,大约有20个,其中5个围成一个小圈坐着,第六个坐在圆圈中心,他们的头都几乎碰到一起了,发出一阵阵愉快而惬意的格格笑声。其余的孩子分成组坐在10英尺以外,目不转眼地注视着他们。
当我们走近他们时,第二组的孩子们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们肃静。于是我们静静的站在那里注视着他们。
大约10分钟后,5个孩子组成的圆圈当中的那个小姑娘跳了起来,欣喜若狂地喊道:“听见了,听见了,我听见了!”
她的声音里包含着一种我们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成功的兴奋,甚至从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也从未听到过。接着,所有的孩子都拥到一起,吻她,拥抱她,围着她嬉戏,欢呼雀跃。我们注视着这一切,没有一点惊异甚或好奇的表示。
因为即使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发生——出乎我们的猜测或理解之外,我们还是做出了对这种事情的反应。
当孩子们向我们涌来,让我们祝贺时,我们频频点头微笑,并同意这一切都很了不起。
“现在该我了,妈妈,”一个塞内加尔男孩对我说,“我已差不多会了。有6个人帮助我,这就更容易了。”
“你不为我们感到自豪吗?”另一个喊道。
我们同意我们都很自豪,但回避了其余的问题。于是,在当于晚上的工作人员会议上,马克讲述了近来发生的事。
“上星期我就注意到了,”我们的语文学教员玛丽·亨吉尔点点头说,“我注意到他们,但他们没看见我。”
“有多少人呢?”戈德鲍姆教授急切地问。
“3个,第四个在中间,他们头部都聚在一起,我以为这是他们做的一种游戏,于是就走开了。”
“他们并不保密。”有人说。
“真的,”我说,“他们认为我们理所当然地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谁都没有说话,”马克说,“我敢肯定没人说话。”
“但他们在听,”我说,“他们格格地大声笑,好像在讲什么天大的笑话似的——或者是孩子们在笑使他们逗乐的一种游戏。”
还是戈德鲍姆博士说得中肯。他非常严肃地说,“你应当知道,琴——你总是说,我们或许能打开在我们之中锁闭着的巨大的思想领域之门。我认为孩子们已经把门打开了,他们正在教和学如何听思想。”
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我们的心理学家之一阿特华特不安地说,“我不相信,我研究过我们国家曾经出版的关于心灵感应的每一份实验报告——杜克的资料和其他全部材料。我们知道大脑波多么细小微弱——设想把大脑波作为一种通信联络手段简直是异想天开。”“还有一个统计学上的因素,”数学家罗达·兰农观察过,“甚至如果人类存在这种潜在本领的话,你能想象得到,会没有记载的例证吗?”
“或许已经有记载了,”历史学家之一弗莱明说。“你能列举出历史上所有的鞭笞、燃烧和绞刑,确定哪一种是心灵感应吗?”
“我认为我同意戈德鲍姆的说法,”马克说,“孩子们正在掌握心灵感应法。我丝毫不为历史的争论或统计数字所动摇,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对环境问题着了迷。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把类似的一群不平凡的孩子抚养成人,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再则,可以说是或可能是一种必须有儿童时代发挥出来的本领,或一种被永远禁锢的本领。我相信,当我谈到在儿童时期就受到思想禁锢并不是不寻常的事时,黑尼格森博士将会支持我的论点。”
“不仅如此,”我们的精神病主治医生黑尼格森博士点点头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没有一个儿童能够幸免思想禁锢,每个人的整个思想领域都在儿童早期就受到了压抑。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绝对真理。”
戈德鲍姆博士吃惊地望着我们。我想说点什么,但欲言又止。我等待着,听到戈德鲍姆博士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经开始认识到我们都可能做过些什么。人是什么?他就是自己记忆力的总和,被禁锢在自己的头脑里,他所经历的每个时刻只是构成这些记忆的轮廓。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弄来的这些儿童可能发挥的禀赋能力有多大,但假设他们达到了享有全部记忆力的程度。不光是在他们之中没有诺言、欺骗、文饰、秘密和犯罪——远远不止这些。”
然后,他把我们这些职员环视一圈,在我们的脸上逐个搜索。我们开始理解他了。我还记得我自己在当时的反应,一种惊奇、忽有所悟与欢喜交织在一起的感情,这种感情是这样使人心酸难忍,以致于眼里泪如泉涌。
“不是吗?我认为,”戈德鲍姆博士点点继续说,“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我最好还是说一说。我的年纪比你们都大得多,我是过来人了,我经历过人类了解到恐怖与兽性的最艰难的岁月。当我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时,我曾千遍万遍地自问:人类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多少有一点意义,它是否是一种简单的偶然事件,它是否是分子结构的不寻常的复合体?我知道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