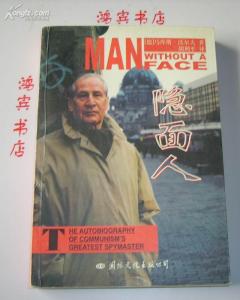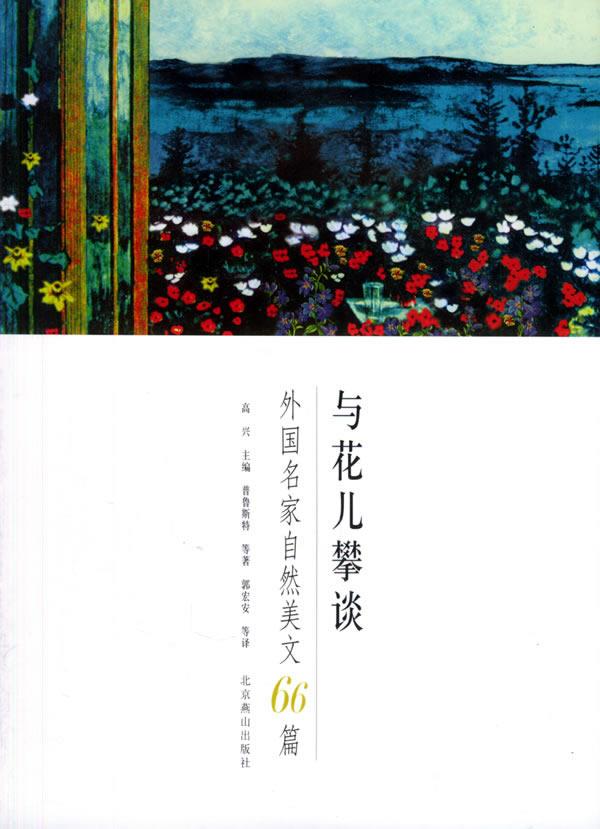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二辑)-第2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关于这个梦,他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只是在学校里学习实用心理学时,间接地假称是某本书上读到的那样提了一下,老师洞悉了他的心理告诉他这是一种被压抑的玩布娃娃的心理渴求。他说:“这个家伙在扮演角色,他强烈地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女人,这些被社会排斥受压抑的同性恋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此等等。梦境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肉欲的满足,小丹迪什觉醒了,因为受到老师谴责而忿忿不平。
但西尔维娅既不是梦也不是一个布娃娃。“我不是布娃娃。滚出来,把这事给了结了!”言辞尖刻而又坚定,让人震惊。
她站有了身子,垂着手,握着拳,满脸怒容,但毫不畏惧:“虽然我必须承认有这种可能,但我还是很疑惑,除非你是真的疯了,你明明知道,你不可能做任何我不希望你去做的事。因为你不能掩饰一切,对不对?你不会杀我,否则你永远都不能向别人解释清楚,而且他们也不会让一个杀人犯再去全权负责一艘飞船了,所以飞船着陆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喊警察,那接下来的九十年你只好去开地铁了。”她格格地笑了起来,“这方面我很了解。我的一个叔叔就因为逃避个人所得税而被降级,现在就像亚马孙三角洲上的一条自动推进式挖泥船一般狼狈不堪,你应该来看看他写的信。所以滚出来,我会很乐意让你逃避一切罪责的。”
她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摇摇头说道:“该死的,我说的没错吧?哦,对了,我得上趟厕所,然后我想要份早餐。”
丹迪什在这些要求中得到了些许的满足,至少,他是预见到这些的。他先开了通向厕所的门,然后打开加热炉热了一点浓缩食物。西尔维娅上完厕所回来时,饼干、咸肉和热咖啡都已经给她端出来了。她伸伸腰,打了个哈欠。
“我猜想你不会有香烟吧。”她问道,“我得生活,给我件衣服,出来让我见见你吧。”
显而易见她刚淋浴过,头上裹着一条小毛巾,皮肤也不见得那么干裂了,真是楚楚动人。丹迪什当时很勉强地在厕所里放了一条小毛巾,但没想到这位受他骗的女孩竟用它来包头。
西尔维娅坐在那儿盯着吃剩的早餐,若有所思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又像演说家似的说了起来:
“我知道,开飞船的往往是一些混蛋,换了别人,谁会一出门就二十年的呢,即使是为了钱,为了任何形式的钱。不错,你就是一个混蛋。所以你把我弄醒了,又不出来和我说话,那我对你也就无能为力了。
“现在,我算明白了,假如你不是因为糊涂干了件蠢事,那么飞船上的这种非人的生活,也会把你击垮的。也许你只是要找个伴?我能理解你。我甚至可以和你合作,为你而守口如瓶的。
“另一方面,也许你正在努力克制住自己的一些粗俗的想法。不知道你是否能做到,因为他们在给你这份工作之前自然对你进行过细致的审查。不过,设想一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假如你杀了我,那他们会把你抓起来;假如你不杀我,那着陆时我会告诉他们事实真相,他们也会把你抓起来。
“我跟你讲过我叔叔的事情。他就冷藏在水星阴暗面的某个地方,头脑里的那些去贝莱姻星球的航线信息全部消除掉了。你或许认为情况不至于这么糟吧,亨利叔叔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的。我猜他当时的情况和你一样糟,气管炎一直都没有好,又没有个伴。当然他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混日子,不过那样的话他就会被调到别的不那么好的地方去了。所以,他敢怒不敢言,倒不如尽可能地寻些开心好。九十年哪!他到目前为止也干了六次,从我离开地球(不管现在叫什么)的时候算起。你也是迫不得已才干的,那么为什么不出来,我们谈一谈?”
她做了做鬼脸,然后又拿起个面卷,涂上黄油,猛地朝墙边的处理器扔去,水马上把它冲走了。这样过了五分钟也可能是十分钟之后,她又说道:“你这该死的,不管怎么说,给我一本书看看吧。”
丹迪什离开了她。他听到飞船在嗖嗖地飞着。过了一会儿,他打开了栅栏开关。他已经输得够惨了,不能再继续输下去了。栅栏展开了,女孩不由得跳了起来。栅栏柔软的触手把她抓了进去,绑带拦腰捆死了她。
“你这该死的蠢驴!”她大声喊叫着,但丹迪什懒得去理她。
麻醉锥体降到了她的脸部,她大叫大嚷地挣扎着:“等一等!我没说我不愿意——”不愿意干什么?她再也不能说出来,锥体使她失去了知觉。一个塑料袋伸出来把她的脸,她的躯体,她的腿,甚至散落在头发边的毛巾全给盖住了。栅栏悄无声息地退到了冷藏室里。
丹迪什没有再看下去,他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另外,报时器也在提醒他又该去做常规检查了。温度,正常;燃料损耗量,正常;航线,正常;冷藏室一个新舱还在储存,其它一切正常。别了,西尔维娅,实在不该选你作目标,丹迪什自言自语道。
可以想像,不久以后,又会有一个女孩被选出来……
不过,弄醒西尔维娅花了他九年的时间,他想他不会再干了。他想到了她那位叔叔在南大西洋河岸开挖泥船的情景,现在轮到他自己了。他得在监禁中度过余生,再不能去开飞船了。
他用光学接收仪向外“看”了“看”下面的那一千万颗恒星,用雷达无助地“触摸”着整个太空世界,然后又在船后排放了整整五百万英里的离子流。他想到了船上的那些无助的数以吨计的躯体,他本来是可以从这些躯体中获得愉悦的,假如他自己的躯体不需要和亨利叔叔的一块儿呆在冰冷的水星上的话。这更助长了他的恐惧感,假如他还能激起自己的恐惧感的话;他也会哭的,假如他还能哭的话。
《二○○二年八月夜遇》作者:雷·布雷德伯里
李罗鸣 译
进入蓝色的群山之前,托马斯·戈梅兹在那间孤零零的加油站前停下来,给车加油。
“这儿有点冷清,是吗老爹?”托马斯说。
老头擦着小卡车上的挡风玻璃:“还不坏。”
“你觉得火星怎么样,老爹?”
“挺好,总有些新鲜玩意儿。去年刚来的时候我就打定了主意。我总会遇到些啥,问些啥,或者为啥吃惊。咱们得忘掉地球和那儿的东西,咱们得看看在这儿自个儿算什么,得看到这有多特别,就是这儿的天气都让我觉得有意思极了。这就是火星的天气,白天热得像地狱,晚上冷得像地狱。我真喜欢这儿特别的花和雨。我来火星是为退休,我想到个啥都特别的地方退休。老头需要特别,年轻人不肯跟他谈,其他的老家伙又受不了他。所以我想对我来讲最好有个地方,能特别得让你要做的就是睁开眼,尽情欣赏。我弄到了这个加油站,要是事太多,我就搬到其它不太忙的旧公路去,在那儿我既能挣钱糊口,又有时间去感受这里特别的东西。”
“主意真不错呀,老爹。”托马斯说,棕色的手随意地搁在方向盘上。他心情很好。他已在一个新殖民地连着干了十天,现在有两天空,打算去参加一个聚会。
“我再不为啥而吃惊了,”老头说,“我只是看,只是体验。要是你不能把火星看成它本来的样子的话,你大概也会回地球去。这里啥都有点疯疯癫癫的:土壤,空气,当地人(我还没见过,但我听出他们在周围),钟表。连我的钟都走得不对劲,这儿连时间都发了疯。有时我觉得就我一个人在这儿,整个该死的星球没别人了。我打赌是这样。有时我觉得自己只有八岁大,身子骨缩成一团,其它东西都变高了。老天,这正是个给老头准备的地方,让我警觉,叫我高兴。你知道火星是什么吗?就像七十年前我得到的圣诞礼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一个——他们叫它万花筒。里边尽是碎水晶,破布头,小珠子和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你把它举起来对着阳光看,就会大吃一惊。那些图案可真绝!那就是火星。尽情享受吧,让它保持原样,别要它变成别的。老天,你知道那边的公路吗?火星人修的,过了十六个世纪还没坏。一共一美元五十美分,谢谢,晚安。”
托马斯把车开上那条古公路,默默地笑了。
这条路很长,一直延伸到黑暗和群山中。托马斯抚着方向盘,时不时从午餐篮子里摸出块糖来。他安安稳稳地开了一个小时,路上没见一辆车,也没有一点亮光。只有这条路不断延伸,在卡车发出的细微的嗡嗡声和洪亮的轰响中延伸。火星就在眼前,如此静寂。火星一向安静,但今晚比以往更宁静。他驶过沙漠和干涸的海洋,驶过以星星为背景的群山。
今晚空气里有股时间的味道。他笑了,脑海里转着这么个怪念头。是有这样一个想法。时间闻起来是个什么味儿,是尘土味,是时钟味,还是人类的味道?想知道时间是种什么声音吗?它是黑暗的洞穴里流动的水声,是哭喊声,是尘土落在空盒盖上的声音,还是雨声?再想远点儿。时间是什么样的?时间是静悄悄落进黑屋子的雪;时间是古代影院里上映的影片,一百亿张脸像新年气球一样坠落,坠落,直至消失。这就是时间的味道、形状和声音。今晚——托马斯把一只手伸出窗外,迎着风——今晚你几乎可以摸到时间。
他在时间的山峦间行驶,感到脖颈有点刺痛,就坐直了,看着前方。
他把车开进一座废弃的火星小镇,关上引擎,全身心投入寂静中。他默然坐下,注视着月光下的白色建筑。多少世纪都没人住了,完美无缺,毫无瑕疵。一片废墟,没错,但无论如何,还是完美无缺。
他又发动引擎,开了大约一英里就停了下来。他带着午餐篮子爬出车来,走上一个小小的岬角,在那里他能回望那片城市废墟。他打开保温瓶,倒了杯咖啡。一只夜鸟飞过。在这片宁静中,他感觉好极了。
约五分钟后传来了声音。山那边古公路转弯的地方,出现了一点动静,又闪出一道微弱的光,然后传来一声咕哝。
托马斯手拿咖啡杯,慢慢地转过身。
山中出现了一个怪物。
这是台机器,看起来很像只玉绿色的虫子,比如说螳螂,灵巧地从寒冷的空气中蹿出。它身上有无数模糊不清的绿钻石和红宝石,绿钻石像在眨眼,红宝石的各个刻面都在闪烁。
它的六条腿落在古公路上,发出雨滴似的声音。机器后部坐着个火星人,眼睛像熔金。他俯视托马斯,就像在看一口井。
托马斯举起手,不自觉地想说“你好”!但他的嘴一动不动,因为这是个火星人。可托马斯在地球的蓝色河流中与路遇的陌生人游过泳,在陌生的房子里与陌生人吃过饭。他的武器就是笑容。他从不带枪,现在也没觉得有这个必要。尽管因为一点小小的恐惧,他的心脏缩紧了。
火星人的手也是空的。他们隔着寒冷的空气对视了一会儿。
托马斯先动了。
“你好!”他叫道。
“你好!”火星人用自己的语言说。
双方都没弄明白彼此的意思。
两人都问:“你是在说‘你好’吗?”
“你刚才说什么?”他们又问,各用各的语言。
两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