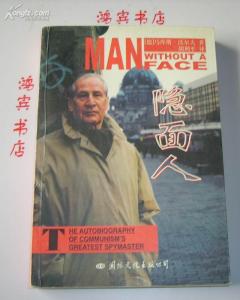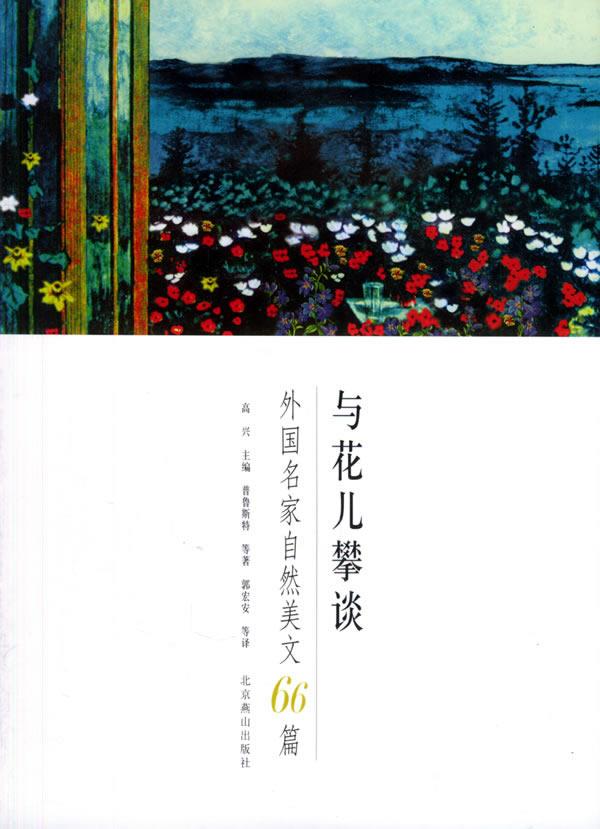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二辑)-第10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活下来的理由?我可找不出来。”
“是命运,命中注定我要出现在你的房子里。”
“你又不是凭空出现的,”我说。“你是从你丢掉衣服的什么地方走到这里来的。”
“不,”他坚决地摇了摇头。“前一分钟我还漫步在我亥利姆的皇宫,下一分钟我就失去了盔甲和武器,站在了你的院子里。我试着想回去,但是飞舞的雪花让我无法看到巴松,而如果我看不到它我就不能够到它。”
“你对每一件事都有完美的解释,”我疲惫地说。“我敢打赌你的罗尔沙赫氏测验(注:视对墨渍图案反应而分析其性格的实验)成绩也一定一流。
“你认识你所有的邻居,”约翰说。“你以前曾见过我吗?你觉得一个裸体男人可以在暴风雪里走多远?曾有警察来警告你有精神病跑出来了吗?”
“即使对警察来说,今晚也不适合出行,而且你看起来象是那种无害的精神病。”我回答。
“现在是谁拥有完美的解释?”
“好吧,好吧,就算你是约翰卡特,而德贾?托里斯正在天空中的某处等着你,并且是命运将你带到了这里,而明天早上也不会冒出个焦急万分的家伙来寻找他走丢的堂兄或是兄弟。”
“你看过我的书,”他说。“至少看过一些。在你的书房里我看到它们了。用书里的内容来考考我。随便你问什么。”
“那能证明什么?有成百上千的小孩子都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它们。”
“那么我猜我们就只能在这里呆坐一宿了。”
“不,”我说。“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但是答案不在那些书里。”
“好。”
“好吧,”我说。“你怎么能对一个从蛋壳里孵化出来的女人如此动情呢?”
“你又怎么能爱上一个有爱尔兰或是波兰或者是巴西血统的女人?”他问。“你又怎么能爱上一个黑种女人,或是红种人或者白种人?你又怎么能爱上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犹太教徒?我爱我的公主因为她是谁,而不是因为她可能是谁。”他停顿了一下。“你为什么笑?”
“我在想我们今年培养出了一批思想敏锐的疯子。”
他指了指丽萨的一张照片。“我敢说她和你毫无共同点。”
“她和我有太多的共同点,”我说。“除了传统、信仰以及教育之外。很古怪,不是吗?”
“为什么?”他问。“我从来不觉得爱一个火星女人有什么古怪的。”
“我想如果你能相信火星上有人居住,而且那些人还是从蛋里孵化出来的,那我相信爱上他们中的一个也没什么难的。”
“为什么你认为去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会如此疯狂呢?一个优雅、充满骑士精神的世界,一个礼貌而高贵的世界。为什么我不该爱上那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如果我没有爱上她难道不是更疯狂吗?当你与你的公主邂逅,你可曾想过要离弃她?”
“我们不是在谈论我的公主,”我生气地说。
“我们谈论的是爱。”
“无数人坠入爱河。但没有一个要因此到火星去。”
“那么,现在我们谈论的是为爱付出的牺牲。”他伤感地微微一笑。“比如说我,我在这里,三更半夜,远离我的公主四千万英里,和一个认为我属于精神病院的人坐在一起。”
“那么为什么你要从火星回来呢?”我问。
“那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他停顿了一下,好像在回忆。“当它第一次发生时,我想一定是上天在考验我,就像他曾考验约伯。我花了十年时间才返回去。”
“而你从来没有想过它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那些古老的城市,干涸的海底,那些战场,凶猛的绿皮战士,我可能会幻想出它们。但是我绝不可能幻想出对我的公主的爱;每一天,每一分钟我都能感受到它,她声音的柔美,她皮肤的光滑,她发丝的清香。不,我不可能臆造出所有这一切。”
“在你的流放期间这一定是一种安慰。”我说。
“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折磨,”他回答。“每天我仰望星空,我都知道她和我未曾谋面的儿子在那无法想象的远方。”
“但你从未怀疑过?”
“从未,”他说。“我依然记得我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相信他们正在等我,而且我想我很快就会知道。”
“无论真实与否,至少你能够相信它,”我说。“你不曾看着你的公主死在你的面前。”
他凝视着我,好像在思索接下来所要说的话。最后他说。“我死过很多次,如果天意如此,我明天会再死一次。”
“你在说些什么啊?”
“只有我的意识能够穿过两个世界的时空,”他说。“我的躯体会被留在身后,一具毫无生命的躯壳。
“而它既不会腐烂也不会干枯,它只是等待你回来?”我讽刺地说。
“我无法解释它,”他说。“我只会使用。”
“我应该感到安慰吗?一个自认为是约翰卡特的疯子在暗示我丽萨可能还活在火星?”
“我会感到安慰的,”他说。
“是啊,可是你疯了。”
“我认为她可能去了火星的这个想法很疯狂吗?”
“绝对疯狂,”我说
“如果你身患绝症,宁愿寻访世界上的每个自称可以医治它的骗子也不老老实实坐在家里等死,这疯狂吗?”
“所以你是个骗子而不是疯子?”
“不,”他说。“我只是一个宁愿死也不愿失去我的公主的人。”
“我赞同,”我说。“但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公主。”
“才十个月。我曾失去我的公主有十年。”
“那是不同的,”我指出。“我的公主死了,而你的公主还活着。”
“还有另一个不同,”他回答。“我有勇气去寻找我的公主。”
“我没有丢失我的公主。我很清楚她在哪里。”
他摇了摇头。“你只知道她不重要的那部分在哪里。”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如果我有你的这份信念我也会满足于你的疯狂。”
“你不需要信念。你只需要勇气去相信,不在于什么是真实的,而在于什么是可能的。”
“勇气是给军阀预备的,”我回答,“不是为我这个六十四岁的糟老头准备的。”
“每个人都有未开启勇气之井,”他说。“或许你的公主不在巴松。或许那里根本没有巴松,或许我确实像你想得一样疯。但你真的满足于接受这样的事实吗?还是你愿意鼓起勇气希望我是对的?”
“我当然希望你是对的,”我暴躁地说。“那又怎样?”
“希望指引信仰,信仰指引行动。”
“它指向玩笑农场。”
他看着我,脸上浮现出忧伤的神情。“你的公主完美吗?”
“十全十美,”我毫不犹豫地说。
“她爱你吗?”
我知道他还要继续问下一个问题,但是答案脱口而出。“是的。”
“一个完美的公主会爱上一个懦夫或是一个疯子吗?”他说。
“够了!”我呵斥道。“再过去的十个月里保持精神健全已经够艰难了。现在你有跑来列举这些充满诱惑的可能。我不能把我余生都花来想我会找到某种方法来再见到她。”
“为什么不?”
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接着我明白他没有。
“暂不说这很疯狂,即使我真的这样做了也将一事无成。”
“你现在这样又成了什么事呢?”他问。
“什么也没有,”我突然泄了气,承认道。“每天早上,我起床后所作的全部事情就是等着这天慢慢的结束,这样我就能回去睡觉,在我再次醒来之前都不用看着她的面孔浮现在我眼前。”
“而你认为这才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的理性行为?”
“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行为,”我回答。“她死了,她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你太看重现实了,”他回答。“一个现实主义者看到硅;一个疯子看到可以思考的机器。一个现实主义者看到黑根霉了;一个疯子看到不可思议的传染病解药。一个现实主义者看到繁星并自问,有什么好担心的?一个疯子看到同样的星辰并自问,为什么不担心?”他停顿了一下并聚精会神地瞪着我。“一个现实主义者会说,我的公主死了。一个疯子会说,既然约翰卡特能找到了征服死亡的方法,为什么她不能?”
“我希望我能这么说。”
“但是?”他说。
“但是我不是疯子。”
“我为你感到难过。”
“我可不为你感到难过。”我回答。
“哦?那你感到了什么?”
“嫉妒,”我说。“今晚或是明天,哪怕是后天,在他们来把你抓回到无论哪里你逃出来的地方之后,你依然会像现在一样虔诚地相信你所相信的现实。你确信你的公主在等你。你会花费你清醒的每一分钟去试图逃脱,试图回到巴松。你拥有信仰,希望和目标,它们令我印象深刻。我只希望我能拥有其中任何一样。”
“这并不难。”
“对于一位军阀来说或许是不难,但是对于一个有关节病和高血压的糟老头来说简直不可能,”我说着站起身。他好奇地看着我。“今晚我已经够疯狂了,”我对他说。“我要去睡觉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睡在沙发上,但如果我是你,我会在他们来找我之前离开。如果你去地下室,你会找到一些衣服和一双旧靴子,你可以拿走它们,你也可以从客厅的衣柜里拿走我的大衣。”
“感谢你的款待,”当我走上楼梯时他说。“我很抱歉让你记起了关于你的公主的痛苦回忆。”
“我珍爱我的回忆,”我回答。“只有现时是痛苦的。”
我爬上楼梯,在床上躺下,和衣而睡,在梦里我看到了丽萨还活着,并朝我微笑,我将这个梦作了整晚。
清晨,当我醒来并走下楼时,他已经离开了。一开始我以为他听取了我的建议赶在他的监管人之前离开了。但是当我望向窗外,我看到了他,就在他前夜所出现的地方。
他的手臂伸在胸前,面朝下倒在雪地里,好像新生的婴儿一样浑身赤裸。在我检查他的脉搏之前我就知道他已经死了。我希望我可以说他的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但是他不是,他看起来就和我第一次找到他时一样冰冷而痛苦。
我打电话给警察,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赶来并将他抬走了。他们告诉我,他们没有听说有疯子从当地精神病院逃跑。
上个星期我去找过他们几次。他们就是无法识别他的身份。任何地方都没有他的指纹和DNA的记录,他也不符合任何失踪人口的描述。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结束了对他的调查,但是没有人来认领尸体,他们最终将他埋葬了,他的墓碑上没有名字,和丽萨在同一所公墓。
一如从前,我每天探望丽萨的坟墓,也开始拜访约翰的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的想法变得疯狂,我无法甩开那些令人不安的念头,希望和可能的界限变得模糊,而我怨恨这些想法。更恰当的说,我怨恨他:他带着即将与他的公主相见的信念死去,而我却在永远都不能与我的公主的相见信念中活着。
我无法自拔地想,我们两个到底谁是那个精神健全的人?是那个以他信念的力量造就现实的人,还是那个因为缺乏勇气去创造一个新的现实而安逸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