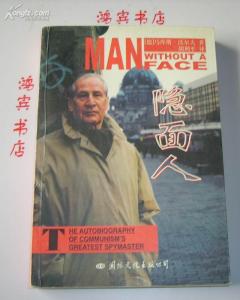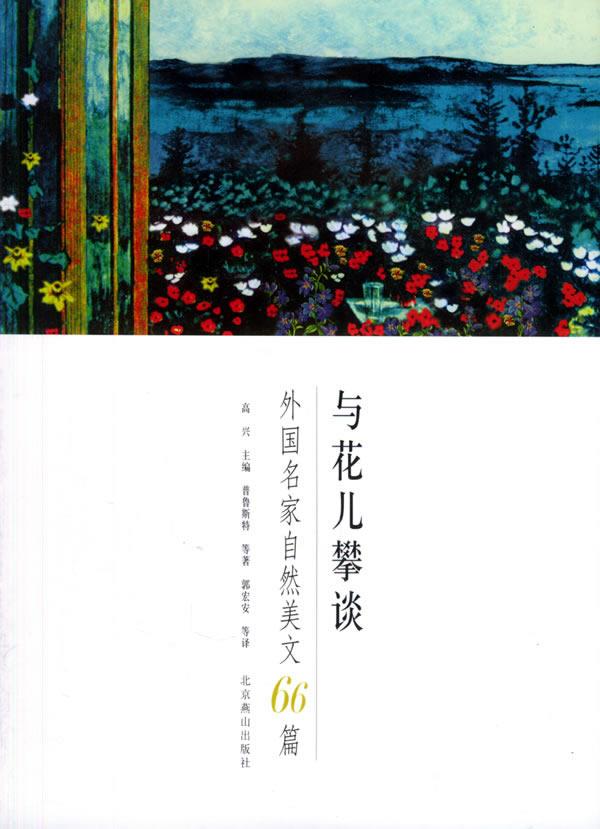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三辑)-第1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地方并不十全十美,因为某些器官是可以装配到人身上完全不同的孔穴中去的。看到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生物,还具有个人特征和自我意识时,那真令人极度兴奋啊!
我们这个复合物的新团体,每年有一次野餐,那是个高潮。
我们决定到汉福德那个废墟去。那里曾遭受过原子弹的轰炸,现在遍地长满野草,其形状和颜色可说是千奇百怪。我们这群人有二百来个,而且打算把组装这件事安排到午饭以后再进行。
女性后勤人员在分发食物,她们后面就是收费点。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力所能及的范围去交钱。我把一张西尼斯特的钞票丢进去,那是从一篇中篇故事的稿费中得来的。不少人过来围观这张钞票,啧啧赞叹之声四起,因为西尼斯特的钞票实在漂亮。尽管它厚得使你无法折叠,哪怕放在衣袋里也使腰包显得凸鼓鼓的。
一个参加过复合物组合活动的人过来看我那张西尼斯特钞票,他拿起来对着亮光仔细审视票子的形状和色彩。
“实在美不可言。”他说,“你想过把它挂到墙上去吗?”
“我只是才想到了这一点。”我说。
他想获得这张钞票,问我愿意用什么价格出让,我给他报的价格几乎是它兑换成美元的三倍那么多,但他欣然接受。
他仔细捏住钞票的一角,大嗅特嗅一番。
“真是不错。”他说。
现在我才认识到西尼斯特的钱的确有股香味。
“它们算得上是第一流的钞票。”我向他保证说。
他又把钞票闻了一下并问我:“你曾经吃过它们吗?”
我摇摇头,这种想法我可从来没出现过。
他一点一点地在钞票的角上啃咬并说:“真好吃!”
看到他吃得这么高兴也让我动了心,真想自己也尝上一口。不过现在这已经是他的钞票,我已经售出了。而我袋中的全是旧美元,淡而无味。
我翻遍口袋,西尼斯特钞票已被用得一张不剩,到家后就是想拿一张贴到墙上也没门,更别说去吃它了。
这时我注意到丽碧,她在角落那里全身蜷缩,看上去更加楚楚动人,于是我赶紧过去和她聚到一起。
《和我的猫咪一起去旅行》作者:迈克·雷斯尼克
我是在邻居家车库后面找到它的。他们退休后要搬到佛罗里达州去住。为了不用付太多去南方的海运费,他们决定处理掉一些东西。
当时我11岁。我本来是要找一本《泰山》,或者是克拉伦斯·马尔福德写的关于赫皮郎格·卡西迪的故事,或者(趁妈妈不注意)找一本妈妈不让我看的米基·史毕兰的小说。我也都找到了,不过现实却是;它们每本都要50美分,而我的身上只有一个5分的镍币。
没办法,我只好去找其他的书。最后发现,只有一本书我买得起:那就是《和我的猫咪一起去旅行》。作者是密斯·普里西拉·华莱士。
我翻看着它,希望书页中至少会藏一些半裸美女的照片。可惜里面没有任何图片,只有文字。
我觉得这本书对一个正想晚些时候通过少年棒球联赛选拔的男孩来说,也过于怪异、过于阴柔了:封面上有浮雕样凸起的文字,卷首及卷尾的页面用优雅的缎子做的封皮,书脊是黄褐色的天鹅绒做的,甚至里面还有一个用缎带粘合而成的书签。我正准备把它放回去时,它掉下来,翻开了一页。上面说,这是仅印的200本中的第121本。
这就让整个事情不同了。5分钱就可以真正拥有一本限量发行版本:为什么不呢?我把它带到车库前,老老实实付了钱。
那个晚上我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不想读一本叫《和我的猫咪一起去旅行》的书,更何况还是一个叫密斯的女人写的。可是我却为它付出了我最后的一个硬币,在下个星期以前我是不会再得到零用钱的。而其他的书我又看过太多遍了,都快翻烂了。
所以我不太积极地拿起它,读第一页,接着是第二页。突然,我感觉自己已经被传送到肯尼亚殖民地、暹罗或者亚马逊了。密斯·普里西拉·华莱士描述事物的本领让我希望我就在那,当我看完第一章时,我觉得我曾经就在那里。
当我40岁时。我最终准备承认在自己身上从未发生过什么不寻常或者让人兴奋的事:我曾经写了半本小说,不过我已经不再打算去把它写完。我花了20年时间想找一个可以爱的人,可是却没有找到。
我厌倦了城市的生活;厌倦了与那些总是和快乐成功相伴的人们为伍;不知为什么,快乐和成功总是躲避着我。我在中西部出生,长大,最后我搬到了威斯康星州北部的森林地区,这里有许多有着异国情调名字的小镇:马尼托沃克、明娜库洼、沃沙——当然同澳门、马拉喀以及普里西拉·华莱士书中所描述的其他一些首都还是大不相同的。
我在当地的一家周报做副编:就是那种让旅馆和房地产广告正确比让新闻报导中名字拼写正确更重要的工作。这不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不过它很安逸。就我来说,我也不打算找一个有挑战性的工作。年轻时对成功的追求已经随着年轻时对爱情的梦想和年轻时的激情一起消逝了。目前的日子,我很满足于宁静的生活。
我在一个无名的小湖边租了一幢小房子,离镇大约有15里远。不过它也不是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它有个老式的走廊。在走廊上有一个和房子一样古老的秋千。一个伸入湖中停放小船的码头,甚至还有最初主人用来饮马的饮马槽。这里没有空气调节器,不过我也并不真正需要它。
那是个晚夏的晚上,威斯康星州的空气中已经有了一丝寒意。我坐在空空的火炉边,读一本描写在柏林还是布拉格,或者是我从未去过的其他城市发生的激烈的枪战加追车。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在疑惑的是:这是不是就是我的未来(一个孤独的老人,夜晚坐在火炉边看通俗小说,或许腿上会盖一块毯子,唯一陪伴他的是一只虎斑猫……)
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想到虎斑猫——我记起了《和我的猫咪一起去旅行》,我从未拥有过一只猫,她却有两只,她去每个地方它们都陪着她。
我已经有好多年都想不起来这本书了。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还留着它,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我发现自己有一种找到它再读一读的冲动。
我跑去客房,那里堆放着所有搬来后还未拆封的东西。那里有大约两打装满书的箱子。我打开第一箱,接着找第二箱。我在寻找中,它出现了,就在那,像以前一样优雅,我唯一的一本限量发行版本的藏书。
接着,我打开它开始阅读。发现自己还和第一次一样入迷。它完全和我记忆中的一样奇妙。像30年前一样,我忘了时间看了个通宵,在太阳升起时读完了它。
那个早上我并没有太多的工作,我心里一直回想的是如此优美的描述和对世界的洞察力,现在已经不再有了。我开始怀疑普里西拉·华莱士是否还活着。她可能很老了,不过即使那样,我还是可以把那封信重新改改再寄出去。
午餐时间我顺便去了当地图书馆,想在那借回她写的别的书。书架上或是卡片目录中都找不到(它是个很温暖的古式风格的乡下图书馆,用计算机处理它的藏书恐怕要等到几十年后了)。
我回到办公室,用电脑搜索她。我找到了37个截然不同的普里西拉·华莱士:一位是出演低成本电影的女星;一位在乔治敦大学教书;一位在布拉迪斯拉发当外交官:一位疯狂养殖展览用狮子狗;一位是南卡罗莱纳州六胞胎的年轻妈妈;甚至还有一个是星期日连环漫画社的打字机。
正当我觉得电脑不可能找到她时,一行字显示在我的屏幕上。
华莱士,普里西拉。生于1892年,死于1926年。《和我的猫咪一起去旅行》的作者。
1926年,不管是在当时或者是现在我都无法寄信了:她在我出生前几十年就已经死了。虽然如此,我还是突然有了一种失落和怨恨的感觉:怨恨如此的人却在这样年轻时就死了。
那还有张照片。看来有点像是一张陈旧的深褐色锡版照片的复制品。一个苗条、有着赤褐色头发的年轻妇女,大大的黑眼睛。不知怎么,我总觉得眼睛里有点悲伤。或许是我自己有点悲伤,因为我知道她会在34岁时死去,而所有的生命激情也会随着死亡一起消散。我复制了一张拷贝放在书桌抽屉里,下班时把它带回了家。
那个晚上,在我加热吃下冷冻食品后。我坐在火炉边再次拿起《和我的猫咪一起去旅行》,随意翻看我喜欢的片段。上面有一处讲到逆着白雪蔼蔼的乞力马扎罗山庄严行进的一队大象;另一处讲到5月的早上当她穿过凡尔赛花园时那让人无法抵御的浓烈花香。然后,在书的结尾,是我最喜欢读的片段:还有这么多的地方要去看;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做。像这样的日子,我希望我可以永远的活着。让我感到欣慰和由衷相信的是:即使在我死了很久以后,只要还有人拿起任何一册书读它,我将会再次活着。
这真是个令人安慰的信仰。比我曾经追求的还要不朽。我没有在书上做记号,也不准备留任何记号让人知道我曾在这里生活过。在我死后20年,或许至多30年,就没人会知道我的存在:一个叫伊桑·欧文的人(我的名字)。
我灌了一大口啤酒,接着读。不知为什么,她描写的每个奇异的城市和原始森林,让我觉得不再奇异和原始,它们更像是家的一部分。每当我读的时候,我都怀疑她是怎样做到这点的。
走廊上的嗒嗒声吵得我心烦意乱。该死的浣熊变得越来越大胆了。可是接着我听到非常清晰的猫叫声。离我最近的邻居也在一里之外,对闲逛的猫来说那可是一大段距离。不过我想最少我可以出去看看,如果它戴有标牌,我可以给它的主人打个电话。否则的话,我也可以把它嘘走,免得它同当地浣熊发生麻烦而被伤害。
我打开门,走到走廊上。果真,这里有一只猫。一只小小的白猫,在它的头上和身上各有几处棕褐色的斑纹。我走近蹲下身想要抱起它。它却后退了几步。
“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轻声说。
“他知道的,”一个娇柔的声音回答道,“他只是有点害羞”。
我转过身:她就在那,坐在我走廊的秋千上。她打了个手势,猫咪穿过走廊,跳到她膝盖上。
今天早些时候我看过这张脸。这张脸曾在深褐色照片中凝视着我。我研究了她几个小时,直到我记得她的每个细节。
是她!
“真是个美丽的夜晚,是吗?”她说,而我只能张口结舌地看着她,“非常安静。鸟儿也睡了。”她停了一下,“只有蝉儿还没睡,在为我们唱着小夜曲。”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只是看着她,等她消失。
“你看起来很苍白。”片刻后她注意到了。
“你看起来很真实。”我最终发出嘶哑的声音。
“当然,”她微笑着,“我是真实的。”
“你是密斯·普里西拉·华莱士,我考虑你的时间太长了,我都产生幻觉了。”
“我看起来像幻觉吗?”
“我不知道,”我承认,“以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