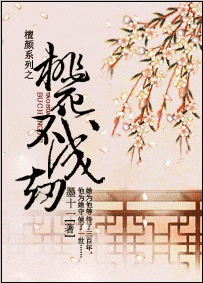不成交易-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嗯,”邦德喃喃道。
“你希望了解这个暗中对手的生平吗,或者,你已经知道了,佳克?”
邦德微笑着。“好吧,诺姆……”
“你以后不许叫我诺姆,否则,我就会捏造一个罪名把你送进布莱德威尔,那样就会把你驱逐出爱尔兰共和国,终生不得入境。”
“好吧,诺曼。我说说吧,马克西姆·安东·斯莫林,1946年出生于柏林,母亲是德国人,克里斯提娜·冯·格什曼,是和一个苏联将军结合的产物,他叫斯莫林,那时她给他当女仆。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齐·斯莫林。青年斯莫林继承了他父亲的姓,却继承了他母亲的国籍。他是在柏林和莫斯科受教育的。他只有几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这是你们的人,诺曼?”
“继续说。”
“他从一所很好的苏联学校参军了,我忘记了是哪一所学校。他可能进入了13军。不管怎样,他很年轻就被提拔了,然后被送到斯波齐纳兹训练中心,那是培养尖子的地方,如果你认为杀人尖子也是尖子的话。青年马克西姆受到邀请加入了苏联军事情报部最秘密的部队,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是进入军事情报部的唯一道路,它不像克格勃,如果你向克格勃提出请求,它们就会把你干掉。从那里开始,斯莫林通过一系列的升迁,又回到了东柏林。他回来的时候,是以东德情报局的高级外勤军官的身份回来的。
“我们的马克西姆可是个万能人物,他是为东德情报局工作的一群间谍中的一名隐蔽间谍,东德情报局必须和克格勃合作,他实际上是苏联军事情报部的一名成员,他一直还要顺便干点儿别的小活儿。”
“你完全掌握了这个人的情况。”穆雷冲他们微笑着。“你知道他们怎么评论苏联军事情报部吗?他们说,要加人军事情报部,你得交一个卢布,要退出来,你就得交两个卢布了。在爱尔兰,这几乎成了口头禅。要想当上军事情报部的军官,是相当难的。一旦进了他们的圈子,要想跳槽,那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实际上这里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去——钻进一个长匣子里。他们非常喜欢训练外国人,而斯莫林只是半个苏联人。他们说他在东德掌握了大权。甚至克格勃的人都怕他。”
“好了,诺曼?关于这个人,你还有什么新东西告诉我们吗?”邦德问道。
“你知道,佳克,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分裂的岛屿上,只有一个麻烦,南方和北方。他们都错了,我敢保证,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你的客人蛇怪在两天前就到达爱尔兰共和国了。现在,佳克,当我听到阿什福德城堡的惨案时,我想起来,在你们那边,已经出了两件这类的惨案,于是心里产生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咦,是吗?”
“关于你的‘苏联参谋总部情报委员会’,也就是苏联军事情报部,有些东西写得很中肯。这个家伙是军事情报部的叛逃者,名字叫苏维洛夫。他提到那些不想保持沉默的人,那些泄露机密的人。他写道:‘苏联军事情报部知道怎样把这些舌头割下来!’有意思吧,佳克?”
邦德点点头,表情严肃。研究情报史的学者往往不考虑苏联军事情报部,似乎它被克格勃吞没了。“苏联军事情报部完全被克格勃控制了。”一位作者坚持这种观点。另一位作者写道:“认为军事情报部是另一个独立的实体,那是纸上谈兵。”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军事情报部一直在奋力争取自己的独立身份。
“你呆呆地想什么呢?佳克?”穆雷自己在床上舒舒服服地坐好了。
“我只是在想军事情报部的精英人物要比克格勃的精英人物更多,也更凶狠。像斯莫林这样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做起事来毫无顾忌。”
“斯莫林就在这儿,佳克……”他停顿了一下,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换上了一幅严峻的表情,“可是我们漏掉了这个杂种,哦,请你再次原谅我的脏话,戴尔小姐。”
“阿灵顿,”海泽尔缺乏自信地咕哝着。邦德看出她的表情既紧张,又有些悲伤。
诺曼·穆雷举起手来,抖动着。“戴尔,瓦根,莎克,谁在乎这个呢?”他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伸胳臂。“已经是深夜了,我必须走了,我得回去睡觉。”
“把他放跑了?”邦德急切地问。
“他来了个金蝉脱壳,佳克。但是,斯莫林很善于脱逃,他简直就是胡迪尼。谈起胡迪尼,斯莫林可能并不是唯一在爱尔兰共和国脱逃的人呢。”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还让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脱逃了呢?”
“现在没有时间开玩笑,佳克。我们得到了一个小情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消息,可是这是一根可以看出风向的稻草。”
“你能抓住这根稻草?”
“如果那个消息是真的,你就不会抓这根稻草了,佳克。”
“啊?”邦德等着听他继续讲。
“消息说,有个比斯莫林职位高得多的人现在就在爱尔兰共和国。我不敢肯定,但是这个消息非常确切。那边从最高阶层派人来了。现在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然后我要向你们两位道晚安了。祝你们做个好梦。”他站起来,走到房间的角落里,拣起他的瓦尔特来。
“谢谢,诺曼。多谢了,”邦德说,送他走到门口。“我能问点事吗?”
“请便吧。我不收费。”
“你让斯莫林上校同志从眼皮底下溜了……”
“是的。而且我们再也没有闻到他的气味,如果说他还在这儿的话。”
“你一直在找他们吗?”
“当然,从一方面来说,我们还在找。佳克,你的人手不够吧。”
“如果你把他们中的一个堵住了,你打算怎么办?”
“把他装上飞机送回柏林。但是,这些家伙将会在奥威尔路那个罪恶巢穴里躲避起来。 你知道,那个地方在屋顶上就有大约600个天线和电子抛物面反射镜。这有些讽刺意味是不是?苏联人在奥威尔路设立他们的大使馆,在屋顶上安装了许许多多通讯设备。你们的人就可能藏在那儿。”
“现在他不在那儿吧?”
“我怎么知道呢,啊?我可不是我弟弟的保姆。”
他们从格拉夫顿大街走进了圣斯提芬的格林大街,海泽尔提着她从斯维茨尔和布朗·托马斯商店买来的臃肿的旅行袋。邦德跟在她后面走,在稍微靠左侧的地方,和她相差两步。他提着一个小包裹,拿枪的那只手悬在那件没有扣上纽扣的夹克衫前面。自从诺曼·穆雷离开旅馆后,他就越来越感到事情的发展让人很不放心。海泽尔对他没有告诉她艾比还活着,感到很恼怒。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我对她是什么感情。你知道她还活着……”
“我知道她可能还活着。”
“你居然不告诉我?”
“因为我没有把握,而且,因为你们以前的‘奶油蛋糕’行动,从一开始给我的印象就是个临时凑合的行动。现在它依然是个临时凑合的行动。”
他停了下来,不想再多说什么,因为他的幽默感很快就被磨得残破不全了。从理论上讲,“奶油蛋糕”行动是个好行动,但是,如果海泽尔是五个被选出来执行这行动的年轻人中的佼佼者,那么,这个行动的策划者可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那时绝对没有时间充分训练他们。然而对他们父母的情况,却做了充分考虑。
邦德的大脑中反复地出现他们的名字,就像一架留声机总是在绕着一条纹路旋转:弗朗兹·特劳本和艾丽·祖克尔曼,两人都死了,脑壳被打碎了,舌头也被齐根割去了;弗朗茨·贝尔辛格,他喜欢人家叫他瓦尔德;艾尔玛·瓦根,她本人;艾密里·尼古拉斯,她可能在罗斯莱尔旅馆。他反问自己,为什么弗朗茨喜欢他的外号:瓦尔德。他自言自语地说,不行,他必须用他们的英语名字来思考他们,尽管他们已经做了很多掩饰。他必须想想死去的布里奇特和米里森特,还有活着的海泽尔和艾比,还有可能活着的京格尔·白斯里。
就在他思考着这五个人物的时候,邦德也想到一些黑色人物,特别是马克西姆·斯莫林,他曾经多次在布满斑点、模糊不清的侦查照片上,在急速跳动的影片中看到过他,通过光纤镜头,他已经变形了。邦德亲眼看他只有一次,那是他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富凯大厦出来时看到的。邦德和另一位军官正在人行道旁的一家咖啡店里坐着,尽管隔着一条宽阔的大街,还有车水马龙的纷扰,斯莫林矮小的身材,健壮的体格,带有军人气质的身形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是他自己要表现得像个职业军人似的那副样子给邦德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但是,他表现得太过分了;也可能是他的相貌,那双眼睛从来没有平静,他那两只手,一只握紧拳头,另一只手的手掌就像一把刚硬的刀刃。看起来斯莫林仿佛在放射着能量,而且是一种邪恶的能量。
这第七个人物,“比斯莫林职位高得多的人物”,诺曼·穆雷没有说出他的名字,给整个事情投下了更加浓重的阴影。
邦德把自己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他看到雨已经停了,空中还有一股凉气,在屋顶上,一朵朵蓝青色的烟云在互相追逐。他们停下来等红绿灯,邦德看到长着黑胡子,头发乱蓬蓬的大个子迈克·闪把握着酱紫色的沃尔沃的方向盘。这个爱尔兰人装作没看见的样子,但是邦德知道他已经认出停在那儿的那辆汽车了,也看到了他和海泽尔正在等红绿灯。他们看见绿灯亮了,便穿过马路,放慢了脚步。他已经告诉海泽尔不要慌张。
“这和你点燃爆炸物的导火索时采用的程序一样。慢慢走。绝对不要跑。”
她点点头。她显然知道有关爆炸的一些事,受过野外训练,他估计是这样。在他们到罗斯莱尔的途中,他要一件一件弄清楚。
他们没有穿过格林大街,而是沿着北侧悠闲地漫步,向东面停着汽车的地方走去。就在他们走到和舍尔邦尼旅馆处在同一水平线的时候,邦德几乎僵住了。邦德朝那赫赫有名的旅馆瞥了一眼,他第二次亲自看到了马克西姆·斯莫林上校清晰、坚实的身影,旁边还有两个身材矮小、块头很足的男人。三个人正从台阶上走下来,朝左右两面张望,仿佛在等车。
“不要朝舍尔邦尼那边看,”邦德压低了声音喃喃说道。“别看,海泽尔,不要看,”他反复说着,在她做出反应的时候,加快了脚步。“继续向前走。你原来的情人从窝里爬出来了。”
第七节 车祸
逃跑根本不可能。无论她穿着衣服,还是不穿衣服,斯莫林都能认出海泽尔,邦德知道,斯莫林也能认出自己。他的照片毕竟被人收进了世界各地几乎每个情报机关的档案。他的全部希望就在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就在斯莫林的注意力显然集中在他们自己的车子上,因此,他可能没看到他们。但是,他知道这样的机会很渺茫。斯莫林是训练有素的,他能从上千人中找出最不熟悉的面孔来。
邦德轻轻扶着海泽尔的手臂,引着她转过了拐角,在他们向那辆汽车走去时,几乎让人觉察不出地加快了脚步。
他感觉到脖颈后面有一种熟悉的、令人难受的刺痛——仿佛有十几只可以致人死命的小蜘蛛在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