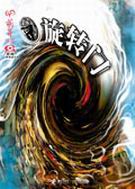旋转的螺丝钉 作者:[英] 理查德·伯顿-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他很悲伤地摇摇头:“什么也没发现。”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欣喜若狂。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他悲哀地重复着。
我吻了一下他的额头……他的额头都湿了。“那你怎么处理那封信?”
“我把它烧了。”
“烧了?”我不失时机地追问道,“这就是你在学校时做的事?”
噢,这究竟引来了什么!“在学校?”
“你拿信?……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
“其他的东西?”他好像在想一些遥远的事情,只有在焦急的重压下才能想起来。但他想到了:“我偷东西吗?”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好像不该问一个绅士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你不能回学校的原因?”
他的反应有点儿让人吃惊:“你知道我不能回学校了?”
“我什么都清楚。”
听到这儿,他久久地、奇怪地盯着我看:“每一件事?”
“一切。因此你……”但我无法再重复。
迈尔斯却可以很轻松地做到:“不,我没有偷东西。”
我的表情肯定告诉他,我相信他的话。但我的手……只是出于纯粹的爱怜……摇晃着他,好像在问为什么,好像我被他莫名地折磨了几个月。“那么,你到底干什么了?”
他神情痛苦地环顾整个房顶,不时深呼吸几下,好像很难受。他好像正站在海底,看着微弱的曙光。“好吧……我说了一些事。”
“只有这么多?”
“他们认为这已足够了!”
“把你开除?”
从没一个人像这个小男孩儿一样这么容易地被开除掉,而且没有辩白的机会!他好像在衡量我的问题,但思维分散,很无助。“啊,我认为我不该被开除。”
“那你对谁提起过他们了?”
他在努力回忆,但失败了。“我不知道!”
他几乎因投降而悲哀地对我笑着,这种悲哀是那么清晰可见,我本应该就此打住,但我入迷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这让他更孤独。“是不是对每个人都说了?”我问。
“不,只是对……”但他好像有点儿头疼,“我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
“人很多么?”
“不……只有几个。我喜欢的几个人。”
他喜欢的几个人?我这时不是更清醒,而是更迷惑了。我很快意识到他可能是清白的。我一时心中没底,很困惑,因为如果他是清白的,那我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骤然而至的问题让我有点儿麻木,我松开了他,因此他重重地叹息一声又背对着我。当他看着明亮的窗户时,我很痛苦,觉得没什么好隐瞒他了。“他们向别人重复你的话了吗?”过了一会儿我又接着问。
他很快走了几步,离我远点儿,呼吸仍很急促,虽然没有恼怒,但很明显在压抑自己。他又看了看灰蒙蒙的天,满脸焦虑。“哦,是的,”他回答道,“他们肯定向别人重复了我的话。向他们喜欢的人。”他又说道。
我反复想了想:“然后,这些事就传到了……”
“传到校长耳朵里?哦,是的!”他简单地回答道,“但我不知道他们会说。”
“对校长说?他们没有……从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问你的原因。”
他把自己那张发烫的小脸又对着我:“是的,事情发展得太糟糕了。”
“太糟糕?”
“我想,有时候我说,往家写信。”
由这样一个演讲者来发表这样一个演讲,让我有莫名的痛苦。我威严地说:“一派胡言!”
接下来,我又更严厉地问道:“到底是什么事?”
我的严厉让他又转过身,但他转身的动作让我一跃而起,我失声大叫,朝他直接跳去……因为玻璃上又出现了那张煞白的脸,好像要阻止他回答。我感到自己的胜利已蒙上了一层阴影,所有的战斗将一无所获。我猛烈的前跳出卖了我。我看到他在我跳的过程中看到了某种预示,我必须驱散他的恐惧。“别再看了,别再看了!”我尖叫着,尽力把他搂在怀里。
“她在这儿吗?”迈尔斯喘着气,闭着眼把头转向我说话的方向。他奇怪地说出“她”,这让我步伐不稳,我喘着气回应道:“耶塞尔小姐,耶塞尔小姐!”他突然愤怒地背对着我。
我被他的猜测……我们对弗洛拉所做的一切的后果……惊呆了,但我想让他明白会更好。“不是耶塞尔小姐!但他就在窗外……就在我们面前。在那儿……懦夫,最后一次了!”他的头好像狗闻到什么气味一样摇摆着,他愤怒地瞪着我,整个屋子充满了毒药味。“是他?”
我决定不顾一切地挑战他:“你说的’他‘是谁?”
“彼得·昆特……你这个魔鬼!”他又环顾整个屋子哀求地说,“他在哪儿?”
这个名字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现在又能怎么样,亲爱的?他又会怎么样?我拥有你。”我对着他开火了,“但他却永远地失去了你!”
然后,为了证实,我对迈尔斯说:“在那儿,在那儿!”
他马上愤怒地跑开了,却只看到平静的天空。我骄傲地听到人面临深渊时的哀号,在他下坠时,我及时抓住了他。我抓住他了,是的,抓住了……那种激情可想而知。但我慢慢感受到我到底抓住了什么。平静的日子,我们俩单独待在一起,他那小小的、无依靠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瓦提克》 序言
威廉·贝克福德,生于1760年,即乔治三世即位的那一年,他是两次当选伦敦市长的一个市政议员的儿子。他祖籍格罗斯特郡,他的家族由于在牙买加经营种植园而发达;他的父亲被送进英格兰的学校学习,在威斯敏斯特与曼斯菲尔德勋爵结下了校友之谊,继承了家族在西印度巨大的财富后,开始了经商生涯。老威廉·贝克福德历任地方官员、国会议员和市政议员。在小威廉·贝克福德出生的四年前,他当上了伦敦的治安官,儿子出生三年后,他坐上了伦敦市长的位置。在任期间,他经常摆设豪华的晚宴,开创了宴请宾客的新纪元。
著名的小说《瓦提克》似乎是市政议员在华府饱餐一顿之后所做的一个梦。故事里提到了对感官刺激的沉迷,尤其强调暴食。瓦提克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大的食客,但是,当印度人和他一同进餐时,尽管桌面已经换了30次,食量巨大的客人仍然没有吃饱。还有渴:在梦中,当瓦提克的母亲、妻子和宦官们不辞辛苦地把盛满清水的无色水晶碗竞相端到他面前时,结果经常是瓦提克对水的渴望超过了对他们的热情,以至于他只顾匍匐在地,趴在水面上喝个不停。这个阿拉伯童话就在这样一个恐怖的场景中达到了高潮。这个孩子是否是在一次华府的盛宴之后产生了写《瓦提克》的想法呢?
老贝克福德是一个奢侈的好客主人,但他并不暴饮暴食。在1763年第一次就任市长的那一年,贝克福德支持维尔克斯市政议员,由于北大不列颠45号决议而受到攻击。由于广受拥戴,贝克福德再次当选市长。1770年5月23日,他走在市政议员和侍从们的最前面,觐见国王乔治三世,他觐献了致辞,而国王对此非常冷淡。
那时,小贝克福德……《瓦提克》的作者,不过是一个不到11岁的男孩儿,家里的独生子。3年后,父亲去世了,给他留下了10万英镑的年薪收入和100万英镑的现金遗产。
在他还小的时候,小贝克福德的母亲就给他请了私人教师,他的母亲是第六世阿波肯伯爵的孙女。莫扎特教他音乐;钱森姆伯爵曾经是他父亲的朋友,他觉得这个孩子很有想像力,因而他建议目前让他别碰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很幸运,她没有这么做,瓦提克给《一千零一夜》续上了第一千零二个童话故事。不同的是,他在东方的奇思妙想里融入了顽皮的夸张手法,而这只能出自英国幽默作家之手,他们时常会嘲笑自己创作的故事,不介意把自己滑稽的一面展示给读者。小贝克福德出生在维尔特郡芬希尔修道院的乡间宅邸。17岁时,他看了漫画《书画名家史》,很感兴趣,他鼓动芬希尔的管家给客人们展出奥格、
巴赞和其他一些名家的卡通作品。
小贝克福德在日内瓦接受了一年半的教育。之后,他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旅游,就是在那个时刻,他开始对写作感兴趣。22岁的时候,法文版的《瓦提克》被一气呵成。他非常投入,写作持续了三天两夜。1784年,在没有征得作者许可的情况下,一个无名氏出版了英文版的《瓦提克》。贝克福德在巴黎和洛桑于1787年发表了自己的作品,那时,他结婚三年的妻子刚刚去世一年,给他留下了两个女儿。
贝克福德去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返回法国,经历了巴士底狱革命风暴。他经常出国;他买下了洛桑的吉本图书馆,把自己关在图书馆中,想读遍藏书。他偶尔会去国会,但觉得没有什么兴趣。他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但是都不如《瓦提克》有趣,其中包括两部根据当时的伤感小说改编的滑稽喜剧。1796年,他在芬希尔定居下来。或许,他想到了瓦提克的高塔,他雇用工匠们夜以继日地为他建造一座300英尺高的高塔;高塔倒塌后,他又安排工匠们重建。据说他在芬希尔花费了25万英镑,在那里与世隔绝地度过了自己最后的20年,终老于1844年。
威廉·贝克福德生命中快乐的主题就是《瓦提克》。这个故事描绘的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外部世界的真实面目,而是以快乐活泼的笔触再现了一个想像力丰富、情节跌宕起伏的阿拉伯神话故事。在这个放纵的哈里发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故事中有一个道义魔鬼,这在作者对艾比利斯大殿的剧尾介绍中有较为详尽的描述。但是这本书带给读者的乐趣反映了作者写作这本书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作者怀着极度的热忱一气呵成此书。他纵情驰骋在活泼生动、充满生机的幻想世界,如痴如醉地刻画了没有尽到母亲责任的“恶毒母后”的累累罪行。当然,他在写这个梦魇神话部分章节的时候也是带着设计舞剧般的兴奋的。
无论是谁,如果他一本正经地来读《瓦提克》,他就和作者的原意多少有些背离了。我们必须留意那些时不时流露出来的讽刺意味,它让我们在感受东方夸张写作手法的同时发出会心的微笑,东方的夸张手法总是强调对众多故事情节和冲突的精雕细刻。严肃地讲,这本书有结构上的瑕疵,但是,当我们感受到作者的眼神的时候,这些瑕疵就化做了美丽。
第一章
瓦提克……阿卜赛兹皇室的第九代哈里发,是穆塔塞姆的儿子,哈若·艾尔·莱斯奇德的孙子。瓦提克很小的时候就登基即位了,加之他聪慧过人,臣民们都相信他的天下必将长治久安。他身材匀称威武,但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一只眼睛会变得非常阴森恐怖,没有人敢正视它,如果谁很倒霉地让它盯上一眼,就会马上倒地,有时就死过去了。由于皇宫里人影稀疏,瓦提克担心国民会越来越少,因而很少发火。
由于沉迷于声色犬马,他以自己的和善来获取一些追随者;他越是宽厚,越是放纵自我,他的追随者也就越多,因为他绝不谨小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