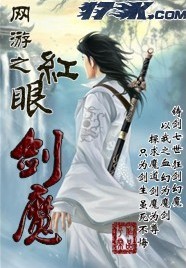柳残阳眨眼剑-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擦去满是酒气的秽物,气怒已极的说道:“不教训教训你丫头,谅你也不晓得大爷‘地头
蛇’金中枢的厉害!”
但明敏秀此刻已是昏迷过去,烂醉如泥,娇躯软绵绵的瘫在邵真的怀抱里。
邵真一手揽住她的腰子,微微一提,放至肩肿上,缓缓走出厢席……
这时,所有的食客都放下杯管,静待好戏上演……
“这位大爷,可容在下道个歉么?”微微抱了一拳,邵真皮笑肉不笑的道。
“道歉?值几文钱?”
怒目瞠睁,金中枢气焰凌盛的说道:“大爷今天非教训你这无知小辈不可!”
说罢,暴喝一声,抡起斗大的拳头,毫不容情的便朝邵真的面门砸下!
“放肆了!”
眼皮眨也不眨的,轻蔑而又显得狂傲的嗤了一声,邵真像是无动于衷对方的一拳,眼看
那碗大拳头差两寸便击在他的天灵盖上,这才轻描淡写的,看起来是如此不经意的抬起左
脚。
那只穿着长统紫色绸缎粉底鞋的左脚,抬起速度是如此的快速!抬起的劲道是如此狠
沉!
即使是一点点躲闪的念头也没有,那中年大汉,“地头蛇”金中枢忽然张口惨叫一声!
嗯,他的小腹,非常结实的挨上了那一脚。
噎噎噎!一连退了三个大步,叭的一声,一屁股跌坐了下去!哇的一声,金中枢按捺不
住的吐出了一道鲜艳刺目的血水,喷得好远,好高,离他两尺远的一个屏风,被洒上斑斑的
红影,加上屏风上原本的图案,煞是美观。
也许是角度的问题,也可能是邵真那双脚“抬”得太快太快了,以致于所有的食客竟然
没有一个知道金中枢是如何跌坐下去的,仿佛,仿佛他在人们的意识里,他便一直坐在那里
似的。痛苦的呻吟了一声,金中枢试图使自己站起来,但他失败了,屁股不过刚抬起,随即
略的一声,“粘”了回去,仿佛是生了根似的,坐着不动了。
那张脸,黑得像炭头的脸,不住的曲扭抽搐着;浓黑的眉,几乎要挤在一齐了,睁得如
葡萄大的牛眼,写明了大多的痛苦,痛苦……
全场上,一片鸦雀无声,好静哟,静得连根针落地的声音也要变成铭然作响。
过了好一会,也就刚回过了神,食客中有两名汉子走了前来,看样子他们是与金中枢同
一路子的,其中一人背负起地上的金中枢,另外一人步至邵真前面,微微抱了一拳,挑了挑
浓眉说道:“这位兄台请了,区区乃‘金家庄’之人,承蒙兄台结架,还望报个万字,以让
本人有所回报。”
潇洒的笑了笑,邵真昂然回道:“不才乃武林末屑,无名小辈也,何堪一提?不说也
罢。”脸色微微一变,说道:“阁下不嫌虎头蛇尾么?”
耸了一下肩,邵真道:“阁下何不用汝之招子瞧清少爷之相貌,身影,不就得了么?”
咬着牙,来人怒目打量着邵真,冷声说道:“山不转路转.咱后会有期!”
“不送了。”像是有那么一回事的拱了一下手,邵真揶揄的说道。
狠狠注视了一会,来人转过身子,朝四周打了一揖,朗声说道:“有找各位雅兴,失礼
了!”说毕,又是一揖,与另一名汉子匆匆下楼去……
柳残阳《眨眼剑》
第 三 章
撇撇唇角,邵真也作揖说道:“在下鲁莽,扰断诸位雅兴,还望见惊!”说罢,招呼了
一名伙计,往客房里走去,房里头布置得甚是堂皇富丽,邵真把醉得已是不知人事的明敏秀
放置于床上,然后像是一个多情而又体贴的丈夫,为她除去了绣花粉鞋,洗涤了她身上所沾
的菜汤秽物……
默默的,邵真忍住心头的苦痛,他不怪她,任何人也要受不了的,是不?世上哪有比能
爱而又不能得到爱的痛苦更痛苦?明敏秀有权这样做的,虽然借酒浇愁愁更愁是一件迹近无
谓的举动。
拧干了毛巾,邵真看来是那么爱意不舍的拭着明敏秀唇角的酒渍……
呃——哇!
忽然,明敏秀又哇了一声,吐出了一大堆酒气冲天的秽物!
邵真根本没想到她仍会呕吐,竟也闪避不及,和方才那位‘地头蛇’金中枢老兄一样,
被喷了个满头满脸!
邵真本身也饮了不少的酒,一闻到那浓烈的酒味,肚里一阵翻腾,差点没跟着一起呕吐
起来,连忙擦干净了脸上的秽物,邵真步到窗旁,启开窗子,透透清凉的空气……
明敏秀确实是喝得太多了,一连又呕了好几次,呕了满身,满地,即连床上也吐了一大
堆。
邵真让她吐了一个痛快,直至明敏秀把胃里的东西吐得一干二净,这才又走前去。
邵真重新擦着毛巾,把床上,地上的脏秽物擦洗干净。
并开始为明敏擦拭衣服……
似乎是感到好受些,明敏秀一连打一两个空呢,缓缓睁开眼睫。
明敏秀只感到两颊仍烫烫的,体内如有一团火在燃烧着,烧得她四肢无力,烧得她全身
难受…
喉中干渴,使她忍不住的嗯哼着,她迫切的感到需要水,水,而邵真那么适时的,那么
体贴的把一杯冷开水送至她的唇边。
明敏秀宛如沙漠里行走多日的旅人一样,一口气喝了三大杯,将近半壶的水,这才吁了
一声,满足似的擦了擦唇角的水渍。
幽幽的,明敏秀把眼中的那股幽怨,完完全全的,毫不保留的投向邵真,说道:“真,
劳累你了”。
“朋友之间,守望相助乃是应当之事。”淡淡的笑了笑,邵真回道。
无奈的垂下了微显蓬乱的螓首,明敏秀苦楚的说道:“求你,别再说朋友两字,好不?”
一颗心在微微颤栗着,转过了身子,邵真咬着牙说道:“何不保留着原有的坚强?我们
这样子,不是很好么?
抬起了脸孔,可以看到眸里泛着一层泪光,是那么的哀伤,那么地无助;明敏秀痛苦的
道:“坚强?为啥不说是委屈呢?三年来,这千多个日子,我们委屈够了!我们为什么不愿
坦认我们在相……”
“不要说了”!
像是要逃避毒蛇的噬咬,邵真猛可地转过身子,打断了明敏秀摇撼他心灵的话,但他一
接触明敏秀那哀恨欲绝的眸子,像是承受不住的又转身过去。
是的,他一直不愿意把他们的相爱表示出来,不!他是愿意的!他恨不得能一把抱住明
敏秀,对她大声说一千万个,一万万个的爱你!爱你,然而“爱”是如此简单么?它必须具
有主观与客观的条件,他知道,他们的主观条件——彼此深深的相爱着,是无可置疑的;可
是,那他一直不愿也不敢去想的“客观条件”的压力,已超过了他们的主观条件!
三年了——从他第一眼见到她到现在,他就一直在想:怎么办呵?
这事,迟早是要有个答案的,但他并不认为是现在。
“敏,今晚我们都太激动了。”努力平息心中的波动,邵真竭力使自己的声调保持最大
的平稳!
“或许,会有那么一天,勇气与胆量会从我们身上出现!
只是,我们必须等待,等待,是么?三年漫长的光阴我们都熬过去了!”
话音一落,人已走到门边,邵真转过头说道:“好好休息,二更之时,我会来唤你。”
说罢即步出门外,把房门反扣上。
用力的吁了一口气,但并未此就能消除邵真心头的郁闷,邵真懒散的走着,显得有些无
精打采,已经喝够了,架,也打了,虽然打得并不够味,但也总算出出心里的乌气,更何况
再过几个时辰便有一场大架可打了,届时即可大大舒出心头的闷气啦。
可是,这段时间如何打发?睡觉?心里太闷,不可能睡得着,那末——噢,当然是找点
刺激的玩意了——豪赌,或者是找个漂亮的妓女泡她一泡。
赌,当然是一件富有刺激与极高“娱乐”的性质的事,他想自己很可能是上瘾了,总觉
得来到这种地方没赌他一番,像是和自己过不去似的。
女人,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男人不愿尝尝销魂蚀骨之乐?当然除了那种心里变态者是
生理上有问题的“蜡头男人”,自是另当别论。
邵真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玩女人,好像是两年前一个满月的夜晚吧,他实在抵受不
了心里的压迫,和克制不了生理上的需要。
他否认当初的动机是为了“肉欲”,而是为了要驱迫明敏秀离开自己。
自己既然无法离开她,只好使明敏秀离开自己了。
明敏秀既然深爱着自己,那么自己在她心中定是完美无缺,至少离她的“理想”并不会
太远。
无可否认的,大凡女人最憎恶她的男人另寻他欢,只要是“正常”的女人,即使再量大,
也要忍受不了的。
邵真的动机与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明敏秀对他的反感。
可是没有,明敏秀并未就此离开邵真,依然是那么地不在乎,那么地洒脱。
反而邵真在偷食“禁果”之后,竟食髓知味,染上了江湖人物的风流通病。
走出了房间的通道,邵真又来到嚣声盈耳的厅堂,但他没有停步,转向左侧的一个大厅
——赌园。
赌园,名字并不雅,事实上赌本身就不是一件太高雅的事情,它可使一个人的意志消沉,
它可使一个人身败名裂,它可使一个人倾家荡产……总之,赌有百害而无一益,如果说有益
的话,那便是赢钱,但赢钱的机会似乎并不会大多,是吗?否则个个是赢家,哪个又是输家
呢?
邵真已打定主意,先赌他一个痛快,然后找一个标致的女人解解闷,再到“金银帮”挑
脑袋去。
走进赌园,放眼一片黑压压人影。
不过人众虽多,但大抵都是王孙公子,富商巨贾,当然也会有些亡命之徒,但一般说来
他们都是亡命的很“高雅”,最低限度,他们的口袋还算是鼓鼓的。
一进去,邵真便被此起彼落呼吆喊六的声音罩住。
赌园里分成好几部,有丢骰子的,有摸牌九的,有下棋的……
秩序当然不能说好,不过一般说来,还像差强人意,赌徒差不多都是身份极高的人,并
不含有太多猥亵不堪入耳的粗话,不过江湖术语倒是充耳不绝。
赌徒有老的,年轻的,有男的,有女的,有的一面抽水烟下赌注,或是品着黄汤抓牌,
是以满室烟雾弥漫,酒气味扑鼻……好一个“乐园”呵。
赌园里是洛阳客栈里唯一没有时间限制的一个部门,它没有开市与打烊的分别,随时去,
随时客满。
赌徒是永不会停歇的水源,一班去,一班来,永远是川流不息,看不出有停顿的可能。
有水便有鱼,有山便有兽,而赌窟与淫巢的“附产品”便是不学无术的登徒子,他们以
保镖的姿态镇守着洛阳客栈,其间不乏各地浪人与亡命之徒……。
邵真的介入,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里的人虽不是三头六臂,但堪称头角峥嵘,大
有来头,谁又会去注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邵真走到一个像楼下掌柜的柜台边,从怀中取出一叠“飞钱”。(笔者按:飞钱乃是吾
国最早之纸钱,其之功用,或可比拟当今之汇票。)
邵真抽了一张三千两银的票额,递给掌柜说道:“悉数换码子,上码。”
码子即相当现在的筹码,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