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达尔文的阴谋 (全本)作者:[美] 约翰·丹顿-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菲茨洛伊和其他人都没有留心他这番话,而查理却记在了心里,并飞快地看了一圈——坐在另一边的麦考密克正回头看着他,好像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也许还在发掘它的意义。
下午大家划船去了詹姆斯岛。查理想更多地收集些鸟的标本。它们看起来也像监狱长说的那样:每一座岛屿,它们都有些细微的不同,像是以此来适应不同的栖息地。查理每到一处岛屿,就射下几只鸟——尤其是那些雀科鸣鸟——制成标本,贴上标签,做详细的记录。像往常一样,这天下午,考文顿也跟他在一起,两人独自在外面办事。
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查理感觉有点眩晕。他们走进一片灌木丛里,发现了许多地雀和嘲鸦正在树丛中飞来飞去。用枪是没有必要了。因为他们发现,只要拿根树枝,再弄点嘘声,就能引来一只雀鸟停在树枝上,然后抓住它。
当看到一只不寻常的黄色地雀时,查理独自追了上去,在树丛中蹒跚而行,追赶着那只小鸟。突然他的脚碰上了什么硬硬的东西,他低头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那儿,从一片落叶中,露出一个人的头颅骨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他觉着一阵作呕,赶快扶住一棵树。然后他慢慢蹲下身来把他从土里挖出来。接着他把它拿在手上,不断翻转。这既令人作呕又让人无法拒绝——那白色的颅顶,太阳穴附近锯齿状的裂缝,腐烂后的牙齿像是在怪笑,口腔和两个鼻孔组成一个黑三角,在舌头的位置还有一窝蛆在蠕动。
他再一次感到一阵眩晕。太阳正在炙烤着大地。他仔细听了听,到处都是昆虫的声音,它们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嗡嗡叫着,还不断摩擦着翅膀,撞得树叶咯吱咯吱响。他还听到海鸟俯冲进海水捕鱼的声音和髯鳞蜥咀嚼藻类的声音。恐惧攫住了他的心,这是他以前从未感受过的。一时间,滚烫的火山熔岩,可怕的蜥蜴,被宰杀的巨龟,头颅骨和蛆虫充满脑际,这是一个可怕的生与死的循环,无休无止地重复着,没有意义,而他则是这个循环的囚犯,大自然是万物的主宰——可憎而又凶暴。
麦考密克出现了,看见查理还拿着那个头骸。
“我想,这肯定是监狱长故事里曾经提及的那艘船的船长,”他说,“可能是他的船员造反了,把他残杀在这个岛上。”
考文顿也来了,“我们拿它怎么办?”他问道,“把它加入我们的收藏吗?”
查理对这个建议表示惊恐,他吩咐考文顿挖了个坑,以基督教的仪式把它埋葬了。
晚上查理给胡克写了封信,他没有提头颅骨的事,不过他以一句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结尾:魔鬼的信徒究竟要把大自然那笨拙、费力、误事而又冷酷可怕的杰作描述成什么样子呢!
3天后,船在忘忧岛下了锚。天气很好,很暖和,吹着柔和的西风,很适宜打猎。查理很想去收集水下生物标本。麦考密克突然来了热情,说他也想去。于是两人和沙利文上尉还有菲利普·吉德利·金一起坐小船出发了。
他们找到一个停船的好地方,又潜了几个小时的水,还留了一个人在船上作救生员,因为没人对自己的游泳技术充满信心。中午时分,他们已经收集了各种各样的鱼、螃蟹、海草等东西,然后到岸上吃午饭。海滩上成排的海狮,在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对他们这些两条腿的生物毫不感兴趣。查理用火点了一堆火,他们用酒把鱼冲了一下,然后就烤了来吃。饭后,金和沙利文稍作休息,查理和麦考密克继续上船去搜集猎物。
两人一直沿着岸边划,找到了一个芦苇环绕的淡水湖。麦考密克站在船头上望着,说是个不错的地方,并说要留在船上。查理跳进湖里,潜了一会儿,露出水面时带着些贝壳和其他宝贝。每次麦考密克都向下看看,然后示意他往更远的地方再找。
查理浮在水面上,朝水下看去。这时他看到水下有个阴影在迅速地移动,尾巴掀起阵阵涟漪。接着是另一个,然后又一个。湖水被这些黑影搅动起来。他伸出头,吸了口气,接着又钻进水里去看个究竟。现在他看清楚了,银灰色的皮肤,尖锐的鳍和尾巴,有五六英尺长——是鲨鱼。共有4头,不,还有。它们在水中轻快地滑行,围成一个圈子,飞快而冷静地寻找着食物。查理贴着水面,游回小船。麦考密克抓着他的前臂,用绳子把他拽上了船。
查理坐在船板上,心还在怦怦狂跳。他看着麦考密克,血压持续攀高。麦考密克有点沮丧,唧唧咕咕地说:“感谢上帝,你没出意外。我大声地叫喊,警告你,可你听不见。”
查理只是简单地说:“咱们离开这个地方吧!”
麦考密克朝海滩划去。查理浑身颤抖,回头望着那片自己差点儿送命的水面,心里还在想着能否看见些小鱼浮上水面,也许可作为他们的午餐——当然是鲨鱼吃剩下的。
《达尔文的阴谋》作者:'美' 约翰·丹顿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二十章
松嫩贝格诊所
苏黎贝格
苏黎世,瑞士
1872年5月10日
亲爱的玛丽·安:
谢谢你的问候,我的回答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惨。我在世上孤单一人,为家人所鄙视,被自己所爱的男人出卖——这些都发生在我头上。我想,我已经为自己的罪过受到足够的惩罚了。但是,现在这最后的惩罚,每个女人都要忍受的巨大痛苦……真是难以形容啊!说真的,玛丽·安,说起这些,我的头都快炸了。
坐在诊所的走廊里,我感到一种无边的绝望。没人能帮我,我畏缩在这个令人孤独的地方。鲜花在草丛中摆动,蓝色的湖面,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这本来应是个安慰人心的好地方,而对于我却毫无作用。想着我的遭遇,心里更觉难以承受。
我犹豫不决地把这件悲惨的事写进信里,希望袒露心扉能对自己的痛楚有所帮助。有一些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痴情,我的爱,对于X的。
而还有一些你还不知道。就在我们家在湖区小住时,我想尽了办法去小树林与他私会,不止一两次,而是5次。每次我们都做了那事。我真的是情不自禁,管不住自己。每一次约会我都比前一次更为狂热。因此,在激情的驱使下,我全然不顾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事实上,我满脑子都是他,再也容不下其他事,除了与他在一起,我也别无所求。
想像一下吧,当我感到他对我逐渐冷淡时,我是多么痛苦。似乎我的爱恋越来越深,而他的感情却在逐渐消退。第一次,一番亲昵过后,他是那么温存体贴,把我搂在怀中,细说着我的好处。这的确是减轻了我因没有抵受住他的要求而带来的负罪感。但是很快,他好像觉得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我这个人——事实上,是我的身体,而且他开始做出无礼之举。我觉得我成了可怕的激情的俘虏——事情发展到关键时刻,不是愚蠢的幻想,而是真实的生活。
刚开始他对我们家的来访真是令人激动。我可以整个早晨都等着他的马奔向大门时的声音,等着故意拖延不出来见他。我只为享受那种期待中的欢娱之情。经常地,我会向房间环顾一周,借此来瞥他一眼,就像他也跟其他普通客人一样。然后,一个秘密的眼神交汇,桌子底下轻轻一碰——这些都让我加剧了那种无以名状的欲望之火。
然而,他的来访越来越少,有时隔上一天,隔上两天,然后是三天。我开始气急败坏,轻率地让人给他送了个信,而他没有回应。一天晚上,他弹了一曲四重奏,我的目光几乎无法从他的身上移开。我在入口处单独截住了他,想质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不过话一出口就完全变了样——他装作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挣脱我的拉扯,匆忙跑了。
我很快陷入忧郁之中,只好推说自己有病。然而我还是很困惑——他还会来我们家吗,我还有希望吗?我在早上我们曾经走过的小路上散步,但再也没有遇见过他。一次跟他单独在一起时,我提议我们再定个约会。这么说时,我不惜放下架子,低眉顺眼,还朝他娇俏地一瞥。但他拒绝了,说他跟人约好了要去打猎,接着他就快步走开了,好像松了口气。
回家后,我是那么不高兴。这一次是真的病了,也因此错过了许多客厅里的聚会。客厅里的音乐与欢闹声传到楼上,更让我觉得郁郁寡欢。
一天晚上,我们都被召集到一起,爸爸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当他笑着举起艾蒂的手时,她的脸刷地红了。爸爸说他很高兴宣布她很快就会成为理查德·利奇菲尔德夫人了。妈妈欢呼起来,兄弟们开始开艾蒂的玩笑,而我差点当场晕倒,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哭着跑回房去。客厅里如此喧闹,只有妈妈注意到了我的悲伤。
婚礼很快定在8月底举行。3个月后他就将走进我们家的生活,乔治安排了婚姻财产协议——我看了,它的总额达到5000英镑,每年还有400英镑的年薪。这笔钱足以让这对夫妻过得舒舒服服。我偷听到爸爸说,他怀疑这个人是一个“掘金者”。
我跟他单独见了一面。为了这次约会,我这几年中第一次去了圣玛丽教堂。我们前后相随地回了家。我要求他对他的所作所为给个解释,至少出于礼貌。他看起来很尴尬。他说他早就跟爸爸讨论过,向我们其中一个求婚。而爸爸说,他该与艾蒂结合,因为她是姐姐。他说他在格拉斯米尔意外地遇上我时,被感情冲昏了头,但很快他就感到这事很不光彩,也很不合适,从而决定把我们的关系作个了断,他说他将永远把我当妹妹一样看待。
我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因为在8月中旬,我已经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告诉了妈妈,她真不敢相信我所做的一切。当她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时,她变得从未有过的生气和忧心如焚。她狠狠地甩了我几个耳光,而我没有哭。她说她知道那人是谁,但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爸爸。她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湖区的一个庄园主的儿子,并让我坚持这种说法。
爸爸非常震惊,他把我叫进他的研究室里。他坐在日常坐的那张皮椅里,没有打我,而是看起来苍老无力,好像他自己刚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使我感觉更糟。他没有质问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谁,他知道得不到什么答案。他说不管我多么痛悔自己的行为,我都将很难再赢回他的尊重,而我只能一辈子独身不嫁,他永远都不会为我准备嫁妆,但他也不会把我逐出家门,我可以永远住在这个家里。
但是,我不能留下这个孩子。为了保住我们一家的名声,他与查理·劳瑞·布莱斯取得了联系。他是美国人,经营着儿童援助社团。爸爸说他知道怎样处理这种问题。一周后,在布莱斯先生的建议下,我在身形未露之前被送到了苏黎世,并得在这儿待9个月。
她是个女婴。我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现这一点。我只被允许在剪去脐带和医生检查的那几分钟里抱了她一下。接着她就被接走了。我被告知她将在苏黎世待一段时间,等长到能经受旅程后,就会被送给一个很好的家庭抚养。
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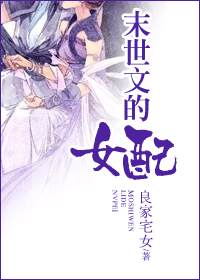
![[家教2718]自做自受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66/6669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