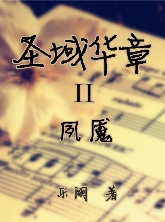圣域-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卡汨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淅淅沥沥的雨中。我转过身去,母亲拉着我的手,我感觉到了她手心的温度。然后她转头看着昭茵,微笑着说,你将成为格拉的妻子,魔界最美丽的妃子。
我没有看昭茵的眼睛。一切都没有必要,我是应该相信她的。然后我心里苦苦的笑了,雨从眉毛滴入我的眼睛,又顺着脸颊滑落。滑到嘴边的时候竟有一种苦涩的咸。雨水冲淡了我腿上的血迹,在脚下聚拢。一滴雨落下,破碎,然后溅起水滴,像一朵突然绽放的花,却很快惨烈的凋零。
我想一切都应该平静了,但我的心却为何还在翻腾,像风把海浪高高的卷起然后重重的落下。在冥界我常常看着花的凋零而黯然伤神,这时孟婆就会对我说,花落了还有再开的时候。但再一次花开要等多久,一天,一年。还是一辈子。
我在魔界的王宫得到了王子的礼遇,得到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宫殿,翼酩殿。我经常到王宫最深的藏书库去翻阅魔界最古老的典籍。在那里我得知魔界现在的王,我的父亲,他是魔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王。在他的带领下魔界才能与天界抗衡。魔界的子民不必再去对天界的神顶礼膜拜,因为他们认为不管谁都应该是平等的。但是现在他老了,再也不复当年的雄风。他的臣子变得越来越壮大,威胁着他的统治。然后我看到了关于勒斯的记载,看到了他的暴虐和残酷。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魔界的王,而只有他自己。魔界的子民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而他就是这样的飞扬跋扈。
在我看过的典籍里依然没有看到关于我的记载,所以我还在一天天的翻阅。黄昏的时候,我总喜欢仰面躺在翼酩殿的角楼上。天边懒散的飘过几片云彩,这时耳边会响起边关传战报的策马声,远远扬气的尘土在王宫的上空飘扬。天界和魔界永远在最远的云端对立,我一直这样认为,因为我不知道天界在何方。
我的母亲为昭茵准备了一座独立的阁楼,按照魔界的规矩,她和格拉会在三个月后举行盛大的婚典。昭茵很少出她的阁楼,偶尔我会在角楼上看到她倚在窗口凄怨的身影。她是在等待下一次花开么,而我又在等待什么?
秋天的雨很多,在窗口滴滴答答的响,我一直在想我的心是否也如这雨一样已经破碎了。对我来说三生石是空白的。而现在到哪一天我才会在魔界的典籍里翻阅到属于我的记载,它会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可是如果我根本就不是一个魔,那我的记载又将在哪呢?还有昭茵,我是否真的可以把她放弃,我爱她是那么的深,不想去伤害她。但是如果她现在不快乐,那又是谁的过错呢?
门开了,我回头看到了我的母亲。她盈盈的走来,脸上永远有抹不去的痛苦。我亲吻了她苍白的脸,然后问她,你为什么不快乐?母亲拉着我的手,她说,孩子,你现在还没有原谅你的父亲吗?他其实是那么的爱你。
我低下了头,想起了父亲说的那句话,是的,他应该被送到宫外去生活。
母亲的眼里突然涨满了泪水,她说,孩子,你可知道,你的父亲他是魔界最伟大的王。可是现在他已经病倒了。你知道勒斯吗?他是现在魔界最强大的魔,其实在二十年以前他就已经是了。他要把你送到宫外生活,你知道你的父亲是多么的痛苦吗?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更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他是魔界的王。你知道吗,每一次我送去的东西都是你的父亲亲自挑选的,那是王宫里最好的贡品。他的痛苦只有隐藏在心里,当你说你没有父亲的时候你知道他有多么的伤心吗?现在,他病倒了,勒斯对魔界的残暴统治已经让他心力憔悴,他总是觉得自己对不起魔界的子民。他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难道你还不能原谅他吗?
~第十节父亲~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以为有些人会永远的坚强,永远的屹立,永远的高高在上,但是我却忘了他们身后的痛苦,那种无法言明的痛苦。我说,母亲,我想去看看我的父亲。
父亲躺在塌上,面容憔悴,就像一朵即将风干的花。我在父亲的床前跪了下来,然后说,父亲,请原谅我。父亲转过头来看到我,他挣扎着想坐起来,但没有成功。我扶住父亲,泪水溢出了我的眼眶。
父亲抚摸着我的脸,他的手宽大而摩挲,那是常年征战的纪录。他说,洛崖,什么都不用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永远都是我的孩子。
我勉强的微笑,然后问,勒斯到底有多厉害,魔界真的没有人能打得过他吗?
父亲点了点头,然后看着我,他忽然又想摇头,但最终还是没有。他问我,你呢?你的出生就是一个谜,我不知道你的魔法有多高。
我说我也不知道。
父亲叹了口气说,我看到你走出幻境。你告诉我,如果勒斯在最后的时刻也没有因为傲慢而减弱魔法,你是不是就走不出来了?
我没有说话,风从窗户的隙缝里钻了进了,薄薄的吹在身上就如刀锋划过。
父亲继续说,你其实可以直接从他的魔法里走出来,对吗?可是你为什么要冒险,你知道如果勒斯没有减弱魔法,而你又失去了最后的时刻,你就只有死。
我笑了。我说我喜欢赌,一个真正的赌徒不管输赢都会去赌。
父亲看着我,很久没有说话。我回头看到格拉站在我的后面,远远的案桌旁一个女子抚着一首哀怨而忧伤的曲子。格拉走到父亲跟前,说,父亲,斐黎我已经叫过来了,你找她有事吗?
父亲点了点头说,洛崖,以后斐黎就是你的妻子,你要和她好好的辅佐你哥格拉。因为我死后他将是魔界的王。
琴声停止了,弹琴的女子走了过来,她看着我微笑,然后说,我是斐黎。
我勉强的笑了,然后转头看着我的父亲,慢慢的说,为什么我不能成为魔界的王?
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格拉转过身离开了。母亲的脸变得煞白,犹如初落的雪。我看着父亲,我知道只有他看过那个幻境,只有他才知道我爱着昭茵。但父亲却摇摇头,他说,这是规矩,魔界几千年来的规矩。斐黎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她一直生活在王宫,接受着很好的教育。她的琴在王宫里弹得是最出色的,比王宫专门司乐的乐师还要好。
我想打断他的话,我想说,那又能怎样,我爱的不是她。但是我没有这样说,因为斐黎站在我的身旁,我不想伤害一个无辜的女子。
我转过身去,殿外下雨了。我说,在我的心里永远没有规矩,我一定会成为魔界的王。
说完我走出父亲的寝宫。我听到斐黎在我身后说,洛崖,我是你的妻子。我苦笑了。然后我听到父亲吃力的说,在幻境里勒斯根本就没有使出他最厉害的魔法,所以即使你有本事冲破他幻境的魔法,你也是打不过他的。我还有半个月就会死的,你要记住,不管你们谁成为魔界的王,一定要时时刻刻想着魔界的子民。
细雨在我的面前落下,像是拉开一层又一层的帷帐。殿内飘出凄楚的琴声,像水珠一样贴着肌肤游动,缓慢而忧伤。我不知道我们会以争吵结束第一次谈话。我记得咯玛说过,狼并不会去想当森林之王,因为它们知道自己是狼,而不是狮子和老虎。那我呢,我是什么?难道我只是一只羊吗,任人宰割的羊吗?雨落到身上忽然有一种粗糙的感觉,白色的贴着肌肤,那是雪,夹杂在雨中的雪。我抬头,眼前是依稀的白色,不过它们又很快的消融移位,像是闪烁着满天繁星的夜空。
我在雨雪中站了很久,一直到冷得没有知觉。然后我看到昭茵站在我的前面,痛苦从她的眼中散淡出来,然后迅速的落下,我似乎听到了它破碎的声音,是心跳吗?昭茵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是那么的温暖而细腻。我再一次问她,如果我成为魔界的王,你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妻子。昭茵点了点头,然后又惊恐的摇头,她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的,我宁愿你活着,我只要你活着,你知道吗?
我低头亲吻了她被雨水淋湿的长发,然后看着她微笑,我说,放心吧,我会没事的。
风又一次吹起,吹散了她的眼泪,和细雨一起飘落。我转身离开,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腿似乎已经被冻住,无法弯曲。我听到昭茵在我的身后说,一切都没有关系,我只要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而是想了很多。如果我要成为魔界的王,我就一定要依靠一个人,那就是勒斯。他在魔界的北方拥有很多的部队,而且这些部队都是训练有素的。守卫在皇城的部队是由格拉控制,但太少了,而且根本不堪一击。孟婆和格拉都对我说过不要和勒斯作敌人。如果不能做敌人,那为什么不能做盟友呢?
勒斯是臣子,本应该住在王宫之外,但他却在王宫里有一座很大的宫殿。我知道他太强大了,所以他需要的东西没有人可以拒绝。当我踏进这座宫殿的时候,我感觉到了窒息。周围似乎弥漫着浓密的黑暗,朝胸口压来,空气不再清新,而是一股最终归宿的死亡气息。我想起了孟婆给我描述过的魔界,然后我苦涩的笑了。
勒斯并没有行臣子的礼节,而是冷笑着看着我。他说,二王子,你来我这有什么事吗?
我点了点头说,魔界之王还有半个月就要死了,我知道你一直想当魔界之王,只是因为现在的魔界之王威信太大了所以你一直没有反叛,对吗?
勒斯依然冷笑着,没有否认。
我继续说,我知道你这几天一直在调动你留在北方的部队,他们正在向皇城进发,是这样吗?
勒斯终于收起了他的笑容,他打量着我,脸色有些不安。然后他问我,你怎么知道?
我叹了口气,说,最近我看到魔界边关传战报的士兵越来越少,这说明魔界与天界的战争暂时缓和了。而魔界所运送边关的粮食却越来越快,这是因为你的部队在朝皇城靠近,运送距离近了,而且你又想在皇城外屯粮。这样只要王一死,你就可以马上占领皇城。
勒斯脸有怒色,他的手伸向了腰间的剑。昨天的雨依然在下,淅淅沥沥像是在小心翼翼的弹着即将断弦的琴。一切都绷得很紧,似乎一触即发。我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笑了。我说,放开你的手吧,我想得到你的帮助。
勒斯松开了手,然后看着我的眼睛说,帮你什么?
~第十一节我要当魔界的王~
我说,我要当魔界的王,只有你能帮我。
勒斯笑了,带有一丝讥诮,他说,你既然知道我想成为魔界的王,我又怎么会帮你呢?
我说,因为你也需要我的帮助。
你的帮助?为什么?
魔界之王一死,你是可以迅速的占领皇城,成为新的魔界之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肯定要杀了格拉才能当王。那个时候你就会背上叛乱的罪名,魔界的子民和官兵自然会不服你的统治。他们一定会拥护我出来讨伐你,即使我们失败了,你的统治也不会很安稳。
勒斯低下了头,他也许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似乎已经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然后他眉头皱了皱,问,你怎么帮我?难道你可以不反抗我吗?
我笑了,摇摇头说,即使那个时候我不想这么做,我也没得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