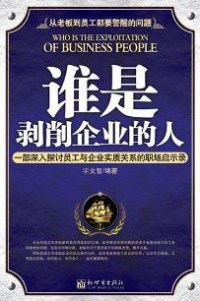谁是谁的鸡肋by小马疯跑(先虐受再虐攻he)-第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桦,我去酒吧了,没找到张宽。”
苏桦点了点头,看着JOHN坐下来,伸出手去握住他的大手。
“JOHN,记不记得你当时把我从天台上拉下来,说我就像个迷路的孩子,其实这两年来,我依然时常迷路,更多的时候我不知道路在那里,自己想走的是那一条,我喜欢捷径,除了在工作上我善於找到捷径,生活上更甚,可生活中哪有真正的捷径,走得快了,丢的也多。我记得你说过,什麽事情都可以勉强,只有感情勉强不了,这两年,我一直在勉强你。”苏桦松开了手,手里放下了那枚戒指。
JOHN把戒指拿起来看了看,弹了一下,挤出个笑容来,“你们中国人最讲究婚约,所以我一心想和你有这样一个仪事,以为这样才能留住你。”
“我知道,JOHN。”苏桦眼睛里的光芒更暗了,“其实这两年你对我非常好,可我不能霸着你的好又没法对你掏出真心,那样对你真的不公平,我真的不配。”
JOHN摇摇头,又拍拍苏桦的脸,“你最近的神精太紧张了,如果感觉到不好,要不就重新开始吃药吧,你这次突然晕倒可不是什麽好现象,我刚刚看了你的检查报告,虽然不算太坏,但也绝不能轻视,如果可以,休几天假吧。”
苏桦点了点头,然後笑着抬起身子在JOHN脸上吻了一下。
心里的那块大疙瘩终於解开了。
34
苏桦是第三天出院的,JOHN陪着他把东西放回去,就带着苏桦去了张宽的酒吧。
酒吧还是像那次来过的那一次一样,不冷清不热闹。
苏桦看了一眼等在门外的JOHN,JOHN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笑容,苏桦定了定神,向吧台走过去。面里有个年级不大的男孩正熟练地配酒,一看到他过来,对他点了个头就指了指吧台前的凳子让苏桦坐下了。
“张宽呢?”苏桦问的心慌,却一点也不犹豫。
“怎麽都找老板,前些天就有好几拨,今天又来了好几个。”
苏桦记得张宽以前说搞那个东西把身家性命都搭上了,不会是那个有什麽问题吧,“您怎麽称呼。”
“别您啊您的。叫我小K就行了。”小K把头凑了过来,低低在苏桦耳边说。“老板回家结婚去了,来的都是想盘店的,上个月他还说得好好的,暂时不转,就是将来转也会转给我,没想到这东西这麽没信用,一拍屁股全变了。”
“结婚?”苏桦呆了。
“是啊,就他那样的还结什麽婚啊,不是祸害人家良家妇女吗?我还以为他是个最坚定的呢,没想到前几天不知受什麽刺激了,扭了头就说要结婚了,说变就变了,真他妈的没劲,哎,我说刺激他的不是你吧,印像中就是那次见了你之後才变得神叨叨的,前几天一直拿着一个老外的照片对比过来对比过去呶,就是那个老外。”说着指了指门外面的JOHN。
苏桦不知道是怎麽出来的,看到JOHN一脸担心地看着他,心一下刺痛得就要裂开了。
结婚,张宽真的要结婚了,终於把他放下了。
实验室里苏桦定购的的仪器已经运过来了,看着那些还打着英文字的纸箱,苏桦一点打开的欲望都没有。他的手里一直在摆弄着一个小东西,接线,点焊,测试,足足弄了两天了。看着苏桦一脸灰败的模样,连李衡都没了八挂的胆量,只是悄悄的吩咐巩青出去要了一份粥端过来强逼着苏桦喝了。
“小桦儿,JOHN明早的飞机,咱们给他送个行吧。”
“好。”苏桦喝完了粥放下了碗,又开始摆弄起手里的那个东西。
“妈的,这个重要还是命重要,大不了,重新买一个呗,现在的比你这个老古董先进多了。”
“差不多快好了。”装上电池,苏桦在桌子上看了一圈,抬起头看到李衡脖子上挂了一个MP4,“把你的耳机我用用。”说着伸过手去把那个MP4的耳机卸下来,一看接口不符,直接拿了把尖嘴钳给钳断了,把线直接接在接口上。
李衡眼见着自己SONY原装的东西成了一个废品,嘴抖了半天,最终还是把嘴里的那句脏话给咽进去了。
当耳朵里那首‘渔人码头,’终於低低地浑着杂音响起来的时候,那些当年听腻了的句子一遍遍击打着他的耳膜时候,他听到张宽在他身後,低低的说,叶子,我是真的喜欢你。他听到张宽的叹气声,喜不喜欢是你的事,等不等是我的事。他听到张宽说我就快对你挖肝掏肺了,他听到张宽在唱
多麽愚蠢是我
多麽爱你是我
你给的寂寞
我已不能回头
张宽终於回了头,终於离了岸,终於把他放下了。
苏桦憋了好几天的眼泪终於掉了下来。
看到苏桦不吱声默默淌泪的模样,李衡一下子慌了,赶紧转过身子去找纸。
“桦儿,你别这样,没什麽过不去的,感情是什麽,屁都不是,当初我都那样了,不也都过来了。”
苏桦什麽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死死地抓着李衡的胳膊在李衡的手弯里拼命地摇着头。
的确没有什麽过不去的。张宽和苏桦也终将过去。这就是命,是他和张宽的命。苏桦真的相信是自己的失德、自私,那些被张宽看穿了的丑形来向他索取的报应。
35
回到家里,苏桦呆呆地看着这个被张宽布置一新的房子,进了厨房,那三个张宽送粥的保鲜饭盒大大小小撂得整整齐齐。简单的冲了碗泡面,吃了两口就扔了,回到客厅开着电视,看着上面或喜剧或悲剧的爱情,连广告时段他都没有变过几个姿式。这几个晚上他都是这麽过来的。盯着一个频道看到底成了一种强迫的消遣。
张保林的电话就是这个时候响起的。
里面一如既往地的关心爱护和夸耀听得苏桦胆战心惊,生怕一不小心就能从里面蹦出张宽的声音,又生怕说到底也没有张宽的声音。情况是後者,没有张宽的声音,只有张宽的一个消息,张宽真的要结婚了,时间定在三天後,张保林希望他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参加。
放了电话,苏桦静静地看着手里的那个陶制的杯子,上面有张宽亲手写下的他的名字。他从没想过小时候那个粗心的张宽为了他能花去那麽多心思。可现在那个人把所有心思放下了,要结婚了。
苏桦轻轻地笑了起来,笑得心都绞到了一起,痛得他全身抽搐。
因为是周六,苏桦不需要请假,直接坐了早班的飞机飞回了C城。
他不知道为什麽要回来,他甚至订了机票又退掉,还在房子里煎熬了差不多整整一天才决定不管怎麽说也要回去一次,不管是为了这麽多年张保林对他的爱护,还是为了这些年张宽对他的隐忍,还是为了自己,回去一次,看了,见了,就彻底死心了。
下了飞机,打车的时候,苏桦刚报了地址,就听出租车司机说了一个消息,直接把苏桦听呆了。
“知道吗,就是那个当年最红火的仪表厂破产了,就昨天,刚宣布的。”
“就那个城东的吗?”苏桦赶紧问。
“还能哪个,早不行了,想当年那个红火劲儿,多少人想进进不去呢,现在,唉,说来说去倒霉都是普通老百姓,厂里的工人这两天正闹事呢,好几百人坐到火车道上了堵着呢,每个职工只分到了两万多,现在两万多能干啥,能撑几年,还不够孩子上学呢?”
苏桦愣住了,招呼车子先别去医院了,掉了个头,穿过这个重工业城市的市中心,向城东开去。
这几年陆陆续续几个厂倒闭,城东早没了前几年繁华的景像,窄窄的街道,破败的院墙,早点滩,蔬菜滩,水果滩大都是下了岗的工人糊口之用。
等到车开到厂门口,当年那个威严的大门早不复当年的模样,门房成了报刊亭,脱了墙皮的墙上隐约着还能看到‘奋战三季度,产量创新高’的字样,当年那个气派的黄铜雕像依然璀璨光亮,安静的车间和热闹的厂大门有着物是人非的凄凉。厂门口围了一百多人吵吵闹闹,有坐的、站的、说的、骂的。
苏桦没有下车,透过车窗打眼看了看,看到里面有不少看着眼熟的中年人,年轻一点的还有自己叫不上名姓的同班同学,几个养父车间里的同事,还有些跟着大人凑热闹不知愁苦的孩子。
看着那些一下子被破产打击的没有一点生气的男人、女人,嘴里隐约传出来的是对以後生活的胆忧和恐惧,赖以生活的饭碗没了,这里的很多人一家子都在这个厂里,父母,子女,一下子好几口人没有了收入,那种境况苏桦看的直揪心。
在里面找了一圈没有看到这群人里面有自己的养母,苏桦扭头对司机说了声,去医院吧。掉头离开了厂子。
医院,是苏桦最不愿意来的地方,他在医院里失去了一切,又差点在医院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站在英国医院的五楼上,多少次下了决心跳下去,跳下去就一了百了,什麽也不计较什麽也不计挂了,可最终他还是一次次的放弃了。虽然活着比死艰难,可又有什麽比活着更充满变数。苏桦不能成为弱者,跌跌撞撞也要努力地向前冲,这种认知已经左右了他二十几年,改不了了。
这所离城里十公里的医院更像是个疗养所,绿树环绕,环境优美,人也很少。下了车,苏桦绕过门诊朝後面的住院部跑过去。
一楼一个单人特护病房里,养母正小心地给养父喂着稀饭,养父嘴歪着,一勺子能有一多半从嘴角漏了出来。
苏桦站在门口看了几分锺,然後轻轻走过去,叫了声“妈。”看到母亲一脸惊谔地看着他,手忙脚乱地站起来招呼他坐,客气得一边放碗一边擦手,好像自己是个什麽大人物,苏桦连忙笑了笑,把养母推到凳子边坐下。
“我刚刚到,来把稀饭给我,我来给爸喂。”
“不不用,你歇着吧,刚下飞机累着呢。”养母似乎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看到苏桦要接碗,慌里慌张抱着碗就往旁边躲。
“妈,我来喂,您先歇会儿。”
看到苏桦一心要做,养母犹豫了一会儿,不再抵抗,把碗和勺子递过去。
苏桦拿了一个围兜垫在养父的脖子下面,舀了一勺家里自制的小菜,混在稀饭里,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把稀饭送进养父的嘴里,那些掉下来的稀饭还没落到围兜上就被苏桦小心地擦掉了。
“小桦,你是听到消息回来的吧。”养母小心翼翼地问。
苏桦回过头笑笑,点点头。“前天晚上听说的。”
“唉 ,说破就破了,那麽大的一个厂,当年还是全国的一面旗帜,说倒就倒,真没想到。”苏桦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他和母亲说的跟本不是一回事,扭回头对他母亲说:“刚我回厂里了,门口还有很多人围在那里。”
“是啊,突然没了工作,就发那麽点钱补偿,厂里也不给个说法,以後可怎麽办呀?”
苏桦轻轻拍了拍母亲的手:“没关系,有我呢。”
他现在万分庆幸自己回来一趟,要是不回来,照以往的习惯,养母肯定会瞒着他自己把这一切悄悄承受了,现在对於他们来说,能有什麽比自己站在他们身後更让他们心安了。
苏桦妈妈脸红了一下,拽了拽衣角;有点尴尬地说:“我不是指我们,你寄了那麽多钱回来,还没用上呢,我是说那些厂里的人,干了一辈子,家里有老有小的,突然就这麽着了,以後可难着呢。”
![兽人之谁是雌性?![耽美]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151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