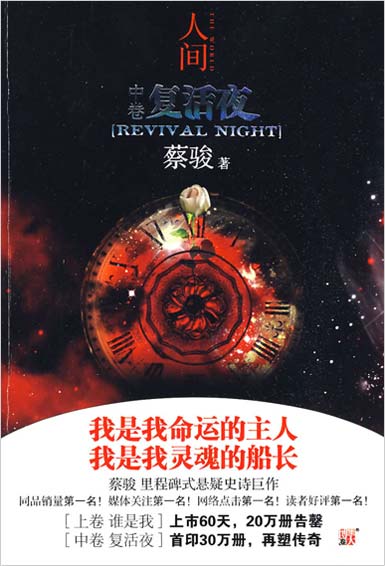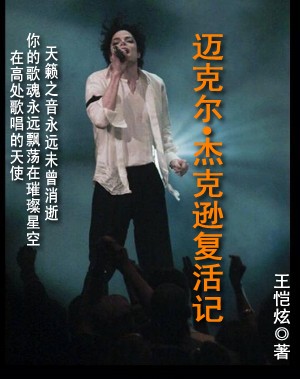复活-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诗人气质的索菲雅姑妈的忧虑就要切实得多。她生怕具有敢作敢为的可贵性格的德米特里一旦爱上这姑娘,就会不顾她的出身和地位,毫不迟疑地同她结婚。
如果聂赫留朵夫当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卡秋莎,尤其是如果当时有人劝他绝不能也不应该把他的命运同这样一个姑娘结合在一起,那么,凭着他的憨直性格,他就会断然决定非同她结婚不可,不管她是个怎样的人,只要他爱她就行。不过,两位姑妈并没有把她们的忧虑告诉他,因此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姑娘的爱情,就这样离开了姑妈家。
他当时满心相信,他对卡秋莎的感情只是他全身充溢着生的欢乐的一种表现,而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也有着和他一样的感情。临到他动身的时刻,卡秋莎同两位姑妈一起站在台阶上,用她那双泪水盈眶、略带斜睨的乌溜溜的眼睛送着他,他这才感到他正在失去一种美丽、珍贵、一去不返的东西。他觉得有说不出的惆怅。
“再见,卡秋莎,一切都得谢谢你!”他坐上马车,隔着索菲雅姑妈的睡帽,对她说。
“再见,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用亲切悦耳的声音说,忍住满眶的眼泪,跑到门廊里,在那儿放声哭了起来。
十三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整整三年没有同卡秋莎见面。直到三年后他升为军官,动身去部队,路过姑妈家,这才又见到了她。但同三年前的夏天住在她们家里时相比,他已换了个人了。
那时他是个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意为一切高尚事业献身;如今他可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迷恋酒色,享乐成癖。那时,上帝创造的世界在他看来是个谜,他兴致勃勃地企图解开这个谜;现在呢,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简单明了,都是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安排的。那时,接触大自然,接触前人——在他以前生活、思想和感觉过的哲学家、诗人——是重要的;现在呢,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跟同事们的交际活动。那时,他觉得女人是神秘而迷人的,正因为神秘就更加迷人;现在呢,女人,除了亲人和朋友的妻子,她们的作用都很清楚:女人是他领略过的最好的玩乐用具。那时他不需要钱,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都花不掉,他可以放弃父亲名下的地产,分赠给他的佃户;现在呢,母亲按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他还不够用,为了钱他跟母亲拌过嘴。那时,他认为精神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我;现在呢,他以为精力充沛的强壮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他身上发生各种可怕的变化,只是由于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因为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日子就太不好过。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处理一切事情就不利于追求轻浮享乐的兽性的我,而总会同它抵触。相信别人的理论,就根本无须处理什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且总是同精神的我抵触而有利于兽性的我。此外,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谴责;他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赞扬。
譬如,聂赫留朵夫思索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问题,阅读有关书籍并同人家谈论这些事,人家就会觉得不合时宜,简直有点可笑,他的母亲和姑妈就会好意地取笑他,戏称他是我们亲爱的哲学家。但他看爱情小说,讲淫秽笑话,到法国剧院看轻松喜剧,并且津津乐道,大家就称赞他,鼓励他。他省吃俭用,穿旧大衣,不喝酒,大家就觉得他脾气古怪,有意标新立异。他在打猎上挥金如土,在布置书房上穷奢极侈,大家就吹捧他风雅脱俗,还送给他贵重礼品。他原来童贞无瑕,并且想保持到结婚,但他的亲人都为他担忧,以为他有病,后来他母亲知道他从同事手里夺了一个法国女人,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不仅不难过,反而感到高兴。但公爵夫人一想到儿子同卡秋莎的关系,而且可能同她结婚,就感到忧心忡忡。
同样,聂赫留朵夫成年以后,他把父亲遗留给他的一块面积不大的地产分赠给农民,因为他认为地主拥有土地是不合理的。不料他这种行为却使他的母亲和亲戚大为吃惊,并且从此成为大家嘲弄的话题。人家多次告诉他,获得土地的农民不仅没有发财,反而更穷了,因为他们开了三家小酒店,索性不干农活。等聂赫留朵夫进了近卫军,跟门第高贵的同僚们一起花天酒地,输去许多钱,弄得叶莲娜·伊凡诺夫娜不得不动用存款,她却满不在乎,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觉得年轻时在上流社会种些痘苗以增加免疫力,还是件好事。
聂赫留朵夫起初作过反抗,但十分困难,因为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好的,别人却认为坏的;反之,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坏的,别人却认为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话。开头这样的自我否定是很不愉快的,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时聂赫留朵夫开始吸烟喝酒,他不再感到不愉快,甚至觉得轻松自在了。
聂赫留朵夫天生热情好动,不久就沉湎于这种受亲友称道的新生活中,把内心的其他要求一概排斥了。这种变化开始于他来到彼得堡以后,而在他进入军界后彻底完成。
军官生活本来就容易使人堕落。一个人一旦进入军界,就终日无所事事,也就是说脱离合理的有益劳动,逃避人们共同负担的义务。换来的则是军队、军服、军旗的荣誉。再有,一方面是颐指气使,对别人享有无限权力;另一方面,在长官面前却又奴颜婢膝,唯命是从。
不过,除了进军队服务以及军服、军旗和合法的暴行屠杀所造成的一般性堕落外,在有钱有势的军官才能进入的近卫军团里,军官们因为富裕和接近皇室而格外堕落。这批人很容易发展成为疯狂的利己主义者。聂赫留朵夫自从担任军职,开始象同僚们那样生活以来,他就落入了这种疯狂的利己主义的泥沼之中。
他没有什么正经事要做,只须穿上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精心缝制、洗刷干净的军服,戴上头盔,拿起别人铸造、擦亮并交到他手里的武器,跨上一匹由别人饲养和训练的骏马,跟着那些同他一样的人去参加练兵或者检阅,也就是纵马奔驰,挥舞马刀,开枪射击,并把这一套教给别人就行了。他们没有别的事做,但那些达官贵人,不论老少,连沙皇和他的亲信都赞同他们的活动,甚至因此夸奖他们,感谢他们。这些活动结束以后,他们认为正当和重要的是到军官俱乐部或者豪华的饭店里去吃吃喝喝,纵情挥霍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金钱;然后就是剧场,舞会,女人,然后又是骑马,舞刀,奔驰,然后又是挥金如土,喝酒,打牌,玩女人。
这样的生活对军人的腐蚀特别厉害,因为要是一个平民过这样的生活,他内心深处就会感到害臊。军人过这样的生活却心安理得,并且自吹自擂,引以为荣,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聂赫留朵夫正好是在向土耳其宣战后进入军队的。“我们准备为国捐躯,因此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仅可以原谅,而且在我们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才这样过日子。”
聂赫留朵夫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也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想法。他由于冲破了以前给自己定下的种种道德藩篱,一直感到轻松愉快,并且经常处于利己主义的疯狂状态中。
三年后他到姑妈家去的时候,正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
十四
聂赫留朵夫这次到姑妈家去,是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已开赴前方,他中途要经过她们的庄园,而且两位姑妈热情邀请他去,但主要的原因是他很想看看卡秋莎。也许在灵魂深处他已受到那如今脱缰的兽性的冲动,对卡秋莎起了歹念,但这一点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只是想重游他曾快乐地生活过的地方,看看两位对他一向十分慈爱和赞赏、可笑而又可亲的姑妈,看看给他留下愉快回忆的天真可爱的卡秋莎。
他是在三月底耶稣受难日①到达的。当时冰雪初融,道路泥泞,而且下着倾盆大雨,把他淋得浑身湿透,身子冻僵,但他还是生气蓬勃,精神焕发——在那个时候,他总是这样的。“她是不是还在她们家里?”马车到达姑妈家熟识的旧式地主庄园时,他心里想。庄园院子里堆着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积雪,周围砌着一道矮墙。他满心希望,她一听见他的铃铛声就会跑到台阶上,但只看见两个裙裾掖在腰里的赤脚女人提着水桶从边门出来,她们显然正在擦地板。正门入口处也没有她的人影子,只见听差吉洪一人出来。他系着围裙,看来也在打扫房子。索菲雅姑妈身穿丝绸连衣裙,头戴睡帽,来到了前厅。
①复活节前最后一个礼拜五。
“啊,你到底来了,太好了!”索菲雅姑妈一边吻他,一边说。“玛丽雅姑妈有点不舒服,她刚才去教堂累了。我们领过圣餐了。”
“恭喜你,索菲雅姑妈,”聂赫留朵夫吻了吻索菲雅姑妈的手说,“对不起,我把您弄湿了。”
“快到房间里去。你浑身都湿透了。瞧你已经有胡子了……卡秋莎!卡秋莎!快给他拿咖啡来。”
“我这就来!”走廊里传来熟识的好听声音。
聂赫留朵夫高兴得心都怦怦直跳。“她还在这儿!”好象太阳从云端里露出脸来。聂赫留朵夫兴高采烈地跟着吉洪到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去换衣服。
聂赫留朵夫很想向吉洪打听一下卡秋莎的情况:她身体好吗?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快出嫁了?可是吉洪的态度是那么毕恭毕敬,庄重严肃,并且一定要亲自给他用水冲手,弄得聂赫留朵夫不好意思向他打听卡秋莎的事,只能问问他的孙子们好不好,那匹被唤作“哥哥的老马”和看家狗波尔康怎么样。原来孙子们和老马都很好,挺强壮,只有波尔康去年疯了。
聂赫留朵夫脱下身上的湿衣服,刚要穿上干净衣服,忽然听见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聂赫留朵夫从脚步声和敲门声中听出是谁来了。只有她才是这样走路和敲门的。
他披上潮湿的军大衣,走到门口。
“请进!”
果然是她,是卡秋莎。还是同原来一样,但出落得越发俏丽可爱了。那双纯洁的略带斜睨的黑眼睛仍旧那么笑盈盈地从脚到头打量人。她仍旧系着洁白的围裙。姑妈让她送来一块刚剥去包装纸的香皂和两条手巾:一条是俄国式大浴巾,一条是毛巾。不论是没有用过的字迹清楚的香皂,还是那两条手巾,或者卡秋莎本人,都是那么洁净、新鲜、纯朴、惹人喜爱。她那两片线条清楚的可爱红唇,象上次看见他时一样,由于内心难以抑制的喜悦而皱了起来。
“欢迎您,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好不容易才说出口,脸涨得通红。
“你好……您好,”聂赫留朵夫不知道对她说话用“你”好还是用“您”好,脸涨得象她一样红。“身体好吗?”
“感谢上帝……您瞧,姑妈叫我给您送您喜爱的玫瑰香皂来了,”她说着把肥皂放在桌上,把手巾往椅子扶手上一搭。
“人家侄少爷自己有,”吉洪夸耀客人的阔气说,得意扬扬地指指聂赫留朵夫那个打开的大梳妆箱。箱子里放着许多银盖的瓶子、刷子、发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