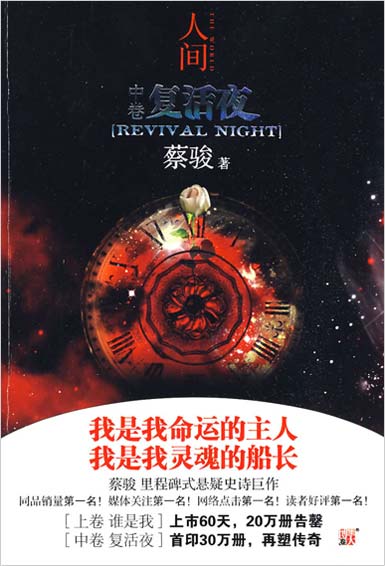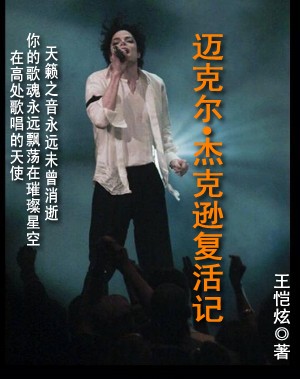复活-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没有数过,我只看见都是些百卢布钞票。”
“被告看见了百卢布钞票,那么,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
“那么,后来你把钱取来了?”庭长看看表,又问。
“取来了。”
“那么,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把我带走了,”玛丝洛娃说。
“那么,你是怎样把药粉放在酒里给他喝下去的?”庭长问。
“怎样给吗?我把药粉撒在酒里,就给他喝了。”
“你为什么要给他喝呢?”
她没有回答,只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
“他一直不肯放我走,”她沉默了一下,说。“我被他搞得筋疲力尽。我走到走廊里,对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但愿他能放我走。我累坏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他把我们也弄得烦死了。我们来让他吃点安眠药,他一睡着,你就可以脱身了。’我说:‘好的。’我还以为那不是毒药。他就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进房间,他躺在隔板后面,一看见我就要我给他倒白兰地。我拿起桌上一瓶上等白兰地,倒了两杯,一杯自己喝,一杯给他喝。我把药粉撒在他的杯子里,给他吃。我要是知道那是毒药,还会给他吃吗?”
“那么,那个戒指怎么会落到你手里的?”庭长问。
“戒指,那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给你的?”
“我跟他一回到旅馆就想走,他就打我的脑袋,把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拔脚要走。他就摘下手上的戒指送给我,叫我别走,”玛丝洛娃说。
这时副检察官又站起来,仍旧装腔作势地要求庭长允许他再提几个问题。在取得许可以后,他把脑袋歪在绣花领子上,问道:
“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待了多少时间。”
玛丝洛娃又露出惊惶失措的神色,目光不安地从副检察官脸上移到庭长脸上,急急地说:
“我不记得待了多久。”
“那么,被告是不是记得,她从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出来后,有没有到旅馆别的什么地方去过?”
玛丝洛娃想了想。
“到隔壁一个空房间里去过,”她说。
“你到那里去干什么?”副检察官忘乎所以,竟直接向她提问题了。①
①检察官按理必须通过庭长才能提问题。不能直接审问被告。
“我去理理衣服,等马车来。”
“那么,卡尔津金有没有同被告一起待在房间里?”
“他也去了。”
“他去干什么?”
“那商人还剩下一点白兰地,我们就一块儿喝了。”
“噢,一块儿喝了。很好。”
“那么,被告有没有同西蒙说过话?说了些什么?”
玛丝洛娃忽然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急急地说:
“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有过什么,我全讲了,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你们要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没有罪,就是这样。”
“我没有别的话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装腔作势地耸起肩膀,动手在他的发言提纲上迅速记下被告的供词:她同西蒙一起到过那个空房间。
法庭上沉默了一阵子。
“你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
“我都说了,”玛丝洛娃叹口气说,坐下来。
随后庭长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接着听了左边的法官在他耳边低声说的话,就宣布审讯暂停十分钟,匆匆地站起来,走出法取。庭长同左边那个高个儿、大胡子、生有一双善良大眼睛的法官交谈的是这样一件事:那个法官感到胃里有点不舒服,自己要按摩一下,吃点药水。他把这事告诉了庭长,庭长就宣布审讯暂停。
陪审员、律师、证人随着法官纷纷站起来,大家高兴地感到一个重要案件已审完了一部分,开始走动。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员议事室,在窗前坐下来。
十二
对,她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的关系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念大学三年级那年的夏天。当时他住在姑妈家,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往年,他总是同母亲和姐姐一起在莫斯科郊区他母亲的大庄园里歇夏。但那年夏天他姐姐出嫁了,母亲出国到温泉疗养去了。聂赫留朵夫要写论文,就决定到姑妈家去写。姑妈家里十分清静,没有什么玩乐使他分心,两位姑妈又十分疼爱他这个侄儿兼遗产继承人。他也很爱她们,喜欢她们淳朴的旧式生活。
那年夏天,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里感到身上充满活力,心情舒畅。一个青年人,第一次不按照人家的指点,亲身体会到生活的美丽和庄严,领悟到人类活动的全部意义,看到人的心灵和整个世界都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他对此不仅抱着希望,而且充满信心。那年聂赫留朵夫在大学里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特别是由于他本身是个大地主的儿子。他的父亲并不富有,但母亲有一万俄亩光景的陪嫁。那时他第一次懂得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荒谬,而他又十分看重道德,认为因道德而自我牺牲是最高的精神享受,因此决定放弃土地所有权,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赠送给农民。现在他正在写一篇论文,论述这个问题。
那年他在乡下姑妈家的生活是这样过的:每天一早起身,有时才三点钟,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到山脚下河里去洗澡,有时在晨雾弥漫中洗完澡回家,花草上还滚动着露珠。早晨他有时喝完咖啡,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查阅资料,但多半是既不读书也不写作,又走到户外,到田野和树林里散步。午饭以前,他在花园里打个瞌睡,然后高高兴兴地吃午饭,一边吃一边说些有趣的事,逗得姑妈们呵呵大笑。饭后他去骑马或者划船,晚上又是读书,或者陪姑妈们坐着摆牌阵。夜里,特别是在月光溶溶的夜里,他往往睡不着觉,原因只是他觉得生活实在太快乐迷人了。有时他睡不着觉,就一面胡思乱想,一面在花园里散步,直到天亮。
他就这样快乐而平静地在姑妈家里住了一个月,根本没有留意那个既是养女又是侍女、脚步轻快、眼睛乌黑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从小由他母亲抚养成长。当年他才十九岁,是个十分纯洁的青年。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妻子才是女人。凡是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都不是女人,而只是人。但事有凑巧,那年夏天的升天节①,姑妈家有个女邻居带着孩子们来作客,其中包括两个小姐、一个中学生和一个寄住在她家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
①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后四十天,五月一日至六月四日之间。
吃过茶点以后,大家在屋前修剪平坦的草地上玩“捉人”游戏。他们叫卡秋莎也参加。玩了一阵,轮到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一起跑。聂赫留朵夫看到卡秋莎,总是很高兴,但他从没想到他同她会有什么特殊关系。
“哦,这下子说什么也捉不到他们两个了,”轮到“捉人”的快乐画家说,他那两条农民的短壮罗圈腿跑得飞快,“除非他们自己摔交。”
“您才捉不到哪!”
“一,二,三!”
他们拍了三次手。卡秋莎忍不住格格地笑着,敏捷地同聂赫留朵夫交换着位子。她用粗糙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向左边跑去,她那浆过的裙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跑得很快。他不愿让画家捉到,就一个劲儿地飞跑。他回头一看,瞧见画家在追卡秋莎,但卡秋莎那两条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腿灵活地飞跑着,不让他追上,向左边跑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坛,没有一个人跑到那里去,但卡秋莎回过头来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点头示意,要他也到花坛后面去。聂赫留朵夫领会她的意思,就往丁香花坛后面跑去。谁知花丛前面有一道小沟,沟里长满荨麻,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一脚踏空,掉到沟里去。他的双手被荨麻刺破,还沾满了晚露。但他立刻对自己的鲁莽感到好笑,爬了起来,跑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卡秋莎那双水灵灵的乌梅子般的眼睛也闪耀着笑意,她飞也似地迎着他跑来。他们跑到一块儿,握住手。①
①在这种游戏中,被追的两人在一个地方会合,相互握手,表示胜利。
“我看,您准是刺破手了,”卡秋莎说。她用那只空着的手理理松开的辫子,一面不住地喘气,一面笑眯眯地从脚到头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这里有一道沟,”聂赫留朵夫也笑着说,没有放掉她的手。
她向他靠近些,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竟向她凑过脸去。她没有躲避,他更紧地握住她的手,吻了吻她的嘴唇。
“你这是干什么!”卡秋莎说。她慌忙抽出被他握着的手,从他身边跑开去。
卡秋莎跑到丁香花旁,摘下两支已经凋谢的白丁香,拿它们打打她那热辣辣的脸,回过头来向他望望,就使劲摆动两臂,向做游戏的人们那里走去。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变了,那是一个纯洁无邪的青年同一个纯洁无邪的少女相互吸引的特殊关系。
只要卡秋莎一走进房间,或者聂赫留朵夫老远看见她的白围裙,世间万物在他的眼睛里就仿佛变得光辉灿烂,一切事情就变得更有趣,更逗人喜爱,更有意思,生活也更加充满欢乐。她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不仅卡秋莎在场或者同他接近时有这样的作用,聂赫留朵夫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一个卡秋莎,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而对卡秋莎来说,只要想到聂赫留朵夫,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聂赫留朵夫收到母亲令人不快的信也罢,论文写得不顺利也罢,或者心头起了青年人莫名的惆怅也罢,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一个卡秋莎,他可以看见她,一切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
卡秋莎在家里事情很多,但她总能一件件做好,还偷空看些书。聂赫留朵夫把自己刚看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借给她看。她最喜爱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僻静的角落》。他们只能找机会交谈几句,有时在走廊里,有时在阳台或者院子里,有时在姑妈家老女仆玛特廖娜的房间里——卡秋莎跟她同住,——有时聂赫留朵夫就在她们的小房间里喝茶,嘴里含着糖块。他们当着玛特廖娜的面谈话,感到最轻松愉快。可是到了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谈话就比较别扭。在这种时候,他们眼睛所表达的话和嘴里所说的话截然不同,而眼睛所表达的要重要得多。他们总是撅起嘴,提心吊胆,待不了多久就匆匆分开。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住在姑妈家,他同卡秋莎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关系。两位姑妈发现他们这种关系,有点担心,甚至写信到国外去告诉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叶莲娜·伊凡诺夫娜公爵夫人。玛丽雅姑妈唯恐德米特里同卡秋莎发生暧昧关系。但她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聂赫留朵夫也象一切纯洁的人谈恋爱那样,不自觉地爱着卡秋莎,他对她的这种不自觉的爱情就保证了他们不致堕落。他不仅没有在肉体上占有她的欲望,而且一想到可能同她发生这样的关系就心惊胆战。但具有诗人气质的索菲雅姑妈的忧虑就要切实得多。她生怕具有敢作敢为的可贵性格的德米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