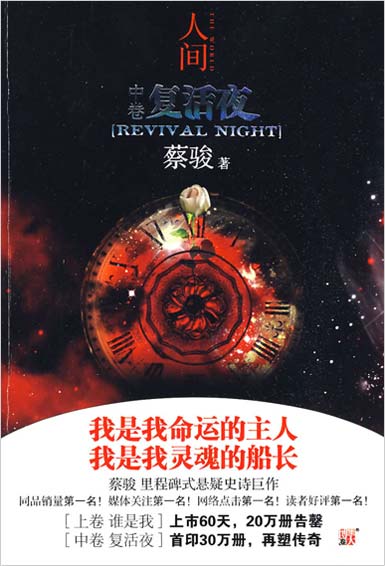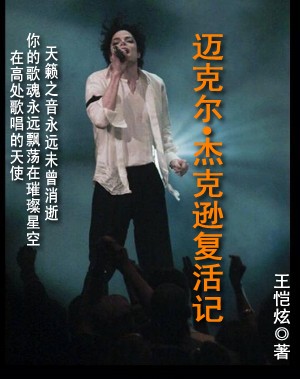复活-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门廊里的人互相挤紧,给聂赫留朵夫让路。聂赫留朵夫来到街上,沿着斜坡往上走。两个赤脚的男孩跟着他从门廊里出来:一个年纪大些,穿一件脏得要命的白衬衫;另一个穿一件窄小的褪色粉红衬衫。聂赫留朵夫回头对他们瞧了瞧。
“你这会儿到哪儿去?”穿白衬衫的男孩问。
“去找玛特廖娜,”他说。“你们认识她吗?”
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知怎的笑起来,可是岁数大些的那个一本正经地反问道:
“哪一个玛特廖娜?是很老的那一个吗?”
“对了,她很老了。”
“哦—哦,”他拖长声音说。“那是谢梅尼哈,她住在村子尽头。我们带你去。走,费吉卡,我们带他去。”
“那么马怎么办?”
“那不要紧!”
费吉卡同意了。他们三人就一起沿着街道往坡上走。
五
聂赫留朵夫觉得同孩子们一起比同大人一起自在得多。他一路上同他们随便聊天。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再笑,却象那个大孩子一样懂事地说话。
“那么,你们村里谁家最穷啊?”聂赫留朵夫问。
“谁家穷?米哈伊拉穷,谢苗·玛卡罗夫穷,还有玛尔法也穷得要命。”
“还有阿尼霞,她还要穷。阿尼霞连母牛都没有一头,他们在要饭呢,”小费吉卡说。
“她没有牛,但他们家总共才三个人,可玛尔法家有五个人呢,”大孩子反驳说。
“可阿尼霞到底是个寡妇哇,”穿粉红衬衫的男孩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说阿尼霞是寡妇,人家玛尔法也同寡妇一样,”大孩子接着说。“同寡妇一样,她丈夫不在家。”
“她丈夫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
“蹲监牢,喂虱子,”大孩子用老百姓惯常的说法回答。
“去年夏天他在东家树林里砍了两棵小桦树,就被送去坐牢,”穿粉红衬衫的男孩赶紧说。“到如今都关了有五个多月了,他老婆在要饭,还有三个孩子,一个害病的老太婆,”他详详细细地说。
“她住在哪儿?”聂赫留朵夫问。
“喏,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男孩指着一所房子说。房子前面有一个非常瘦小的淡黄头发男孩。那孩子生着一双罗圈腿,身子摇摇晃晃,站在聂赫留朵夫走着的那条小路上。
“华西卡,你这淘气鬼,跑到哪儿去了?”一个穿着脏得象沾满炉灰的布衫的女人从小屋里跑出来,大声叫道。她神色惊惶地跑到聂赫留朵夫前面,一把抱起孩子就往屋里跑,仿佛怕聂赫留朵夫会欺负他似的。
这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女人,她的丈夫因为砍伐聂赫留朵夫家树林里的小桦树而坐牢。
“那么,玛特廖娜呢,她穷吗?”聂赫留朵夫问,这时他们已经走近玛特廖娜的小屋。
“她穷什么?她在卖酒,”穿粉红衬衫的瘦男孩断然回答。
聂赫留朵夫走到玛特廖娜小屋跟前,把两个孩子打发走,自己走进门廊,又来到屋子里。玛特廖娜老婆子的小屋只有六俄尺长,要是高个子躺到炉子后面的床上,就无法伸直身子。聂赫留朵夫心里想:“卡秋莎就是在这张床上生了孩子,后来又害了病的。”玛特廖娜的整个小屋几乎被一架织布机占满。老婆子和她的孙女正在修理织布机。聂赫留朵夫进门时,头在门楣上撞了一下。另外两个孩子紧跟着东家冲进小屋,小手抓住门框,站在他后面。
“你找谁?”老婆子因织布机出了毛病,心里很不高兴,怒气冲冲地问。再说,她贩卖私酒,见了陌生人就害怕。
“我是地主。我想跟您谈谈。”
老婆子不吭声,仔细对他瞧了瞧,脸色顿时变了。
“啊呀,我的好人儿,我这傻瓜可没认出你来呀,我还以为是什么过路人呢,”玛特廖娜装出亲热的口气说。“哎哟,我的好老爷呀……”
“我想跟您单独谈谈,最好不要有外人在场,”聂赫留朵夫望着打开的门说。门口站着几个孩子,孩子后面站着一个瘦女人。她手里抱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娃娃。那娃娃十分虚弱,但一直笑嘻嘻的,头上戴着一顶碎布缝成的小圆帽。
“有什么好看的,我来让你们知道厉害,把拐杖给我!”老婆子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把门关上,听见没有!”
孩子们都走了,抱娃娃的女人把房门关上。
“我正在琢磨:这是谁来了?原来是老爷,是我们的金子宝贝,百看不厌的美男子!”老婆子说。“你怎么光临我们这个穷地方了,也不嫌这儿脏。啊,你真象金刚钻一样好看!来吧,老爷,这儿坐,就坐在这个矮柜上吧,”她说着用围裙擦擦矮柜。“我还以为是哪个鬼溜进来了,原来是东家,是好老爷,是恩人,是养活我们的好人。你可得原谅我这老糊涂,是我瞎了眼了。”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老婆子站在他面前,右手托住脸颊,左手抓住尖尖的右臂肘,用唱歌一般的声音讲起来:
“老爷,你也见老了。想当年你真是棵鲜嫩鲜嫩的牛蒡,可是现在呢,简直认不出来了!你准是太操心了。”
“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件事的,你还记得卡秋莎·玛丝洛娃吗?”
“卡吉琳娜吗?怎么不记得,她是我的外甥女……怎么不记得,我为了她流过多少眼泪,流过多少眼泪!那件事我全知道。我的老爷,谁在上帝面前没有作过孽?谁在皇上面前没有犯过法?年轻人嘛,就是这样的,再加喝了咖啡红茶,就让魔鬼迷了心窍。要知道,魔鬼可厉害了。有什么办法呢!你又没有把她扔掉,你赏了她钱,给了她整整一百卢布。可她干了什么啦?她就是糊涂,没有头脑。她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会过日子了。她虽是我的外甥女,我得直说,这姑娘不走正道。我后来给她安排了一个多好的差使,可她不听话,竟然骂起东家来了。难道我们这等人可以骂老爷吗?嗐,人家就把她辞掉了。后来又到林务官家里干,日子本来也过得去,可她又不干了。”
“我想打听一下那孩子的情况。她不是在您这儿生了个孩子吗?那孩子在哪儿?”
“当年为了那娃娃我费了不少心思,我的好老爷。她那时病得可厉害,我料想她再也起不了床了。我就照规矩给孩子受了洗,把他送到育婴堂。嗯,做母亲的眼看就要死了,何必叫这小宝贝的灵魂受罪呢。换了别人,就会把娃娃撂下不管,也不会给他吃,让他死去算了。可我想还是花点力气,把他送育婴堂吧。好在还有几个钱,就打发人把他送了去。”
“有登记号码吗?”
“号码是有的,可他当时就死了。她说刚一送到,他就死了。”
“她是谁?”
“就是住在斯科罗德诺耶村的那个女人。她专干这个行当。她叫玛拉尼雅,现在死了。这女人可聪明啦,干得挺灵巧!人家把娃娃送到她家里,她就收下来养在家里,喂他吃。喂了一阵子,另外凑几个再送去。咳,我的好老爷!等凑满三四个,一起送去。她干这事可聪明了:先做一个大摇篮,好象双层床,上上下下都装娃娃。摇篮上还有把手。她就这样一下子装四个娃娃,让他们脚对着脚,脑袋不挨着脑袋,免得相碰,这样一次就送走四个。她还用几个假奶头塞在娃娃嘴里,这样他们就不会吵了。”
“后来怎么样?”
“后来,卡吉琳娜的娃娃就这么被送走了。她在家里把他养了两个礼拜的样子。那娃娃在她家里就害病了。”
“那娃娃长得好看吗?”聂赫留朵夫问。
“好看极了,再也找不着比他更好看的娃娃了。长得跟你一模一样,”老太婆一只眼睛眨了眨,说。
“他怎么会这样弱?多半是喂得很差吧?”
“哪里谈得上喂!只不过做做样子罢了。这也难怪,又不是自己的孩子。只要送到的时候活着就行。那女人说刚把他送到莫斯科,他就断气了。她连证明都带回来了,手续齐备,真是个聪明女人。”
关于他的孩子,聂赫留朵夫就只打听到这些。
六
聂赫留朵夫在小屋的门楣上和门廊的门楣上又接连碰了两次头,才来到街上。穿白衬衫的、穿灰衬衫的、穿粉红衬衫的几个孩子都在门外等他。另外有几个孩子也凑到他身边来。还有几个抱婴儿的女人也在等他,包括那个不费劲地抱着头戴碎布小圆帽、脸色苍白的娃娃的瘦女人。这娃娃的脸象个小老头,但一直现出古怪的微笑,摆动着痉挛的大拇指。聂赫留朵夫知道这是一种痛苦的笑容。他打听这个女人是谁。
“她就是我对你说的那个阿尼霞,”岁数大些的男孩说。
聂赫留朵夫转身招呼阿尼霞。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问。“你靠什么过活?”
“怎么过活吗?要饭,”阿尼霞说着哭起来。
模样象小老头的娃娃整个脸上浮起微笑,同时扭动两条象蚯蚓一般的细腿。
聂赫留朵夫掏出皮夹子,给了那女人十个卢布。他还没有走上两步,另一个抱娃娃的女人就追上了他,然后是一个老太婆,接着又是一个女人。她们都说自己穷,要求周济。聂赫留朵夫把皮夹子里的六十卢布零钱都散发掉,十分忧郁地走回家,也就是回到管家的厢房。管家笑眯眯地迎接他,告诉他农民将在傍晚集合。聂赫留朵夫向他道了谢,不去房间,而走到花园里,在撒满白色苹果花瓣、杂草丛生的小径上徘徊,思索着刚才见到的种种情景。
厢房周围先是静悄悄的,但过了一会儿,聂赫留朵夫听见管家房里有两个女人愤怒的争吵声,偶尔还夹杂着管家含笑的平静声音。聂赫留朵夫留神倾听。
“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你为什么还要撕下我脖子上的十字架①?”一个女人的愤怒声音说。
①基督徒常戴十字架,到死才脱下。这里的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要逼我死?”
“你要知道,它刚闯进去,”另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说,你还给我吧。你何必折磨牲口,还害得我孩子没有牛奶吃!”
“你得赔钱,或者做工来抵偿,”管家若无其事地回答。
聂赫留朵夫走出花园,来到住房的台阶前。那里站着两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其中一个怀了孕,看样子快分娩了。管家身穿帆布大衣,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门口台阶上。两个女人一看见东家,就不作声,动手理理头上的头巾;管家从口袋里抽出手,脸上浮起了微笑。
事情是这样的:据管家说,农民常常故意把小牛甚至奶牛放到东家草场上。现在,这两个农妇的两头奶牛就在草场上被捉住,赶到这里来了。管家要罚每头奶牛三十戈比,或者做两天工抵偿。两个农妇再三说,第一,她们的奶牛是偶然闯进来的,第二,她们没有钱,第三,她们即使答应做工抵偿,也要求先立刻放还这两头牛,因为它们一早就在太阳底下烤,没有吃过一点饲料,正在那里可怜地哞哞叫。
“我向你们提过多少次了,”管家一面笑嘻嘻地说,一面回头瞧瞧聂赫留朵夫,仿佛要请他做见证似的,“要是你们回家吃午饭,一定得把牲口看好。”
“我刚跑开去看看我的娃娃,那些畜生就走掉了。”
“你既然在放牛,就不能随便走掉。”
“那么叫谁去喂娃娃呢?总不能要你去喂奶吧。”
“要是牲口真的踩坏了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