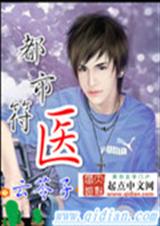都市男女错位婚姻:大校的女儿-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拿书来给我看。现在想那主任当时根本就是在敷衍我,逮着什么拿什么,不假思索,杂且乱,连当时的禁书都拿来了。我倒也无所谓,没有了目标也就不讲范围,照单全收。什么《 啼笑因缘 》、《 安娜·卡列尼娜 》、什么《 日心说和地心说的斗争 》、《 人类的起源 》、《 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乱七八糟,互不相干。
那天晚上我坐在被窝里看书,上身棉袄,脚底下蹬着个热水袋。外面天已经黑了,时间却还早,不到六点半。天太冷,宿舍里没暖气,每到晚饭后,科里的学习室便挤满了人,看报,聊天、下棋,磨蹭到熄灯回宿舍钻被窝睡觉。我轻易不去凑热闹,嫌吵。岛上风大,冬天更大,冬天的晚上尤其大,宿舍里面的风都有三级。我们医院单身汉的简易楼就坐落在海边,刮台风时的海水沫子都能飞溅到门外长廊的铁栏杆上,弄得铁栏杆上到处是被海水锈蚀的瘢痕,如同烧伤病人愈后的皮肤。
有人用钥匙开我的门。是雁南。她住在我的隔壁,每天晚上都得到我这里来遛一趟,每天每天,像医生查房。为了免受冷天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开门之苦,我给了她一把自己房门的钥匙。她也给了我一把她的。我倒没有查房的习惯,只是食欲较好,而雁南房间里总有可吃的,她正在谈恋爱,谈恋爱的女孩子一般都有一个零食的无偿供应者。雁南对零食的兴趣不如我大,雁南不馋。她那从海外( 我们是海内 )乘火车乘轮船定期进来的包裹里的东西,大部分就由我享用了,我不爱吃的雁南才会分给别人。她的那位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她对此满意,那时我们女兵都喜欢干事而不喜欢参谋。战时出将平时出相——和平时期,干事比参谋有前途,男干事女医生是当时部队婚姻的最佳配方。那人出身贫寒,这也使雁南满意。她从小在军区大院里长大,看不起她熟悉的那些男孩子,认为他们没有分量。一个毫无背景的穷孩子能奋斗到军区一级的大机关,本身就证明了他的才华和能力。我没有见过那人,连雁南和他见面都很少,他们的感情联系主要靠通信。雁南是在探家时由家人介绍与他认识的,回来后不久接到了他的信,那封信我看过,雁南需要跟人商量怎么回信,她被他的文采吓住了。信上这样写道:“时序流易,日月如梭,晚风吻面,繁星满天,军营已经进入了宁静深沉的夜,我坐在窗前,思绪陷入了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情感与理智驱动了我的手,不觉欣然命笔……”信结尾是,“愿我们的友谊,能够穿过平原,越过高山,跨过黄河,飞过海峡,将我们紧紧地联在一起!”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2)
字是没的说,非常的漂亮,柳体。我表示了佩服,我的字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学生体。然而说到雁南所谓的“文才”,我不敢苟同。雁南为此跟我争得红了脸,我还是不敢苟同。气得雁南说:“就算不怎么样,总比你我强!”
我寸步不让:“可能比你强,比我,不一定!”并当即“欣然命笔”,以雁南的身份给那人写了封回信,没他信中的词儿多,但用就在点上,雁南看完后就不吭声了。雁南的基本鉴别能力还是有的,服从真理的基本觉悟也是有的。门开了,又关上了,熟悉的消毒液味儿渐近,我没有回头,被窝塞得严丝合缝,不愿意动。雁南走到对面我的脚边坐下,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她一向随和。
“看什么呢?”她问。我正在看丰子恺的《 音乐知识十八讲 》,一本很老的书,繁体字,纸页磨得都毛了。我把书合上让她看封面。“丰子恺是谁?”她又问,我也不知道。她笑了起来,“不知道就看!”
“不看,干什么?”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会儿,小声道:“我说,你写东西挺好的,干吗不试一试?”
后来,当我的处女作在部队最高文艺期刊《 解放军文艺 》上发表了时,雁南说:“你是我发现的。”
我的处女作不到六千字,手法陈旧思想幼稚。要搁今天这个文学花样翻新,出手就是长篇,十二岁小女孩儿都能写出诸如找男朋友要找“富贵如比哥( 比尔·盖茨 ),潇洒如马哥( 周润发 ),浪漫如李哥( 李奥纳多 ),健壮如伟哥( 这个词我就不解释了 )”这样文字的年代里,我那东西只能是汪洋大海里的一个泡沫。但在当时不同,当时那的确是一件挺了不得的事。来自
医院的夸奖羡慕嫉妒自不必说,我甚至还收到了读者来信。姜士安给我打来过一个电话,其时他已调到深海一个更小的岛上。电话中他说:“祝贺你!”那几天我正美得晕头转向,不假思索或者说是有点习惯了的,就把那祝贺收下了,都没想起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我是在后来才知道他当时已经结婚了,那一刻我的反应之强烈出乎我的意料。就好比一件你喜欢的东西,虽说放在那里并没有什么用处,甚至你可能都把它忘了,但一旦有一天发现它没有了,属于了别人,你会若有所失蓦然一怔。
在连队时姜士安一直是我的施爱对象,怜爱、友爱的爱。这是我从小的毛病了,看到弱小的或不幸的,怜悯之心便油然而起。那时就常有大人说我将来适合做医生了,我想我那个当医生的理想,可能就是这样给怂恿出来的。
那个时候,我觉着姜士安是我接触过的人里最可怜的人了。刚下连有一段时间里我并不认识他,分不清他和排里的其他几个男新兵谁是谁。一律的瘦,矮,黑,一律的家乡土话。连队里农村兵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这种形象;一个连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村兵,加上穿着同一样的服装,短时间内他们在你的眼里会完全一样,如同一片树叶和另一片树叶。后来,是一个星期天,星期天两顿饭,下午,连队改善生活吃发面包子,他让我认识并记住了他。那天的包子是白面的,馅儿是剁碎了的萝卜、油条和粉丝,炊事班为图省事把包子包得巨大无比,一个足有三两,我对面一个小黑瘦子一气儿吃了十二个:两只手一手掐俩,几口一个,吃完了转身再拿,拿了三次,直到摆在两排餐桌中间那几个巨大笼屉里各剩下一团湿漉漉的土黄色笼布,才住了腿、手和嘴,满脸的意犹未尽和幸福,那时我一个包子还没有吃完,顾不上吃了,只顾看了,看得都傻了,三两一个十二个大包子啊,堆起来也是一座山啊,都吃到哪里去啦?老兵们含笑看着新兵们的吃相,时时对个眼神儿,带着过来人的优越、宽容和刻薄。新兵能吃这是常规,都是些农村来的穷孩子,多少年吃不饱饿过来的,而我对面这个小黑瘦子,似乎又是他们中间饿得最狠的一个。那天吃完饭洗碗时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回答是:“姜士安啊。”颇使我不好意思,毕竟一个排的战友相处这么些天了。才发现他其实挺与众不同的,比一般的男兵都黑,都瘦,更突出的是矮,跟我差不多高,小孩儿似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是山东农村人,初中毕业,今年十九岁。除了头一条,后两条都有点出乎意外,初中毕业在那时得算是高学历了,他这样的农村兵大多高小都没有毕业。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3)
回宿舍发现雁南正躲在上铺吃桃酥,连队三令五申不准乱花钱吃零食,这规定似乎格外针对着我们女兵,雁南不怕。雁南的父亲是军区副司令员,即使她本人品格端良,也架不住来自各级领导的密不透风的另眼相待,毕竟她才十五六岁,是个地道的孩子。除了敢花钱买,为了吃,她还敢去偷。也是我们连的伙食太糟糕了,不知别的连队是不是也这样,还是我们连的司务长有问题,一天三顿两顿咸菜,尽管有时给炒一炒蒸一蒸,再炒再蒸,咸菜还是咸菜。主食一顿大米两顿玉米面饼子,一周两次白面。姜士安们也许无所谓,比起他们过去的吃不饱来说,生活是向前进了;对于我们,则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倒退。雁南最常偷的,是猪油。趁炊事员不在,溜进伙房内部,从黑棕陶瓷罐里撅出一大筷子猪油,再舀点儿酱油,一块儿拌进热热的大米饭里,味道好极了!很快,猪油拌米饭在女兵里风靡。男兵没人敢干,女兵干这事若被发现,恶作剧而已,男兵被抓住被报告连部,那就是偷。话虽这样说,我每次干也是提心吊胆,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偶尔为之,但是,每一次,成功之后,吃的时候,我定要分出一份来给姜士安,不管多少。他太瘦太矮了,纯属营养不良。看他大口大口吃着我调制的猪油拌饭,我很满足。那满足有点像小时候为给一只没人要的小狗多一会儿温暖抱着它一块儿在外面挨饿受冻,为满足一个乞丐的索求奉送了自己的早点因此饿一个上午——是一种牺牲了肉体需要换取来的精神上的满足,雁南曾说我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去做修女。我尽其所能对姜士安好,不拘是猪油拌饭,谁家来人带来好吃的我也会把分给我的那份分他一些。我对他比对所有其他男兵都好,因为不在意他,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对他好。我所谓的“不在意”是这样的:如果对方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比如,一个个子高而挺拔,从城市入伍或者是干部子弟的人,一个当时我所认为的我的同类,我就会在意,会矜持地保持距离。
雁南在连里待了一年就走了,上大学去了,我却去不了。当时我父亲已由军区司令部二级部长调任某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正师到副师,降职使用,那个年代这类事很多。母亲来信只简单陈述了这个事实,别的没说,但我本能地知道,他们已经无力再为我们做什么了。雁南是上午走的,走的时候我正在值班。中午下班回来,雁南床上只剩下了一个光板,我心里难受极了,为了没能送她,更为了我自己。下午是我们值勤分队补觉的时间,排长让女兵班出一个人查线,副军长家的电话不通了,我就积极主动地要求去了,这种时候睡也睡不着的,与其睁着眼干熬,不如出去走走。男兵班也出了一个人,是姜士安。
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据老兵说海岛的冬天还没有这样冷过。近海的海水都结冰了,白花花一片,夜晚看时,假面具一样阴森可怖。海上好长一段时间不能通航,听深海几个小岛上的电话守机员说,他们早就不洗脸了,那些岛上的淡水全得靠船运去。后来还是海军派来了几艘破冰船,犁地也似的在冰海里轰轰地跑了好几天,才算开辟出了几条航路。那天的路面上,薄雪与冰冻在一起,又硬又滑,电线杆子朝北的一面一律半雪半冰。我们一路走着一路查,电缆没有问题,电话没有问题,是明线出了问题。明线出问题最麻烦,要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爬上去,一截一截线地试,我们从下午开始,一直查到天都黑透了,一直查到副军长家前最后一个电线杆子了,还没有发现故障在哪里。由于心情不好中午没怎么吃饭,这时候就感觉到饿了。走前灌了壶热水的,要喝时才发现水已结成了冰,军用水壶被冰撑成了一个球形。姜士安以为我渴了欲去给我要水,机关干部住宅区家家都亮起了标志有人的灯,我说我不渴就是饿令他颇为为难。是啊,要水可以,要饭——要饭怎么可以?
“韩琳,你坚持坚持。我抓点儿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