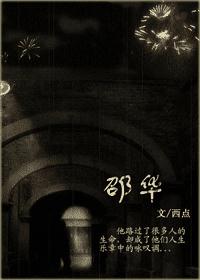琢玉成华(h,虐,he)作者:南栖-第1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浑身一个突兀的激灵。
迫人的静谧,再度笼罩住这座空旷的殿阁,一股无形的威压却无端的散发开来——佛印盖顶般,镇住形同蝼蚁的一切鬼魅。
景元觉的笑容未变,负手在身后,缓缓迈开步子,在柔软的地毯上,踱了一个整圈。末了,停在我的右肩。
令人战栗的温度忽然覆将上来。
他把我的手举到我的胸前,掰开拳心一根根紧攥的指头,严丝合缝的□来,直至环环相嵌——泛着青白的指甲和其下饱满红润的指腹,便一同暴露在视线避之不及的地方。
景元觉的呼吸就吐在耳侧,温暖而又平缓。他的目光却越过我的脸颊,聚在纠缠不清的十指之上,“那么,苏卿回来……是为了掌中物,还是伸掌的人?”
久久没有回答。
两股目光,胶着在一处相连的指间。
景元觉的手指慢慢弯曲,向下成爪,扣住我的手背。他抓得太紧,紧到指甲变了白色,渐渐让我的手僵硬、感觉不出一丝血脉的流动……然而即便这样,分毫后撤的意图,都会即刻间遭到更大的钳制。
直到我忍不住哼了一声,背后的人轻轻一声叹息,放松了一点力度,却把自己下颌的重量,压在我的肩上。
“你的沉默,有时也很残忍。”
他如是喟然。
血液回流的畅快,让我没有接口。
不过……
可不是么。
只可惜真相这种东西,有时候,更加残忍。我侧了头,垂下眸子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陛下?”
肩上的重量轻了一些,手上的压力却再没稍减。
“长夜庄……知晓了有好些年。”景元觉语调平直的说,只手捋起早晨河水匆匆淬湿的发,一绺一绺,尝试着把它们梳通。
“藏头露尾,不露真容,没什么大的行动,朝中有远比他们更紧要的眼中钉,于是,一直放任自流。”
我点了点头。
“不知道他们领袖真实的身份。以为只是勾结朝臣的江湖帮派。在这次以前,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朕。”
他的指尖滑到因为脏污打结的地方顿住,有一种撕扯的痛。
“说起来,真是命悬一线……”
我顺着他的动作,皱眉偏头。
景元觉换了一条途径,终于把发结扒通,吁了一口气。“你呢……当初相遇的时候,还以为是故意隐瞒出身的高人,查也未曾细查。”
听到此处,回想起来京路上几次不深不浅的试探。彼时他冒充廉王四子,我装作乡野隐士。两个人虚伪一路,假成一双——
不由得笑起来,“是么?”
他恶意的扯了扯我的头发,好似惩罚我的失笑。
“你同元胜聊过了。任用之后,他派人实地查访过,地籍造册上确有苏鹊其人,也就罢了。那家伙,既没有将他的怀疑忠诚的告诉朕,朕自己隐约的疑惑,也没有主动去求证过。”
其实纵有蹊跷,他大概也并不会十分在意罢。
真正强大的人,不拘枝末小节。
“谁没有一两件想要隐瞒的事。”景元觉垂下本来捋发的手,环在我的腰间。另一只推着我的右手,轻轻扣在我的胸上。
这种类似拥抱的姿势,带给人仿佛感动的触动。“若然不是天意,也许终朕一生,都不会深究。”
……
柔软的温暖分开缭乱的发丝,落花般,悄悄印在后颈上。
周身难以抑制的颤抖起来,一刹间就那么茫然无措的立着,胸膛起伏而不能自己。末了,只在右手上使了力,熨帖他掌心的热度。
“我信。”
“刘玉,把他带过来。”
景元觉淡淡的吩咐。
门口的人应了声,退出去。再到两个人的脚步响起来,其中一个在门口停步,一个一直不停,直到进入大殿。
进来的人撩起衣摆,双手伏地,垂首跪在我的面前。
当然,使他行如此大礼的对象并不是我,而是那位站在我的身后,维持着相拥姿态未变的帝王。
我漠然看着地上此人。
青衫标识了他的身份,羽冠衬托着他的风骨。重华寝殿高贵如斯,若非亲信和倚重,纵使裂土之王分疆之吏,也不得其门而入。
一介布衣寒士,终至登堂入室。
“抬起头来。”
景元觉的声音越过我,命令着来人,“好好看着朕。”
来人的眼睛在抬起的一瞬间睁大,黑沉的眸子定格在仰视的角度,颤动不休。开启了一半的口梗在那里,只随着呼吸,上下开阖。
这种君臣暧昧相拥的画面……
即使最镇定的人,也难免裂出一丝惊讶。
景元觉松开了环扣腰身的左手,却不罢休一般,轻轻托起我的下颌,迫使我慢慢偏了头,对上他的侧脸。
那投来的目光专注而用心,看来就好像水一般温柔。然而实际上……这么近的距离太过分明,不带有一丝的温度。
他终于瞥了开去,对着下方。
“你知道你指认的这个人,朕同他的关系吗……”
他问得几乎漫不经心,好比茶余饭后的闲聊。甚至左手还托着我的下颌,食指轻轻上挑,像是对待一件心爱的珍宝。
“你知道,你今天在这里的每一句证词,无论是真还是假,都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臣为陛下尽忠,无愧天地,虽死不畏。”
难为此人,惊骇之后速速镇定下来,竟能一如当初理直气壮策论天下大势,仍旧挺直了他的腰杆。
景元觉垂眼看着他,浮出一捋浅笑。他放开托颌的左手,却仍然扣着我的右手,并肩站到我的右侧。
地上人平视着前方。
“千金之躯,不坐危堂,何况陛下枕席之侧?苏鹊此人者,明王义弟,长夜庄位次行二,狯猾倾险,设谋权变,更兼以色惑君,万万不可轻留!”
我不禁失笑。
此乃诤诤血谏,是为罕见。
瞅一眼景元觉,他亦听到最后一句,将唇边一捋原本似有若无的浅笑,盎然扩大了几分。
再低下头来,忠和奸的分别,油然而生。有些事,自见到这位大人的那一刹起就明了开来,明了到此刻我都懒得再问。
可惜答案必然曝露。
“当初在廉王家里招募人才,”景元觉不动声色的在我身边评说,“二哥要是知道朕自己挑拣了你,怕是也不必再费尽心机塞进一个他……以致最后为了一颗棋卒,弄得大事皆休。”
等他悠悠说完。
我蹲下身子,与那人堪堪对视,“失敬,不知庄内行几,郭大人?”
郭怡的目光不避不让,梗脖昂首道,“蜀中无名寒衣,入京蒙混庶几。本来不在庄中,明王以利相诱,细作棋卒之辈,何来所谓行数?”
刚要发难,侍郎大人好似洞察了我的心思,冷然一道寒光射来,接续道,“——郭怡心中,唯陛下一代明君,行事不拘一格,眼光深远独到,才是我大覃功业未来之幸,是百姓社稷千秋之福,是臣郭怡衷心所认之主!”
呵,好!
怒极反乐,若不是景元觉还牵着我的手,我就要为他击掌赞赏了!
就剩下一个问题。
我拘起剩余的笑意,轻声的问他,“七月初八那天晚上,你也在那里吗?”
郭怡略带疑惑的望我一眼,随即点头。
如此便罢了。
景元觉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起来。突然起立头昏眼花,向后退了一步,倒靠在他张臂等待的怀里。
景元觉低头瞥了眼跪在地下的人,目光沉静而又冷漠,似乎此人刚才那一番慷慨激昂的表白,全然未入他的耳中。他连一只手都懒得抬起,只向门口的方向,稍稍侧头,“滚下去。”
郭怡对这侮辱性的命令毫不动容,他立即双手着地叩了一个头,躬身面对着下令的人,膝行而退出。
我看着他这样一直退到门口,起身跨过门槛,却站在门外忽然拱手,“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侍,苏大人执迷不悟,纵使才情盖世,又能行路几何!”
“滚!”
景元觉大吼。门外等候的禁卫立即涌上来,架上这位门下侍郎的肩膀,不由分说将他拖将下去。
偌大的寝殿里兀然安静,又剩下我们两人,无言拥在一起。
时间过得既迟缓又迅疾。即使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也不会使人感到沉闷。
我渐渐少了站立的力气,所有的重心,都倚靠在他的怀里。
“苏鹊……你究竟是什么人?”
景元觉在我耳边轻问。
“……你将他们,关在哪里?”
我挨着他的颈侧细语。
半晌。
阳光斜扫殿堂,有些刺目的迷了眼睛。
我叹了口气,“即使我不说,过不了多久你也会查到的。”
景元觉的胸膛微微颤动,似乎是发出无声的笑意。他接着俯在我的肩上,几乎是咬着我的耳朵,说,“在刑部大牢。”
未曾想,这般轻易得到了答案。我挣扎着挣脱了他的钳制,他竟然也没有多少用力。
只是追着我的步子,不急不徐的唤,“你要去哪?”“你去哪里,苏鹊?”
跨过高大的门槛,门口杵立的禁卫纷纷对我行使注目礼。然而没有主子的命令,他们手持着兵刃脚下生根,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去我该去的地方。”
秋阳高照的天光,瞬间闪花了我的眼。
铺陈着红毯的石阶,像一条血色的玉带,宏伟倾流直下。我摇摇晃晃走在上面,松软的绒毯,似乎能包裹住自己的脚踝。
身后有一阵混乱的人声。
好像有什么人在那里惊呼,有什么人在跑动,又有什么人在试图劝阻。
我已经走到这条血路的末尾,脚也不曾停步,头也不曾回过。
直到耳边风声忽疾——
几根发丝飘落下来,徐徐坠在绒毯上。
像是斩断的墨绦,无力的蜷曲在我的脚边。
有股细小的热流,从右脸颊烧灼直下,滴滴溅在地上。
往前两尺,一柄寒光莹莹闪耀的长剑,笔直竖插着,没地寸余。
我呆愣了一瞬……
虚软转身。
正对上高台众人慌乱拦堵处,景元觉猛兽爆发般凶狠的指天怒喝,“再放你走一次,朕有如此阶!”
八月十一、十二、十三,接连留于重华殿。
许是忙于清剿无暇歇息,许是避过内奸而不愿见,反正自那日正殿门前拔了侍卫配剑、惊心动魄的当空一掷后,再没有见到主人的身影。不论如何,我这个郭怡口中的惑君逆臣,在空荡荡一座帝王寝宫里留守,坐镇偏殿东阁。
上下三层,重华高台。入住当日就有满满三箱用件自中书侍郎府迢迢运来,其余吃穿,更一应俱全。
我不愿自比那金屋藏娇的美姬,也不敢再轻易揣度对方的想法。无论从这里哪个角度往阁下看去,都是一重重高大的黑衣禁卫围在周遭,安然静默,明刀真枪。
即便是拘押软禁,名节扫地——
事到如今,能控制的也着实不多。
每日有固定的客人到访。
长夜庄逆反案的主审之一,宗正寺景氏宗族当家、统领廉王府的主事,世子景元凛。
“明王现在何处?”
“入朝至今,何事经手外漏?”
“牵连涉案的官员,可还有什么补充?”
……
他每每一日三问。
回答他的都是沉默。
说起来,此君与我也只是泛泛,兼之性格严谨,做派老成,并不是可与交心之流。而且,即便他屏退众人,


![(HP同人)[HP]世界第一暗恋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5/501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