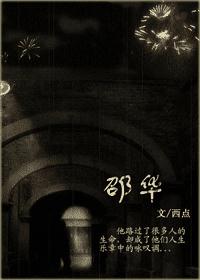琢玉成华(h,虐,he)作者:南栖-第1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随同的汉子得令燕一般矫健跃出了巷子。为了避免万一的牵连,他先是翻进了隔壁院墙,而后大咧咧推门而出,醉汉一般摇摇摆摆晃荡着,一路横行到羽衣楼隔壁的赵记包子。
“呃!”
十四打了个响亮的酒嗝,一条花街都能听到。他摸了摸子虚乌有的肚腩,岔开双腿立定,举手作势欲拍门——
看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
突然有人捂上了我的口,将我微微探出的身子向后狠拉,就在此时——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对角巷道里一闪而逝的寒光。
那是兵刃的银光!
回首惊见闻哥脸色凝重如铁,电光火石间,已拖着我后撤了数步。
十丈外响起酒醉汉子大力拍门的“梆”、“梆”、“梆”……一声唿哨过后,便是万丛利刃破空。
小半个时辰兜转,一路仓皇奔波,闻哥额头挂着大滴的汗珠,我偶尔帮把扶他腰际的手,缩回来经风一吹,满是黏稠的凉意。
无人有心情说话。
直到眼前的景色再度熟悉起来。我们在暗巷里靠墙站定,双眼发红的二十一不待他人说话,一个抱拳,扭头闪身上前,敲响了门扉。
笃,笃,笃。
压抑的叩门声,在夜色里回荡。
许久许久,久得我们都放弃了希望,方闻“吱呀”一声轻响,厚重老旧的古刹木门,缓缓打开。
一身布衣的熟脸大和尚淡然面向来客,手中提笼散发着橘色柔和的火光,显得那般遥远而不真实。
披衣而起的老方丈,把自己的禅房让给了我们。
事到如今才从赵七叔口里知晓,此间老寺多年前风雨飘零之际,曾由闻哥母后出资修缮。出家人不闻外事,难断人是人非,此后只为感念先人恩德,随时提供一个方便之处。
老方丈忙着唤人烧水,取来伤药和棉纱。
闻哥撑剑坐在炕上,方便我们替他割开外衣,剔出那嵌在肉里的甲片,一块块扔在铜盆里,发出当啷的锐响。
我手抖得厉害。
要用左手握了右手的腕,右手才稍微听话。有时动作轻了,取不出角度刁钻的甲片,有时动作重了,又会将歪斜的甲片推向腹内深处。不一会,就是满头的汗。
这时听到了轻轻的笑。
抬头便看闻哥望着我,牵起嘴角。本来苍白的脸因着这突现的一层容光,添上许多焕然的生气。
“怎的?”
我不解的问他,不明白腹间尚是血肉模糊、目不忍睹的一片,为何忽然竟能心情愉悦如斯。
闻哥听话略略一顿,又抿了抿唇,渐渐敛却唇间笑意。然而一对凤目里的眸光始终水一般鲜亮的漾着,初看似深又似浅,细探如喜又如悲。
我不觉停了手上动作。也不知这无声的一瞥里,究竟有多少难解的思绪,有多少难言的话语。但是终究千头万绪,千言万语,也都化作一句喟然叹息,“不想临到头来,多年经营,都比不过当初一介无心的善念……”
他阖上了眼。
联想如今落脚之处,可不其然。
我看着赵七叔将用妥的铜盆撤下,又倒满一盆热水端回来,绞了巾帕,替他擦拭伤口的血污。完了,不计成本的抹上厚厚一层金疮药,再用干净的棉纱圈绕裹好。“出家人慈悲为怀,何况施恩在先。佛门清修之地,本来不宜沾染血腥,不过……也算是因果天定,一报还一报。”
闻哥睁眼莞尔。
“你不懂。”
他说。
子夜前收拾妥当。闻哥倚坐在炕上,和赵七叔小声商量着天明后派人出去查探,寻机离开京城的事。千头万绪也需一丝一缕开解,此时最忌的,反而是惶然乱了阵脚。
我原本靠在一边,听着听着,偶尔插两句嘴。人静了不一会,却倦意袭来眼皮像落了千斤重坠,粘上再睁不开来。
醒来时簌簌发寒,正是夜半。身上披了一条薄毯,赵七叔在一旁炕上发出绵长的鼾声,本该是闻哥的位子,却不见人影。
出了门,抬头月光如晦,穿透一层笼罩在京城上空的烟雾,斜过大雄宝殿的屋檐,隐约撒进禅院,照见地面上一对石灯笼拉长的竖影。
我裹紧了身上毯子,慢慢踱出禅院。远处偶有几声犬吠马嘶,寺中却一派静谧无声,依稀能见大雄宝殿右进檐下,一个握刀守夜的身影,孤零零立在阶上。
怎样?
我用口型无声问其人。
二十一轻轻摇首,表示此处院落暂且无虞。看见我继续询问的眼光,他顿了顿,向殿北抬颌。
便寻了方向去。
寺后有一座藏经浮屠。木制七层宝塔,京中也不多见。当年初建时想必是宝相庄严,登临拜谒者络绎不绝,然如今老旧失修了,檀越不再、修葺的善款也跟着失去着落,平日里便只能高高锁起,谢绝香客参观。
那座古旧的高塔下,月色如水,泼洒青石地面。现如今一人孑然而立,正是那当初施善的子息。
“还伤着,怎能一个人乱走?”
我急怒攻心,为着这不知珍重的人。
闻哥闻声便知来人,也并未回头,反倒向后伸出一只手来,“……那你便扶我,上去走走。”
我未曾答话。
以他现在的状况如何也该是卧床,而未来的日子,必将有少不了的颠沛奔波,能缓息一刻,还怎生浪费得了。
“喊不动了?”
闻哥的手停在半道,等不到回应,慢慢翻向半空,像是半作无奈又了然的摊手。“本来我想……许是老天怜我奔波半生,眨眼又要远离,让宿在寺里,天明之前……望一眼这京城土地。”
还是败下阵来。
用从老方丈处借来的钥匙开启塔门,铜锁方落,一股腐朽尘封的味道扑面而来,呛得我掩鼻低咳。
握着的闻哥手转了方向,他几是不自觉在我头上揉了揉,“……打小便对灰尘敏感,到了如今,还是这样么。”
这一句话出来,我们都愣了愣。
……
他回头先行登上了梯级。待我回神追上去,搀住他的手臂,方才慢下脚步,站在楼梯中间。“初上山时,大家都有心事,却都喜欢围着你,跟你说话。因为你这小子,先是生病烧哑了嗓子,后来是打心里闷着不愿意说话……在云雾山上,比起满山的松柏,更像真正的木头。”
脚下的木梯吱呀、吱呀发出不堪重负的嘶叫,似乎在抗议客人硬来。闻哥在转弯的过道停了停,给它们一个喘息。
我情知他说的过往句句是真,还是忍不住反问,“……是吗?”
闻哥反手拍了拍我的手背。
“那时你小,我们记忆尤深的事,不知也还记得。”他站在第一层的塔楼,任夜风透过窗棂吹起披散发丝,好似悠然月下,与人笑说往事。“你芸师父有时回庄,会抱着你絮叨外面的事,说着说着,总会回到她和范师傅的故事。”
“我猜,她以为你烧成了小傻子……”
“你的记性却很好。”
“因此,当她第十次和你说起那某名山剑派掌门的独女,放弃十载修行追随一个上山游览、名叫范楚云的年轻才子,无怨无悔用了十数年修得正果的故事的时候,你呀……没有能够忍住。”
我知晓他说得是哪一回事了。为了这一遭口头痛快,后来的年头里,没有少被人家记恨。
此刻,我含笑听着他说下去。
“当时你这小子突然张口,‘你的号取得好。’”
“芸娘瞠目结舌,整个人懵了,也不知是该为作哑巴的你突然开口说话而惊喜,还是该为作傻子的你说话如此没头没脑而哀痛……”
“偏你这孩子,丝毫不介意周遭的状况,继续道:凌‘云’凌‘云’,所以大娘你吃定范楚云——’”
我跟着他笑起来。
尤记得当时凌云仙子一惊一乍间很没有武德的松了手,我啪的摔在地上,小屁股差点裂成四半——早知道开口说话的后果是这样,我就不说话了。
可是彼时,芸师父根本没空理会我的怨念,她疯疯癫癫的跑出去,举起双手满院子大喊大叫,又哭又笑,“来人啊,来人啊!庄主呢!小孩说话了!死小孩终于说话了!我养的死小孩终于说话了——”
……
是这一刻,笑中犹带泪痕。
我们上了二,三,四楼。
小小的普济寺,渐渐尽收眼底。
闻哥说明明出身江南诗书门第的孩子,山上养了两年,尽学会了上树掏鸟蛋,下地偷山参。
闻哥说初来时多么腼腆知羞的孩子,山上养了三年,也晓得了背后涂人乌龟,嘴上蜜里调油。
闻哥说双手抱在怀里不过一团大的病秧子,山上养了四年,怎能梁上泼人一瓢凉水,跑得比兔子还快……
闻哥说,“弟不教,兄之过也。自打你跟了我起,好像一天一天,就越发远离君子之行。”
可不是呢。
他一巴掌拍在我的脑门上,冰冰凉凉,“你这叫人不省心!”
第五层,谁也没有说话。
那年一别山麓,叫无忧的孩童明白此人不仅是一人的闻哥,还是山下的明王,是众人的期望,是终究要做大事的人。
第六层。
闻哥走得急,说得多,扶手在墙上,气息便有些沉重,“你记不记得,前年我去广平,瞒过他人同你夜游西山。那时你已人称北地白莲,名扬关外,偏偏赏爱那里山湖草木之流,无论如何也要带我去看,说是……”
我拍着闻哥的背,突然间畏惧起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可惜,他并没有停止,“愿弃人间逐鹿,甘于泉石之栖。”
他身上特有的淡淡松香味,透着些许悠远的愁。
“……今日万事成空,始知此言真义。”
灯火阑珊的京城,在我们脚下绵延。
她好似浓妆的妇人,闭门歇户,方能洗尽一身铅华,呈现蒲柳般的素姿。又好似疲累的老人,追忆往昔般,早早伴着落日陷入无言的睡眠。
无论哪般,此时夜深,而这一座中原大地上最宏伟最雍容的城池,酣然正到深处。
一片沉重压抑的寂静里,彷如什么也不能打破这份广大的包容。放眼望去,只有方圆数处隐隐燃着的烟柱扭曲着线条缓缓上行,不慎遮蔽了天空某一处本该亮丽闪烁着的星辰,才提醒了尚是清醒的人……
这个夜晚注定难忘。
浮屠顶层的扶手落满了积年的灰烬。素来爱洁的明王殿下,却似未曾发觉一样,撑手在栏上,眺望广袤京华。
高处的回旋风撩起他飞扬的发丝,偶尔露出侧脸俊朗坚忍的轮廓。
他出生在这片土地上,在这里收获过与生的荣耀。他曾经在东北苦寒之地,浴血守卫过这里的安危。他也曾经被这里狠心的遥遥放逐……是爱是恨,他都比我这个匆匆过客对这里有着更深更厚的感情,也许终其一生,都无法割舍。
……我自自己的忧思中回来,闻哥却已转身望着我。
“鹊儿,”他轻轻缓缓的问,“为什么?”
我愣神的看着他。心中隐隐知道他问的是哪一个,但又莫名的,不希望当真需要回答。
闻哥等了一刻,一双手拢在腰前,反倚在靠栏上。背后如洗的月色,将他的身影拉得修长。两片薄唇闭了又启,问道,“为什么,和他?”
到了此时,无心隐瞒。只是有时候天下事皆有因果,偏偏就有那么一两个独外,是任你逐本朔源,怎样也解释不来……
我想缘分此事,必是其一吧。
心里的那根弦,起初只是抖一抖,动


![(HP同人)[HP]世界第一暗恋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5/501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