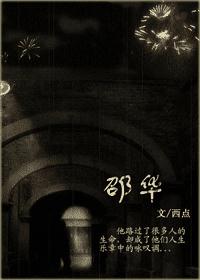琢玉成华(h,虐,he)作者:南栖-第1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什么!”
后边的人动作更快。
因为……
黑气四塞,衣裳涨大如鼓,一时间咫尺而不见真颜。几句话当空嘶喊着吼过,人吃了满满一嘴的土。
眼里也进了沙。
就在腰上劲力一松,我几乎能挣脱的时候,又有人猛的扑过来,结果两边的力气一使,整个人贴饼样给按在了墙上。那新来人大喊的唾沫星子,几乎都喷在了我的脸上,“来人保护苏大人!”
沿途屋上的瓦片噼里啪啦的作响,击碎的瓦砾下雨般的往下掉,砸在人的脑壳上。有人把不知是外衣还是毯子之类的东西搭在头顶,用力按着我的头。
终究进了附近的屋子,房门一在眼前阖上,遮天蔽日的黄沙和咆哮嘶吼的狂风就被隔绝在外。
几人都松了一口气。
定襄王一身狼狈,满面灰尘,也顾不得其它许多,“起黄雾啊!你们还在外面作甚!没看见下人个个都跑得没影了吗!”
也顾不得屋子里的其他人,我揪着他,紧紧盯着他,“天降不祥,后天的仪式还作吗?”
“你……”
定襄王迟疑的瞪着眼,一个“你”字开头,半晌未曾接话。我心知大概是此时满头枯叶,状似疯魔的样子太过骇人,看来就不似个能共语的常人,可是已等不及,“说啊!王爷!”
“我哪里知道!”
定襄王一急,干脆甩手推开,面色暗沉难辨,“京城起霾雾也不是没有过,轮不到我等在这妄言,待皇上归来后,一切不是自有定论!”
整屋皆是无言。门外风声却摧拉枯朽,如同万马过境,烈烈不休。
“子贺但听圣上安排。”
背后一把沉着的声音就在这其中响起,平静得不合时宜,“如果君命不改,还望各位海涵陋室残破,仍能不吝出席。”
心又凉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风声渐渐转小,天地隐约有平复的迹象。屋里的人纷纷松了气,三三两两的交头说起话。
我仍然看着定襄王。
旁人的议论,全不入耳中。定襄王方才说的话别人也许没有听清,可是我靠他最近听得最明……他的话里,什么叫做归来?
定襄王始终避着我的目光。
外面天光越来越亮,几乎恢复了傍晚的晴光。几点雨滴打在窗纸上,却稀稀落落,没有了风疾时磅礴的气势——就在我以为他再也不会说话的时候,定襄王转头偏向西方,轻声舒气,“皇上在晋陵军营犒军,稍晚便归。”
就登时觉得腿一软……
若不是身后张之庭反应快,差点坐倒地上。
晋陵军营,晋陵军营——
返京神威军的大营……
不能乱。
不能乱啊。
“苏鹊?”
定襄王的眼神已经带了惊讶和诧异,我扶着张之庭慢慢站起来,低头摆手,避过他伸臂探来的关切。
明明心里已经乱成一团麻,此时还要装模作样。谁也不知道,我却必须镇定,因为只要此刻的言行稍有不慎,就会害了他人。
好在恰在这会,额角有什么黏黏糊糊的液体缓慢流下来。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心里也有数。
“这……方才打到头了?”
定襄王张望着,本不确定的语气,在一个停顿后焦灼起来,“来人,大夫呢?周大人!快叫人来看看!”
这下连主人也惊动了。黄风过后诸事皆忙,可怜那一个万般无辜的准新郎,还要被到贺的王爷吆喝着,分出心招呼砸伤的客人。
其实只是瓦砾掉落不巧正中,一点破皮的伤。但我一声不发,闭目坐在太师椅上由人清理,就连其间张之庭掐住我不放的手,也未曾费力去挣脱。
我需要时间冷静想一想。
顾不得许多了。
乱轰轰闹过一阵之后,都看出左右无甚大碍,才得以向主人辞行。
周子贺自然要客气一回,但张之庭收到我的眼色,跟着站起来,向王爷和尚书一拱手,“周大人府上尚需要时间收拾,后院的琴乐演排也不得不延后。正好下官和苏大人有手谈之约,送行之事就一并代劳了。”
他应对得自如。
两人上了车。
帘子一放下,我便压低了声音,“之庭,今日苏某一事相托。”
马车轮子辘辘转动,轧在京城青石板铺就的大道上,轻微摇摆着晃动。
对方闻言好似僵了一下。既没有立即接话,也没有启口否定的意思,反而是陷入了无声的沉默中。
我腾出一只手来,扶住了额。
记忆里,有过插科打诨,有过彼此挖苦,却从未曾用过这样慎重的口气,和对方好好说话。相交几年过去,更从来不知道,自己会有等着他的沉默,心里却打起了鼓的时刻。
……是不知晓啊,在他心中的苏鹊,那份把酒闲聊、对弈合奏的交情,究竟重在几何?
马车又转过了一个路口。
我们的身形都跟着转弯的弧度而朝外歪斜。张之庭的头借机从车厢的阴影里偏过来,才发现那双漂亮的杏眼一眨不眨,瞳仁在夕阳末尾的霞光里,像是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辉,“……好。”
我本来要说的话咽在了肚子里。苦笑道,“你不先问什么事的吗?”
此人缓慢却肯定的摇首,再来,嘴角竟是微微牵起了一抹笑——好似天下间无论什么样的允诺,此刻只要开口,都是云淡风轻的易举。“我答应你。没有那个必要。”
额上的破皮处隐隐作痛起来。
我挑开车帘看了看,车行迅速,已经越过东市,上了平安大街。再往前走,就要横过朱雀大道,在西市往北拐,直到禁城附近的甜水巷了。
回头,张之庭仍旧静静望着,我点了点头。
“说起来,当初你我萍水相逢,全因投缘而共处,四五年一晃而过,若回首论起,还真觉如一场好梦。”
他听着听着,渐渐敛去了笑容。
大概是说话人的语气,没有事前试想的古井无波。
“你看,本该肝胆相照的相处,可惜苏鹊多心擅疑,从前便有诸事相瞒,还望……你能原谅。”
我一鼓作气的说下去。
方才莽撞乱闯时,嘴角也不慎被倒霉的枝条抽到,说话时就会忍不住痛得嘶嘶抽气,所以必须足够勇敢和用力,才能在马车的颠簸中,将每一个字都吐得分清。“将来若有什么万一,请你但求自保,不与苏鹊此人再有牵扯。”
“砰咚”的一声巨响,车厢左右摇晃。
是张之庭猛然之间站起来,脑袋撞上了矮窄的顶棚,“你说什么!”
我扶住车壁,“君子重诺,小人毁信。”
“胡扯!”
他猛虎下山一般扑过来,双手揪住我的衣领——经这么一折腾,车子摇晃益发厉害,外面周家的车夫疑惑的唤。
“两位大人……”
可是车里叫嚷的声音更大,以致完全压过了他,“就小人了又怎么样!都由着你,都由着你!就你说了算?给我把话说清楚!”
谁承想优雅如乐卿大人竟也会有胡搅蛮缠的一天。
“你已经答应过了。”
在动手方面也许及不上他,可是口头的工夫,乐卿大人又怎么比得上苏某,“有本事现在就掐死我,不然当断则断——停车!”
本来以为大庭广众之下,乐卿大人难免会顾惜面子自重身份,然而跳下车来,拉拉扯扯的境况也并未好转。
给了周府惊骇的把式一吊赏钱让他回去。我绷着脸甩手在平安大街上大步流星,后面张之庭小跑着紧跟。
路上沙尘瓦砾堆积,一些临时建搭的摊棚倒塌了不少,沿街有许多小摊小贩在躬身收拾满地散落的物什。即使是上规模的酒肆客栈,境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旗幡、招牌之类倾倒无数,折断的竹竿和木棍、掉落的匾额、灯笼,滚得满街都是。
不过虽然经历了少见的天象,京中百姓一来毕竟见多识广,二来多年谈不上富饶但算作安康的日子过下来,个个神态平和,忙着收拾自家的一摊凌乱,偶尔抬头骂几句不长眼的老天,倒无人真正露出什么异色。
京畿卫大概已经接到了指示,出现在各条街市上,分成一个一个小队巡视安民,身影往来不息。尤其是人多混乱的西市,派驻了不少兵士和马匹候在门口,一面指挥民夫入内,一面则肩挑手扛,往外帮着清运杂物。
遍地狼藉中,隐约井然有序的样子。
我在往西去的最后一个路口停步。瞧着忙碌的军民,生出许多惭愧。
百姓求的不过是安生的日子。可惜啊,身在上位的人所经所营的事,却多半掺杂了私利和腌臜。
一路走来,张之庭跟在我后面不说话。我也就铁了心,当作他并不存在。到鼓楼临街一个馆驿里租了匹马,牵到西华门之下。
满身披挂的京畿卫率们,却将高大雄伟的瓮城团团围住,对前面排着每一个欲往西去的人亮出威风的长枪——
“戒严了!风沙过境,不利出行!接上峰命令,一律暂停通行!一律暂停通行!”
……
转身在街上张望了一下,紧贴着城门处,有间供人歇脚的客栈。店里的人正将摇摇欲坠的挂幡重新绑定,上面粗笔“杜康”二字,不一会儿又迎风招展起来。
我将马缰丢给小二,在店里靠街的桌子边坐下。看看天色,摸出一锭银子。“做两个小菜,温一壶酒。”
这一坐,人来人往,及至人去楼空。
就是几个时辰。
张之庭从我进来后就抽了条板凳坐在对边。他使唤着小二,先后加了几个菜,不断烫着酒,自顾的吃食。我没有赶他。
……
金乌隐没于西方,玉蟾升起在东方,渐渐上了当空。
时间过去的越久,我的心里就越发的沉重。
谁知道城墙的外头,发生了什么……
灯火通明的街市,慢慢的,一点点,减去了妆点的辉煌。
白日里被霾雾打乱的生活,经过辛勤的努力,入了夜,此刻也恢复了正常。街面的铺子早早收了摊,打烊休整的店家,也已经合上了门板。风尘之后,还愿在街上闲晃的人本就稀少,而之前对日落前出城还抱着一丝期望的人群,在天黑后早已从西华门前散去,只余下青黯的城门上京畿卫率年轻的身影,在火光映照之下,平添冷峻挺拔。
大街后面不远的民宅里,间或会传来几声幼儿的啼哭,还有醒来的父母轻唤安抚之声,一段若有若无摇篮曲的调子……
更衬托得这座广大宏伟的城池,一派宁静安谧。
其间唯一的打扰,是客栈的小二不停的来催,语气由好声好气到按捺不住,终于在接近子时的那一次,被乐卿大人啪的一块佩玉撂在桌上,唬得默默退场。
梆、梆、梆、梆……
敲锣的声音,伴随着打更人老迈悠长的调子,“四更了——四更了——”
一声声,幽荡荡的,彷如唤魂。
我从臂弯里抬起头,眼前仅剩的一盏油灯,灯火如豆,再看对面的位子,已经没了人影。
……
虽然算是希望的结果,心里却不可避免的失落了。
撑着桌角站起来——然而稍微侧首,一双骨节分明的手,就倒提着衣角悬在半空。顺着往上,是它们主人偏侧往边的脸。
脑袋上的破处一抽抽的痛起来。
“你……”
我开了口,又咬住唇。这算是什么样的时刻,由不得我稍许感怀。必然,还是什么都不说得好。
张之庭转过来的眸子,就在没有等到的下文


![(HP同人)[HP]世界第一暗恋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5/501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