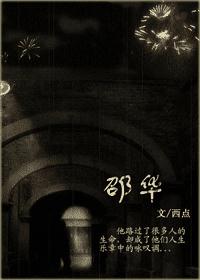琢玉成华(h,虐,he)作者:南栖-第1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里面一个俊秀英武的少年,一个豪放壮硕的大汉,早已左右对坐,杯箸开动,面前是见底的酒碗和丢弃的骨渣。
“王爷,这么早就出来望夜街了。”
对我这一句实为“你闲到就等在这里候消息”的揶揄,那坐在首位的锦衣大汉挑眉尴尬的一笑,随即又极为洒脱的向外招呼,“来人,加座!没见到爷有贵客到了吗?”
张之庭在这种场合远比我有教养。
他拉下一张看不出表情的长脸,弹了弹衣冠,老老实实对这两个人依次行礼,“卑职见过定襄王,见过齐小公爷。”
齐鹏此时酒后的晕红已经有点上了脸,白面微醺,热汗略现,敞着衣领扶膝盘坐,颇不似不久之前还在外带兵杀戮的一方将领。见了我们,他微点了点头,不自在的把目光往里瞥去——差点叫我发乐,不想经过了几月的沙场历练,他竟然还保留着当初那种少年人既骄傲又羞涩的性子,实在难得。
我捅了捅张之庭的胳膊,两人也不再客气,不分主次坐进桌。
开口之前,景元胜先是目光炯炯的在我面上徘徊。
他的目光如此直白,直白到张之庭频频侧目,终于惹得我不胜其烦,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点头。
王爷于是抚了抚肚子,顺眉顺眼,呵呵畅笑起来。
“来,来,都是自己人!齐鹏这次初战告捷、家里好日子将近双喜临门——说起来,你们二位还是他大大的媒人……好不容易逮上了,不喝个痛快怎么行?”
我们一直喝到月上梢头。
入夜后,京城晚市的繁华灯火就在窗下不断延伸,蜿蜒燕川中的桨声船歌就在楼边远远回荡,杯中温热的琼浆,让人的精神放松,充满愉悦。
齐鹏得胜返京,满心喜悦的齐太夫人,早已和得婿成龙的广平郡王眉开眼笑的互称亲翁,过了礼聘,将在七月的吉日成婚。
比起今天达成的那件牵扯,这一件,既真且喜。
席间,我们就由这桩百年好合、福泽绵绵的事情说开,提到了边疆的战事平息,谈起了京城的安治稳定……更展望了太宗遗业在当今天子的治下,也许三年、五年,也许十数年、数十年之后,仍旧传承在这片大地上的王朝,是怎样的面貌。
我们都知道,但凡国力和文化都达到某种程度的国家,才会展现一幅歌舞升平、又波澜壮阔的时代绘卷,在历史反复曲折的洪流之中,留下一道粲然夺目的记忆。而说不定,今日瑶光楼上在座的几位,正是恰恰能够拥有那么罕见的一份幸运,生而亲睹,并赶上成为这幅美妙的绘卷之上、风流尽显的人物之一。
说来我与定襄王或是齐鹏并不亲近,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个夏日的夜晚,借着酒意,谈笑尽兴。
站起来相扶出门的时候,头都有些晕乎乎的打转。
定襄王饮酒海量,饶是此时舌头也大。出门时,抓过楼下唱曲的父女就给了个银锭,拽着人家一脸窘迫又不敢用力挣扎的老爷子,结结巴巴唱个不休,“若叫那太白在……左,二……二郎在右,那哪……哪吒金咤……显化无……边,率土普天无不……乐啊噢噢……河……河清海晏……穷……穷寥廓 ……噢……噢啊……”
我摇着折扇,左摇右晃看得极欢。
直到乐卿大人眉头倒竖,捂耳跺脚,在门口围观的百姓中硬是分出一条道来,将人一路横拖回府。
进了甜水巷,到府门前,对着门口一只石辟邪一只石天禄,我呵呵笑着原地蹲住,任张之庭死拉硬拽,再也不肯挪步。
“你丢不丢人?”
他指责我,用脚尖踢我。然后又回头,冲周围模糊的人影猛喊,“去去去!有什么好看!”
我抱住一只石兽,揽在怀里揉了揉,又硬,又热,却乖乖不动,比损友的臭脾气,好上许多。
张之庭把手搭在额上,仰天长叹,放下来,依旧是怒气冲天。“喝那么多干什么!酒量很好么,跟练家子比!”
我对着自家石兽叹息,不忍看他再当众咆哮下去。
“走吧……”
“好,走啊。”张之庭前胸衣襟汗湿了一大块,脸上也满是汗水,神情是狰狞又憋屈,“起来!这边!你还知道要走?”
这话说的……
真逗。
我就咯咯笑了,结果腿又软,只得冲他招手,等他把身子弯下来,头低得平着我的高度,才好心好意的告诉他,“……你走。”
“什么?”
“嘘,”这是一个秘密,需要私下里,静悄悄的说,“……你走,远远的,快快的,不回头。”
张之庭半蹲半站,傻掉了。
他张着口,瞪着两只眼睛,在门笼的灯光里圆圆的,好似一对铜铃。
周围聚集的看热闹的闲人渐渐多了。落入他们眼里,四品大员蹲在家门口耍酒疯的场面,一定很是难得。
“你喝醉了,对不对,苏鹊?”
乐卿大人问话。他问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出口。也不知是自个痴傻,说得不快,还是怕说快了,我听不懂。
但我使劲点头。
有自知之明,是我的长处。
“不。”
张之庭摇头,脸上带着犹疑,语气却笃定。他伸手要摸我的脸,我眯着眼睛看,在要碰到的时候,忽然灵活往旁边一让。然后嘻嘻笑着,见他落空的手抖得像患了抽风,“不……醉了的人,不会承认自己喝醉。”
石兽边猜谜与躲藏的游戏在严管家扑出大门的时候告一段落。
当时我受了惊吓,胃里一翻,哇的吐上了老管家的脚背。这个不幸的意外之后,严管家宛如凶神恶煞一般,一路以他家大人能听到的音量小声叽叽咕咕,将我拖将进去,洗刷摆弄,拎干沥净,关进卧室。
折腾到床上,我看屋顶的横梁时,它还一直一直转动。
阖上眼,昏昏沉沉,似乎在雾里散步,反复几个来回,迷途知返时,却又湿又冷,找不到归路。
心里渐渐发慌。又隐约觉得有什么野兽之类大凶的东西,一直在浓雾后面,觊觎这副皮囊,窥视这身形骸。我拔脚跑了几步,却又像是被脚下的枝蔓绊住,沉重提不起力气,慢慢要淹没在雾气里。
这当口兀然就醒了。
像是突然浮出了水面一样,睁眼,一身湿淋淋的冷汗。手脚非常僵硬,胸口像是堵了沉重的块大石,大口喘息,方缓过一点儿劲来。
夜深,所以被魇住了。
卧室里仍旧是黑暗一片,静悄悄的,只有外头偶尔传来几声呿呿的虫鸣,窗户的方向,不曾有一丝黎明前的光亮。
我醒来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景象,如同月来在这间屋中度过的数个夏夜。可不知怎的,我明白,有人一直坐在对面。
很久了。
久到屋里静谧的空气中,已经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若隐若现的龙涎香味。
但是他没有点灯,也没有发出声响。
除了侧耳细听时,伴着这厢缓缓平复的呼吸、那头一点微不可察的气息流动,显示着他还是一个活物。
若不是已经渐渐适应黑暗的目力,艰难的从阴影高处分辨出一点模糊的、时隐时现的白影,我大概会以为,对方也已经睡着。
“……”
我张了口,可是又想不出什么话来问。
他静静的坐在这里,不是一时半刻,却什么也没有干。这件事的解释,除了作不愿夜深人静时惊动旁人想,唯一的可能就是,并不想和醉鬼攀谈。
大概还在生气。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明白。
但是我心里有愧,又有一点沮丧,想要继续阖眼装睡,想要糊弄过去,等到天明就会过去。可惜真这样做之前,心中忽的升起一丝恐惧,恐惧在这样沉寂的夜里被噩梦缠身,却不能相碰的距离。
那一丝恐惧,本来只是些微晃一晃脑袋就能甩掉的感想,却在黑暗里无声无息的时光流逝中,一点点放大,胀满了胸怀。
噢,太糟了……
终于在魂魄惊醒之前,手先撩开了薄被,一脚踏在荫凉的石砖地上。
紧接着重物落地的声音。
在寂静的房间里,有若轰隆巨响。
极其丢脸的,因为宿醉未醒的缘故头重脚轻,以扭曲的姿势向下栽倒,脸贴在床下踏脚板之上。
我为这个意外深感羞赧。耻辱的趴在地上,好等待身体的疼痛渐渐过去,安静再次落下,将此人此事掩埋。
周围很静。
如同我的心愿。
半晌,都没有动静。
久到我以为之前黑暗中的人影确实是我的错觉,才有一只手来扶。
最初的试探,带着点谨慎观察的犹疑,可随后伸到腋下的支撑,又很用力。
那层温度透过衣襟的感觉,渗进我仍旧不清不楚的脑子里,叫人鼻子发酸。“景元觉……你笨!”
我的声音又干又哑,听起来十分凶恶。
他似乎被骂蒙了头,一时没有应声。
好一会儿,挑了个相对坐着的姿势,掰开我捂着肘的手,帮着要揉。温热的肌肤一接触,结果我“啪”一声打掉他的手——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景元觉也愣在那里。
过了好一会儿,又伸手,摊开掌心覆在跌肿了的地方,慢慢的给揉。
“别发酒疯。”
他警告我。
本来因为揉痛想要挣扎的动作,被扼杀在威胁里。我赖在景元觉肩膀上,不配合的动一动,立刻得到了一下大力的。
我顿时怒火攻心。
“呀!”
他惨叫起来,捂着肩头创口,努力抑制着声音小下去,在我耳边吼叫,“你!又咬,白眼狼吗!”
我得逞的笑起来,嘿嘿嘿,嚯嚯嚯。意犹未尽的舔舔嘴唇,看见对方的僵硬,又掰开他的手,好心的帮他吸干。
……只有一点点血味。
“你怎么能这样。”
景元觉终于把我抱到了床上,一面整理被褥,一面反复徒劳的扒着我黏在他身上的手脚。
他扒一次,我就再黏上去一次。他只有一双手,可是我却有四肢,因而对这个必胜的游戏,乐此不疲。
一开始他动作还算轻柔,后来就有点急。
“有完没完!”
结果他吼了一声,把我推到被子堆里。
我觉得十分委屈,好似玩了一半却遭到同伴的背叛,干脆埋头倒在被子里,一动不动兀自伤心。
景元觉没一会又来拉我。
“苏鹊?……没事吧。”
我闭着眼睛装死,他使劲摇,不住的摇。问的话一句比一句焦急,“苏鹊,你吓我?苏鹊?把眼睛睁开,睁开看我!”
给摇得头昏脑胀,胃里难过,又想吐了。没想到装死是这么难过的一件事,于是我把眼睛睁开一条缝,怒瞪他。
“喂!”
景元觉骇得手一抖,却明显放松的样子。阴影里,只看得见他的眉郭舒展下来,脸庞的轮廓,似乎也从刚硬变成了柔和。
“你怎么能这样?” 他的手在我的额头上摸了又摸,叹了口气,突然埋在我的颈项低喃,“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么折腾我……”
反反复复,就那么两句。似乎在埋怨,在指责,又似乎在求全。也许,还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有这样的反转,可是心里的感觉,就像掺了一层沙又掺了一层蜜,痛和甜夹杂在一起,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晕晕乎乎中,伸出手拍他的背。
一下,一下,觉得自己亏得不行。可是一直也没有停止,直到后来精神不支,不知道什么时候


![(HP同人)[HP]世界第一暗恋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5/501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