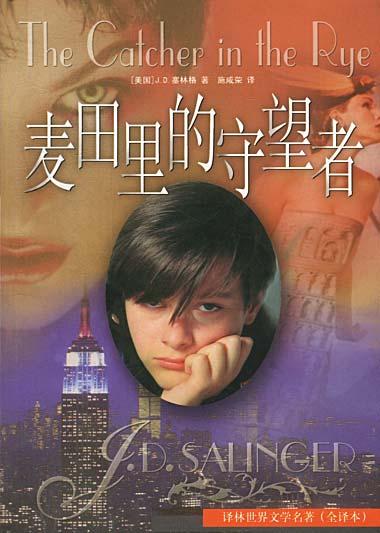麦田里的守望者-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呃,那你说出来。”
“我喜欢艾里,”我说。“我也喜欢我现在所做的事。跟你一起坐在这儿,聊聊天,想
着一些玩艺儿——”“艾里已经死啦——你老这么说的!要是一个人死了,进了天堂,那就
很难说——”“我知道他已经死啦!你以为我连这个也不知道?可我依旧可以喜欢他,对不
对?不可能因为一个人死了,你就从此不再喜欢他,老天爷——尤其是那人比你认识的那些
活人要好一千倍。”
老菲芘什么话也没说。她要是想不起有什么好说的,就他妈的一句话也不说。
“不管怎样,我喜欢现在这样,”我说。“我是说就象现在这样。跟你坐在一块儿,聊
聊天,逗着——”“这不是什么真正的东西1”“这是真正的东西!当然是的!他妈的为什
么不是?人们就是不把真正的东西当东西看待。我他妈的别这都腻烦透啦。”
“别咒骂啦。好吧,再说些别的。说说你将来喜欢当个什么。喜欢当一个科学家呢,还
是一个律师什么的。”
“我当不了科学家。我不懂科学。”
“呃,当个律师———跟爸爸一样。”
“律师倒是不错,我揣摩——可是不合我的胃口,”我说。“我是说他们要是老出去搭
救受冤枉的人的性命,那倒是不错,可你一当了律师,就不干那样的事了。你只是挣许许多
多钱,打高尔夫球,打桥牌,买汽车,喝马提尼酒,摆臭架子。再说,即便你真的出去救人
性命了,你怎么知道这样做到底是因为你真的要救人性命呢,还是因为你真正的动机是想当
一个红律师,只等审判一结束,那些记者什么的就会全向你涌来,人人在法庭上拍你的背,
向你道贸,就象那些下流电影里演出的那样?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个伪君子?问题是,你不
知道。”
我说的那些话老菲芘到底听懂了没有,我不敢十分肯定。我是说她毕竟还是个小孩子。
不过她至少在好好听着。只要对方至少在好好听着,那就不错了。
“爸爸会要你的命。他会要你的命,”她说。
可我没在听她说话。我在想一些别的事一——一些异想天开的事。“你知道我将来喜欢
当什么吗?”
我说。“你知道我将来喜欢当什么吗?我是说将来要是能他妈的让我自由选择的话?”
“什么?别咒骂啦。”
“你可知道那首歌吗,‘你要是在麦田里捉到了我’?我将来喜欢——”“是‘你要是
在麦因里遇到了我’!”老菲芘说。“是一首诗。罗伯特。彭斯写的。”
“我知道那是罗伯特。彭斯写的一首涛。”
她说的对。那的确是“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可我当时并不知道。
“我还以为是‘你要是在麦田里捉到了我’呢,”我说。“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
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
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
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
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不象话。”
老菲芘有好一会儿没吭声。后来她开口了,可她只说了句:“爸爸会要你的命。”
“他要我的命就让他要好了,我才他妈的不在乎呢,”我说着,就从床上起来,因为我
想打个电话给我的老师安多里尼先生,他是我在爱尔克敦。希尔斯时候的英文教师,现在已
经离开了爱尔克敦.希尔斯,住在纽约,在纽约大学教英文。“我要去打个电话,”我对菲
芘说,“马上就回来。你可别睡着。”我不愿意她在我去客厅的时候睡着。
我知道她不会,可我还是叮嘱了一番,好更放心些。
我正朝着门边走去,忽听得老菲芘喊了声“霍尔顿!”我马上转过身去。
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看去漂亮极了。“我正在跟那个叫菲丽丝。玛格里斯的姑娘学打
嗝儿,”她说。“听着。”
我仔细听着,好象听见了什么,可是听不出什么名堂来。“好,”我说。接着我出去到
客厅里,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师安多里尼先生。
第23节
我三言两语就把电话打完,因为我很怕电话刚打到一半,我父母就撞了进来。不过他们
并没有撞进来。安多里尼先生非常和气。他说我要是高兴,可以马上就去。我揣摩我大概把
他和他妻子都吵醒了,因为他们过了好半天才来接电话。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出了什么事没
有,我回答说没有。我说我倒是给潘西开除了。我觉得还是告诉他好。我说后,他只说了声
“我的天”。他这人很有幽默感。他跟我说我要是愿意,可以马上就去。
安多里尼先生可以说是我这辈子有过的最好老师。他很年轻,比我哥哥DB大不了多
少,你可以跟他一起开玩笑,却不致于失去对他的尊敬。我前面说过的那个叫詹姆士。凯瑟
尔的孩子从窗口跳出来以后,最后就是他把孩子抱起来的。老安多里尼先生摸了摸他的脉
搏,随后脱掉自己的大衣盖在詹姆士。凯瑟尔身上,把他一直抱到校医室。他甚至都不在乎
自己的大衣上染满了血。
我回到DB房里的时候,发现老菲芘已经把收音机开了,正播送舞曲。她把声音开得很
低,免得被女佣人听见。你真该看见她当时的样子。她直挺挺地坐在床中央,在被褥外面,
象印度的修行僧那样盘着双腿。她正在欣赏音乐。我见了真把她爱煞。
“喂,”我说。“你想跳舞吗?”她还是个很小很小的毛孩子的时候,我就教会了她跳
舞什么的。
她是个了不起的舞蹈家。我是说我只教了她一些基本动作。她主要靠自学。舞要真正跳
得好,光靠人教可不成。
“你穿着鞋呢,”她说。
“我可以脱掉。来吧。”
她简直是从床上跳下来的,然后她等着我把鞋子脱掉,我们就一起跳了会儿舞。她的舞
跳得真是好极了。我不喜欢人们跟小孩子一块儿跳舞,因为十有九次那样子总是十分难看。
我是说,在外面的餐厅里你总看见那么个老家伙带着自己的小孩子在舞池里跳舞。他们总是
牛头不对马嘴,老攥住孩子背上的衣服一个劲儿往上拉,那孩子呢,简直他妈的不会跳舞,
所以那样子真是难看极了,可我从来不带菲芘或别的孩子在公共场所跳舞。我们只是在家里
跳着玩儿。不过话说回来,她毕竟与别的孩子不同,因为她会跳舞。不管你怎么跳她都跟得
上。
我是说位只要把她搂得紧紧的,那样一来不管你的腿比她长多少,也就不碍事了。她会
紧跟着你。你可以转身,可以跳些粗俗的花步,甚至还可以跳会儿摇摆舞,她始终紧跟着
你。你甚至还可以跳探戈呢,老天爷。
我们跳了约莫四个曲子。在每个曲子的间歇时间,她的样子好笑得要命。她摆好了跳舞
的姿势。
她甚至连话都不说。你得跟她一起摆好姿势等乐队再一次开始演奏。我见了差点儿笑
死。可你还不准笑哩。
嗯,我们跳了约莫四个曲子,随后我把收音机关了。老菲芘一下跳回床上,钻进了被
窝。“我进步了些,是不是?”她问我。
“怎么进步的?”我说。我又挨着她在床上坐下了。我有点儿喘不过气来。我抽烟抽得
他妈的太凶了,呼吸短得要命。她却连气都没喘一下。
“你摸摸我的额角看,”她突然说。
“干吗?”
“摸摸看。光是摸一摸。”
我摸了一下,却什么也没感觉到。
“是不是烧得厉害?”她说。
“不,你觉得烧吗?”
“是的——是我有意搞出来的。再摸摸看。”
我又摸了一下,仍没感觉到什么,可我说:“这回好了,我觉得有点儿烧了。”我可不
愿意她产生他妈的自卑感。
她点点头。“我可以搞得烧到比体温表还高。”
“体温表。谁说的?”
“是爱丽丝。霍尔姆保教我的。你只要夹紧两腿,屏住呼吸,想一些非常非常热的东
西。一个电炉什么的。随后你整个脑门就会热得把人的手烧掉。”
我差点儿笑死。我立刻把我的手从她脑门上缩回,象是遇到什么可怕的危险似的。“谢
谢你警告了我,”我说。
“哦,我不会把你的手烧掉的。我不等它热得太厉害,就会止住——嘘!”说着,她闪
电似的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这么一来,可吓得我命都没了。“怎么啦?”
我说。
“前门!”她用清晰的耳语说。“他们回来啦!”
我一下子跳起来,奔过去把台灯关了。随后我把香烟在鞋底上擦灭,放到衣袋里藏好。
随后我一个劲儿扇动空气,想让烟散开——我真不应该抽烟,我的天。随后我抓起自己的鞋
子,躲进了壁橱,把门关上。嘿,我的心都快从我嘴里跳出来了。
我听见我母亲走进房来。
“菲芘!”她说。“哟,别来这一套啦。我早看见灯光了,好小姐。”
“哈罗!”我听见菲芘说。“我睡不着。你们玩得痛快吗?”
“痛快极了,”我母亲说,可你听得出她这话是言不由衷。她每次出去,总不能尽兴。
“我问你,你怎么还不睡觉?房间里暖和不暖和?”
“暖和倒暖和,我就是睡不着。”
“菲芘,你是不是在房里抽烟了?老实告诉我,劳您驾,好小姐。”
“什么?”老菲芘说。
“要我再说一遍?”
“我只点了一秒钟。我只抽了一口烟。随后把烟从窗口扔出去了。”
“为什么,请问?”
“我睡不着。”
“我不喜欢你这样,菲芘。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母亲说。“你不再要条毯子吗?”
“不要了,谢谢。祝您晚上好!”老菲芘说。
她是想尽快把她打发走,你听得出来。
“那电影好看吗?”我母亲说。
“好看极啦。除了爱丽丝的妈妈。她不住地弯过腰来,问她感冒好点儿没有,在整个放
映期间简直没有停过。后来我们乘出租汽车回家了。”
“让我来摸摸你的额角看。”
“我没有感染到什么。她根本没病。毛病就在她妈妈身上。”
“呃,快睡吧。晚饭怎么样?”
“糟糕透啦。”
“什么糟糕不糟糕的,你没听见你爸爸怎么教你用文雅的字眼儿吗?有什么地方糟糕?
你吃的是极好的羊排。我都把莱克辛登路走遍啦,就是为了——”“羊排倒挺不错,可查丽
娜不管往桌上放什么东西,总是冲着我呼气。她也冲着所有的食物呼气。她冲着一切的一切
呼气。”
“呃,快睡吧。吻妈妈一下。你祷告了没有?”
“我是在浴室里祷告的。晚上好!”
“晚上好。现在快给我睡昭。我的头疼得都快裂开来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