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就感觉到他们近在眼前。她远远地就感觉到她丈夫走近了,不由得注视着他在人群中走动的姿影。她看见他向亭子走来,看见他时而屈尊地回答着谄媚的鞠躬,时而和他的同辈们交换着亲切的漫不经心的问候,时而殷勤地等待着权贵的青睐,并脱下他那压到耳边的大圆帽。她知道他的这一套。而且在她看来是很讨厌的。“只贪图功名,只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她想;“至于高尚理想,文化爱好,宗教热忱,这些不过是飞黄腾达的敲门砖罢了。”
从他朝妇女坐的亭子眺望的眼光(他一直望着她的方向,但是在海洋一样的绢纱、丝带、羽毛、阳伞和鲜花中认不出他的妻子来),她知道他在寻找她,但是她故意不去注意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贝特西公爵夫人叫他,“我相信您一定没有看见您的夫人;她在这里呢。”
他露出冷冷的微笑。
“这里真是五光十色,不免叫人目迷五色了,”他说着,向亭子走去。他对他的妻子微微一笑,就像丈夫和妻子刚分离一会又见面的时候应有的微笑那样,然后上前招呼公爵夫人和旁的熟人们,给每人以应得之份——那就是说,和妇人们说笑,同男子们亲切寒暄。下面,靠近亭子,站着一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尊敬的、以其才智和教养而闻名的侍从武官。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攀谈起来。
在两场赛马之间有一段休息时间,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妨碍谈话。侍从武官反对赛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反驳他,替赛马辩护。安娜听着他那尖细而抑扬顿挫的声调,没有遗漏掉一个字,而每个字在她听来都是虚伪的,很刺耳。
当四俄里障碍比赛开始的时候,她向前探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弗龙斯基,看他正走到马旁,跨上马去,同时她听着她丈夫的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声音。她为弗龙斯基提心吊胆,已经很痛苦,但是更使她痛苦的却是她丈夫的那带着熟悉语气的尖细声音,那声音在她听来好像是永不休止似的。
“我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堕落的女人,”她想,“但是我不喜欢说谎,我忍受不了虚伪,而他(她的丈夫)的食粮——就是虚伪。他明明知道这一切,看到这一切,假使他能够这么平静地谈话,他还会感觉到什么呢?假使他杀死我,假使他杀死弗龙斯基,我倒还会尊敬他哩。不,他需要的只是虚伪和体面罢了,”安娜暗自说,并没有考虑她到底要求她丈夫怎样,她到底要他做怎样一个人。她也不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今天使她那么生气,话特别多,只是他内心烦恼和不安的表现。就像一个受了伤的小孩跳蹦着,活动全身筋肉来减轻痛苦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同样需要精神上的活动来不想他妻子的事情,一看到她,看到弗龙斯基和经常听到人提起他的名字就不能不想起这些事情。正如跳蹦对一个小孩是自然的一样,聪明畅快地谈话在他也是自然的。他说:
“士官骑兵赛马的危险是赛马必不可少的因素。假如说英国能够炫耀军事历史上骑兵最光辉的业绩的话,那就完全是因为它在历史上发展了人和马的这种能力。运动在我看来,是有很大价值的,而我们往往只看到表面上最肤浅的东西。”
“这不是表面的,”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说。“他们说有一个士官折断了两根肋骨哩。”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浮上素常的微笑,露出了牙齿,但是再也没有表示什么。
“我们承认,公爵夫人,那不是表面的,”他说,“而是内在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于是他又转向那位一直在和他认真谈话的将军说:“不要忘了那些参加赛马的人都是以此为业的军人,而且我们得承认每门职业都有它不愉快的一面。这原属军人的职责。像斗拳,西班牙斗牛之类的畸形运动是野蛮的表征。但是专门的运动却是文明的表征。”
“不,我下次再也不来了;这太令人激动了哩!”贝特西公爵夫人说。“不是吗,安娜?”
“这是激动人的,但是人又舍不得走,”另一个妇人说。
“假使我是一个罗马妇人的话,我是不会放过一次格斗表演的。”
安娜一句话没有说,尽拿着她的望远镜,老盯住一个地方。
这时,一位高大的将军穿过亭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中止谈话,急忙地、但是庄严地立起身来,向将军谦卑地鞠躬。
“您不参加赛马吗?”将军跟他开玩笑说。
“我参加的竞赛可更难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恭敬地回答。
虽然这回答毫无意思,将军却显出好像从富于机智的人口里听到机智的回答那样一副神情,细细地品尝着lapointedelasauce①——
①法语:话中的风趣。
“有两方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演员和观众两方面;我承认,爱看这种东西正是观众文化程度很低下的铁证,但是……”
“公爵夫人,打赌吧!”从下面传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朝贝特西说话的声音。“您赌谁赢呢?”
“安娜和我都赌库佐夫列夫,”贝特西回答。
“我赌弗龙斯基。一副手套吧?”
“好的!”
“多么好看呀,可不是吗?”
当周围有人谈话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了一会,但是随即又开口了。
“我同意,但是需要勇气的运动不是……”他继续着。
但是正在这时骑手们出发了,于是一切的谈话都停止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静默下来,每个人都站起来,把视线转向小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赛马并不感兴趣,所以他没有看骑手们,只是用他那疲倦的眼睛心不在焉地打量着观众。他的眼光停在安娜身上了。
她的脸色苍白而严峻。显然除了一个人以外,她什么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她的手痉挛地紧握着扇子,她屏住呼吸。他望了望她,连忙回过头去,打量着别人的面孔。
“但是这里这位妇人和旁的妇人都很兴奋呢;这是非常自然的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他极力想要不看她,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目光被吸引到她身上去了。他又观察了她的脸,竭力想不看出那明显地流露在那上面的神情,可是终于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怀着恐怖,他在上面看出了他不愿意知道的神色。
库佐夫列夫在小河旁第一个堕下马来使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安娜的苍白的、得意的脸上却清楚地看出了,她所注视的人并不是跌下马的那一个。当马霍京和弗龙斯基越过了大栅栏之后,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士官跌下马来,受了重伤,而一阵恐怖的叹息声在全体观众中间掠过去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安娜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她好容易才明白她周围的人们在谈什么。但是他更频频地、执拗地注视着她。安娜虽然全神贯注在飞驰的弗龙斯基身上,却感觉到她丈夫的冷冷的眼光在旁边盯着她。
她回过头来,询问般地望了他一眼,微微皱着眉,又回过头去。
“噢,我才不管哩!”她像在对他这样说,就再也没有望过他一眼了。
这场赛马是不幸的,在参加比赛的十七个士官中有半数以上堕马,受了伤。到比赛将要终结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激动,因为沙皇不高兴,大家就更激动了。
九
大家都大声地表示不满,大家都在重复不知谁说出来的一句话:“只差和狮子角斗哩,”而且大家都感到恐怖,因此当弗龙斯基翻下马来,安娜大声惊叫了一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但是后来安娜的脸上起了一种实在有失体面的变化。她完全失去主宰了。她像一只笼中的鸟儿一样乱动起来,一会起身走开,一会又转向贝特西。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她说。
但是贝特西没有听见。她弯着身子,正跟走到她面前的一位将军说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安娜面前,殷勤地把胳臂伸给她。
“我们走吧,假使你高兴的话,”他用法语说;但是安娜正在听将军说话,没有注意到她丈夫。
“听说他也摔断了腿,”将军说,“真是太糟糕了。”
安娜没有回答她丈夫,她举起望远镜,朝弗龙斯基堕马的地方眺望;但是离那地方那么远,而且那么多人拥挤在那里,她什么都看不见。她放下望远镜,正待起身走开,但是正在这时一个士官骑马跑来,向沙皇报告了什么消息。安娜向前探着身子倾听。
“斯季瓦!斯季瓦!”她叫她的哥哥。
但是她的哥哥没有听见。她又起身预备走。
“我再一次把胳臂伸给你,假使你要走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触了触她的手。
她厌恶地避开他,没有望着他的脸,回答说:
“不,不,不要管我,我要留在这里。”
她这时看到从弗龙斯基出事的地点一个士官正穿过赛马场朝着亭子跑来。贝特西向他挥着手帕。
士官带来了骑者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背的消息。
一听到这消息,安娜就连忙坐下,用扇子掩住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她在哭泣,她不仅控制不住眼泪,连使她的胸膛起伏的呜咽也抑制不住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身子遮住她,给她时间来恢复镇静。
“我第三次把胳臂伸给你,”他过了一会之后向她说。安娜望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贝特西公爵夫人来解围了。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邀安娜来的,我答应了送她回去,”贝特西插嘴说。
“对不起,公爵夫人,”他说,客气地微笑着,但是坚定地望着她的眼睛。“我看安娜身体不大舒服,我要她跟我一道回去。”
安娜吃惊地环顾了一下四周,顺从地站起身来,挽住她丈夫的胳臂。
“我派人到他那里去探问明白,就来通知你,”贝特西低声对她说。
当他们离开亭子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和他遇见的人们应酬,而安娜也要照常寒暄应酬;但是她完全身不由已了,像在梦中一样挽住她丈夫的胳臂走着。
“他跌死了没有呢?是真的吗?他会不会来呢?我今天要不要去着他?”她想着。
她默默地坐上她丈夫的马车,他们默默地从马车群里驶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看见了这一切,却还是不让自己考虑他妻子的实际处境。他只看见了外表的征候。他看见了她的举动有失检点,认为提醒她是自己的职责。不过单提这件事,不说别的,在他是非常困难的。他张开嘴,想要对她说她举动不检,但是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完全另外的话。
“说起来,我们大家多么爱好这些残酷的景象啊!”他说。
“我看……”
“什么?我不明白,”安娜轻蔑地说。
他被激怒了,立刻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我不能不对你说,”他开口了。
“现在我们一切都要说穿了!”她想,感到恐惧。
“我不能不对你说今天你的举动是有失检点的,”他用法语对她说。
“我的举动什么地方




![(安娜·卡列尼娜同人)名流之家[安娜]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50/15064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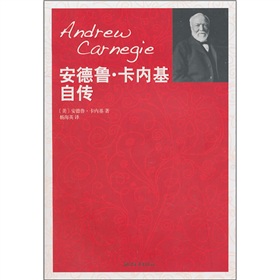
![(安娜·卡列尼娜同人)归来[安娜·卡列尼娜]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61/1615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