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至芳菲春将尽+番外 作者:陈则菱(晋江2014-12-29完结)-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样的父母可真有点。。。。。。
沈艳兰瞪着我,一副吃人的样子:“关你什么事?我的爹娘也是你能骂的吗?”
想想也是,以前一位同事说过,骂娘骂娘 ,就是我可以骂你的娘,但不许你骂我的娘。于是我嘿嘿两声向她道歉。
姚娘子撇撇嘴:“也没什么不明白的,为争吃一口饭,父子变成仇人的还有呢,要怪就怪这个天灾好了,这也是命。”
吵这些孰是孰非毫无什么意义,还是未来更重要。我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疑问:“姚大娘,我可是出过家的,那家人不忌讳吗?”令狐冲大哥说过,遇见尼姑,逢赌必输,那家人真不在乎?
姚大娘啧啧两声:“看来你还不知道呢?要不是艳兰这孩子拼命说你好,我才不想要你呢,她们三个,要模样有模样,要手艺有手艺。你小脸黄黄的,既不会梳妆打扮,又不会女红,能摊上什么好差事?要不是秦府说了可怜这落英城里的百姓,我才不敢揽这个活。”
:“原来是这样,看来我给大姚娘添麻烦了。”我忙狗腿地向她道谢,也感恩戴德状地向沈艳兰道谢,难道我错看她了,她,其实是个热心肠的?
沈艳兰十分不悦:“就知道你把我当坏人,我不就是说话冲一点吗,哼!”
我呵呵傻笑起来,小丫头,看来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们出发往洛京方向去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底,听姚大娘说,要在过年前将我们送到秦家。我想可能是过年活多,急需人手。
洛京在在落英城的西北方,马车大概要走半个月。
在路上,姚大娘不断地买了一些人上来,又卖了出去,陆陆续续的做成了不少笔贩卖人口的生意,估计利润也挺多,后来几天甚至看到她唱出小曲儿来,居然也委婉动听,虽然歌词十分口水。
趁她心情好,也因为洛京越来越近,我开口问了许多关于秦府的情况,她都以自动设置好的回答“不知道”,或者“到了便知”来回答。
嘿,没想到嘴还挺紧。
我们这四个人中,只有我死皮赖脸,签了个活契,不过是长达八年,姚大娘很不高兴,不过看在我给了她一半卖身钱的份上,也就不和我计较。
在路上,闾烟飞很认真地纠正我的发音错误,比如指出我把“晚饭”说成了“满帆”,一副咬文嚼字的认真小学究模样,完全不同于沈艳兰嘲笑我把“喝水”说成“瞌睡”时的不屑。
这两个小妞!还不知道老姐我是故意逗你们开心的么?把观众当猴耍的我乐滋滋的。
伊春德最喜欢和我在一处,这令我的自信心大大膨胀,看来我长得虽然“没模样”,但肯定长的像邻家大姐姐一样亲切善良…后来才知道,其实都是那件棉袄的功劳。
马车里很冷,伊春德总是靠在我身上,我也默默地搂过她的肩膀,沈艳兰看到我们两人大白天的搂搂抱抱,很是看不下去“至于吗,又没冷死人。”一脸深恶痛绝,好像我们是万恶不赦的百合。
我懒得跟这个愤青计较,谁叫人家被父母赤果果地抛弃了呢?其实我可以对她施以心理援助的,不过,十岁敢为人缝伤口再神奇也只是个技术活,如果十岁就能做心理医生,就很值得被人怀疑了,我是不会以身犯险的。
闾烟飞是个不挑剔的人,一路上没见她有任何抱怨,任何悲伤,除了纠正我的那个“满帆“之外,她的泰然自若,使我想起《越狱》里的米帅。
我好奇地问她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她说是教书先生,难怪,她认真地纠正我的发音,而不是象沈艳兰一样嘲笑一句就了事。
我还知道了沈艳兰的父母是做小生意的,伊春德的娘曾给大户人家当过丫鬟,而且是小姐身边的大丫鬟。
相处的时间越长,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多,后来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叽里呱啦,沈艳兰愤青般的“哼哼”挺多,可我凑趣般的“哈哈”也不少,一路上车厢里其乐融融。
作者有话要说: 做手术的和被做手术的小萝莉都很诡异。
不过我国古代医学的发达远非我们想像,据说在扁鹊那个时代,就能做复杂的换心脏和开头颅骨手术了,这些都是有实物证明的,在哪个博物馆?我忘了。
矮矮的桑树,几个稚龄的少女挽了篮子寻找些什么,在古代,桑林是约会的好地,代表浪漫。
图图来自度娘。
☆、第四章 远近高低各不同
我们的终点并不是某个森严的大宅院,而是一座依山傍水的田园。
田园门前并无牌楼,大门一类表示界限的东西,眼前只有一块巨大的太湖石上刻了“沁水田园”四个苍劲的篆体字。
今天是腊月二十五,天气寒冷,庄园的树木银装素裹,是雾凇,挂在树上的冰霜如同各种形状的秋菊,晶莹剔透,美不胜收。
换了一辆马车,我们进入沁园,大约一顿饭的功夫,来到管事院。姚大娘领着我们见了管事的,那管事的详细地询问了我们四个的情况,最后安排我们的去处:沈艳兰到双清苑,闾烟飞到紫蓼庭,伊春德到露香院,我则到伏波堂。
伏波堂?我暗叹一口气:听起来就像个佛门净地,转来转去,又回到原点,难道我天生就是尼姑命?
伊春德很紧张,沈艳兰镇定自若,不过,在告别时,我恰好捕捉到她脸上一抹古怪的微笑,不是欣喜,有点像自嘲,又有点像是不屑一顾,总之,极其复杂。闾烟飞彬彬有礼地朝管事的道谢,微笑着和我们告别,我假装镇定地说了几句励志的话。
管事的是个胖胖的老年妈妈,她见我们四个一本正经地告别,感到好笑般微微笑:“用不着这般伤感,都同在一个园子里,以后还是能见面的。我们老夫人最体恤下人了。”
姚大娘在一旁解释道:“这四个丫头虽然不是亲生姐妹,依我看来比姐妹还要好呢,有点义结金兰的意思。”
管事的老妈妈可不赞同,她敛住了笑:“做下人的,一定要以主人的吩咐行事,万万不可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否则,想在园子里呆下去就难了。”
姚大娘吓了一跳,赶紧催促我们:“还不谢谢周妈妈的指点,要是坏了园里的规矩,受惩罚不说,连我的名声也坏了。”
我们四个依言感谢周妈妈不提。
伏波堂坐落在庄园的东南角,这里翠竹环绕,黄墙黑瓦,地上石板步生莲花,颇有古穆之意。我被安排在西边的厢房住了下来,居然一个人住一间房间,后来知道,这里当差的人很少,空房间多的是。
房间日常物品一应俱全,半新不旧,质量优良,让我转忧为喜的是,房间里居然有不少书籍,虽然以佛经居多,但也不缺儒家经典,更有笔墨纸砚,而且纸张都是表面虽然粗糙但韧性较好的黄麻纸,倒像是为我量身定做好的一般。
第一个夜晚就在我的惊喜与猜疑中慢慢度过,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有点冷,可床上的被褥都很厚实,我拿出梳子分别在两个脚底板用力梳了数下,直到双脚被弄得热烘烘的才罢手,很快就睡着了。梦中依稀听到冰霜从竹子上破裂坠地的声音,清脆动听。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六,我领到差事:清洁摆放供品的器皿,整理献给菩萨的柏枝佛手等物事。
和我一起干活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中年妇人,我管她叫方居士,她是一个在家居士,通过和她的聊天,我了解到秦家的一些情况:
秦府的男主人秦公祺,当朝镇东将军,两年前率兵击退进犯长安的西凉军,护送皇室从长安迁回陪都洛京,英勇善谋,忠心可嘉,被封镇东将军,掌管京中御林军;因将军夫人至今未归,目前沁园中所有事务由秦老夫人打理。
两年前,秦公祺为了召集义军,几乎散尽所有家财,遣退所有庄内下人,所以现在秦家庄园内当差的,几乎都是新采办来的,落英城地震,秦老夫人得知后,特别嘱咐管事的从落英城多买些无家可归的孤儿,这样既可迅速物色到合适的人选,也能多积功德。
大年三十,我居然收到新衣和新鞋袜,吃上米饭和肉,看来秦府的福利待遇还不错,只是不知薪水几何?雇员晋升制度如何?
大年初一,秦老夫人到伏波堂烧香祈福,我站在人群的最外围,伸长了脖子往里望,冷的瑟瑟发抖,暗暗祷告老太太赶紧结束。
大年初一到初五,我的工作依然是洗啊,抹啊,搬啊,整天忙得跟个陀螺一样,晚上倒头就睡。
大年初六,方居士终于放我一天假,不过叮咛我千万别到外面乱走,否则很容易迷路。
我一整天就窝在房间里,研墨练字,读书喝茶,吃完晚饭,出门在竹林里散步消化,已经好几年没沾荤腥的肠胃还真有点娇气呢。
由于我的头发刚长出来没有几分长,现在又是冬天,不管在屋里还是在外面,我都头带灰色布帽,如果不是因为身穿婢女衣裳,肯定没人当我是女孩子,样子难看,难怪被分到这个清水衙门。
日子如水般流去,伏波堂的梅花开了,香气沁人心扉,一棵红梅,一棵白梅,与翠绿的竹林相辉映,雅致之极。
梅花将落,庄园内开始为迎接秦公祺的女眷回园而忙碌。伏波堂的主管嘱咐所有堂内当差的人要谨听慎言,做好本分。
积雪融化,我以伏波堂为圆心,加大了活动范围半径,对于沁园,我已经渐渐地了解到它的一丝半毫:庄园北依莽山,南邻沁水,以田园风光与亭台楼阁相结合,园内溪泉遍布,绿树滴翠,一个天然的东湖位于园子中间。
这一天我来到了东湖边。
只见湖面开阔,波光粼粼,湖心一个小岛,绿树掩映,长堤边上巨树参天,树叶新绿,远处岸边,兰舟朱楫,随风轻摆。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桃红柳绿,瑞花遍开,芳香扑鼻。
这里分明是最理想的风花雪月之地,富贵温柔之乡,才子佳人约会的最佳地点,出家人哪能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年纪小小的我都忍不住生出杜丽娘的伤春之情了,只是不知这里有没有柳梦梅哦!
清明那天,沈艳兰突然来到伏波堂,看到她从简易的马车上下来,我惊讶不已。
她没有理会我的惊讶,而是似笑非笑地问我:“大师难道也会魔魇了?还不带我进屋?”
我连忙将她请进我的房间,请坐上茶,她也不客气,理所当然的看我忙。喝完一杯茶后,站起来走到桌子,她随手翻了翻桌上的书,又拿起我写的几张纸,一张张的看看,轻声念了出来:
咏双梅
白衣胜雪红裳艳,
相依相偎翠竹前。
清丽高洁皆惊世,
难分伯仲报春仙。
初见东湖
湖面映如镜,
岂止生十景。
一心观全貌,
候坐伏波亭。
田园春光畅想
嘉木瑞花遍满山,
草长莺飞满湖岸。
欲赏只待能翩翩,
得道成仙修行难。
这三首诗是我的信手涂鸦之作,用隶书写在毛边纸上,沈艳兰冷笑道:“果然是逍遥自在,可惜连张好纸都买不起。”
她居然很识货!我嬉皮笑脸的道:“是啊,我本来就是出家人,卖身的钱又送出去一半,哪还有钱留下来风花雪月,要不,你买了送我?”
:“哼!”她鼻子里挤出一声:“送得了一时送得了一世吗?再说用那么好的纸写给谁看?”
我随口胡诌:“
![[综漫]芳落芳菲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115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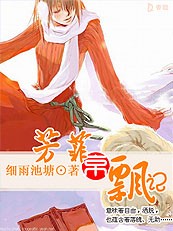
![[综漫]芳落芳菲-芳落(完)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6/1685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