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至芳菲春将尽+番外 作者:陈则菱(晋江2014-12-29完结)-第1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半杯喝下肚,身上渐渐温热,我停杯抬头,低声说道;“味道很好。表哥,谢谢你。”
他宽大的衣袖无声的动了动,眼中的涟漪幅度不断扩大,几乎可以将他的平静情绪淹没,他的嘴唇嗫嚅了一下:“表妹,我一直不放心,只想亲口问你一句,你,是真心愿意的吗?”
他问的是我嫁给秦桓之的事,我艰难地点点头,说了声:“是的。”垂下眼睑,不敢再看他的脸。
他忽然笑了,有种淡淡的讥讽:“听说,他待你不薄,能给你的,都给了,只是,芳菲。。。。。。”他忽然激动起来:“你嫁给他,仅仅是因为心里喜欢他?”
他问的话很奇怪,偏偏又问到点子上,我回沁园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嫁人,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心中疑云渐生,问道:“表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他见我避开话题,怅然若失,也没有回答我,反问了一句:“芳菲,你身上的毒都清了没有?”
我把他这句话里的含义理解成:你和他,同房了?所以脸渐渐地红了。
他微笑了起来,眼中却有种淡淡的苦涩,看得让人揪心般的难受。
外面有人在敲门,吴侯敛声问道:“何事?”
门外有人答道;“洛京秦二公子求见。”
我长叹一声,来得真快。
吴侯看了我一眼,不紧不慢地说道:“有请。”
门无声地打开,秦桓之翩然而至,拱手和吴侯客气着:“允节到了荆州怎么也不光临寒舍?桓之也好尽地主之谊。”
客气到不行,也虚伪到了极点。
吴允节微微笑道:“默存旅居荆州,多有不便,愚兄怎能冒昧叨扰?就由愚兄在此楼中略备薄酒,款待贤伉俪,如何?”
反唇相讥,说秦二同学才是客人。
两人表面上说得都很客气,实际上是针锋相对,都想表明自己才是荆州的主人,对方是荆州的客人,看来荆州古城,将来难免会有一场恶战。
秦桓之瞥了我一眼,慢声说道:“允节的好意桓之心领了,桓之今日琐事缠身,恐不能奉陪,来日方长,不如我们改日再聚?”
他还在强调自己是主人。
吴侯云笑淡风轻:“愚兄随时恭候大驾。”
两人在打口水仗。
一个气焰高涨,先发制人,一个成熟稳重,隐而不发。
我瞄了一眼身边的秦桓之,他的眼睛几乎不动,这是他心里不痛快的表现,想抓奸不成,还被人反客为主地噎了几下,心高气傲的秦家二公子,伤自尊了。
走前吴侯拱手相送,我回他一个稽首礼:“弟子告别先生。”吴侯淡淡笑,秦桓之冷眼旁观。
在回住所的路上,秦桓之若无其事走在一行人的最前面,和茂林他们有说有笑,当我不存在,我自知大难临头,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游离在他的视线之外,边走边想,他会怎样惩罚我呢?
一回到住所,茂林他们跟穿了隐身衣一样,倏的一下子,全都看不见了,偌大的庭院,就只剩我们两人,我朝四下看了看,嗯,光秃秃的,人都躲到哪里去了?怎么不把我也带走啊!
一张俊脸突然近在眼前,森冷的气息令人不寒而栗:“天天在外面跑,终于把老情人引来了,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我凝滞了半秒:“吴公子是我的丹青先生,不是老情人。”
他低低地哼了一声:“先生!先生跟弟子会面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分明是存心不良。”
我分辨了一句:“并没有偷偷摸摸。”
他失笑:“如果光明正大,他为什么不到家里来?”
这我哪知道!我摇了摇头,不做声。
他问道:“摇头是什么意思?”
我又赶紧点头:“不知道。”
他死死盯着我的脸,好像想从我脸上抠下几两金子一样,目光亮的吓人,我不敢再看,将脸微微侧到一边。
他伸手一把捏住我的脸,逼着我和他近距离对视,紊乱的呼吸时有时无地吹到我脸上,气息暖暖的,让人神智不清。
:“他为什么找你?”他冷冷地开口。
我小声说:“他,问我过的好不好。”
他的眼睛眨了一下:“你怎么说?”
我瑟缩了一下:“我说,还好。”
:“还好。”他重复了一下:“那就是不够好!你说!是我没给你正室的名分?还是我对你不好?”
我忽然觉得这种挑字眼的争辩很无聊,跟小孩子的胡搅蛮缠一样,纯粹是浪费精力,于是疲惫地说道:“桓之,我们先冷静一下,好吗?我想你也累了。”
:“我不累!”他像赌气一样,和我唱反调,一脸痛恨地在我脸上探究不止:“你累了?在他面前不是有说有笑的吗?怎么一见到我就累了?你敢嫌弃我,你这个朝秦暮楚的坏女人!”
他忽然痛骂起来,眼睛里充满了憎恨,又充满了怜悯,像个怨妇一样唧唧歪歪:“你知道吗,芳菲,我一直很好奇,你心里到底想什么?分明和我过了明路,却追着姓顾的到江东,姓顾的对你那么疼爱,你偏偏不要,回头跟我打得火热,和我好了一阵,突然不理我了,又跟着姓顾的跑了,我现在很想知道,如果当初没在吴郡截住你,你会回来找我的,对吗?嗯。”
说着说着,他声泪俱下,抓起我的肩膀不停地摇晃;“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愿意为我生儿育女,是为了他,对吗?你是为了帮他,才嫁给我的吗?你这个骗子,你这个反复无常的坏女人。”
他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凌厉的掌风将我扇得跌落在地,眼前一片金星直冒,耳边轰鸣不止,一股甜甜的味道涌上喉咙,我陷入黑暗之中。
八月十七,荆州传来噩耗,缠绵病榻多年的孤独云容,没了。消息一传来,露香院马上挂上了三丈素缟,搭起了灵堂,桩桩件件有条不紊,应该是早就准备好了的。看来兰歆夫人的信息很准确,秦家众人对此也有心理准备,只是不知道,伊春德是否像沈艳兰预言的一样,会被秦彰之扶为正室呢?
沁园里的人都在为独孤云容的丧事出力,我以为会被秦老夫人安排抄写经文的差事,正想主动积极开工,却不料,秦桓之被武平侯派往荆州,说是让他去迎接独孤氏的灵柩,而我,则被秦桓之赶上马背,被迫和他一起快马加鞭,风雨兼程地穿州过府。
荆州是远古传说中的九州之一,地处荆山和衡山之间,西控汉中巴蜀,东临东吴南越山越,北接中原。荆州共有五郡,长江以北三郡:南阳,襄阳和江陵,长江以南两郡:武陵和南郡,孤独氏世代居住的荆州城,在江陵郡内,古老的城池南临长江,北依汉水,曾是古代楚国的都城。
江陵郡土壤肥沃,水系发达,物产丰富,百姓生活富庶安定,独孤氏是皇室宗亲,却又与世无争,所以江陵郡风平浪静。二十多年前,中原一带发生动乱以后,大批文人士族流亡至此,躬耕隐居,继续享受宁静的生活,不少岩穴之士也隐身山林,待价而沽,西园文化宾客钟铉曾是其中的一位。
独孤氏府内气氛肃穆沉重,独孤云容的灵柩早已移至家庙,只等启动北上的行程,秦彰之戚色淡淡,不似十分悲痛的样子,久病床前无孝子,也许独孤云容抱病数年,早就把俩人之间那点志同道合的情分给磨光了,伊春德的得宠从侧面反映了这个事实。
出发前武平侯明明吩咐过的,我们是来迎接灵柩的,可到了荆州城,一切都变卦了,秦桓之留了下来,作为他身边唯一的合法伴侣,我理所当然的也回不了洛京。
我们的住处是秦彰之滞留荆州期间居住的房舍,秦桓之很不喜欢房子的装饰风格,入住的当天便命人撤换了墙上所有的挂饰,更换了大部分家具座椅,一切都按照他的喜好将房子重新布置,一直忙到第三天晚上,仆人才勉强将房子摆设成他想要的样子。
装修是件苦差事,不死也得脱层皮,我在他做出决定的当天便装傻充愣,假装对装饰房子的事情一窍不通,在他的深深鄙视痛恨中,成功躲过一劫。同时我也明白了两件事情,一是,秦彰之肯定不会回来了,二是,我们得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虽然我很牵挂洛京的“个人事业”,但是有句话说得好:生活总是在别处,风景总是在别处。既然秦桓之同学都能住下来,我又为什么不能呢。
秦桓之还真是大忙人,他每天都早早起床,用过早膳便带着茂林和崔灏冰等人出门,直到傍晚才回来,用过晚膳后,会有不同面孔的客人登门拜访,他和来客们秉烛夜谈,高谈阔论,不到三更时分,绝不回房间休息,我每每在睡梦中被他惊醒骚扰,心里总不是滋味。
可是日子还得过下去,我慢慢地也找到了生活的乐子,首先将荆州城逛了遍,再到大街小巷里听不同阶层表演的花鼓戏,然后找年迈的老头老太给我讲当地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又到书肆书摊上淘各类古旧书籍,晚上秦桓之接待客人的时候,我就在书房里整理汇编白天搜集来的资料。
功夫不负有人,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从搜集得来的资料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楚王姜瑜的宫殿就在周围一带,不过早已是废墟一片,藤蔓丛生,要想在那里寻找关于楚王的蛛丝马迹,只怕是难于登天。
我到书肆的次数多了,渐渐的也和书肆的老板们熟悉起来,还做成了一两单生意,以梁鹄的名义编写了一套民间传说的书籍,老板们见我的字写得不错,书籍的内容也新颖,所以都愿意替我接单子。一招鲜吃遍天,我继续在书籍发行的道路上漫步行走。
秦桓之见我整天忙的不亦乐乎,也感到好奇,待他翻过我整理的资料后,只是笑笑,既不赞同也不反对,只是莫名其妙的让我别本末倒置,误了正事。
我问他何为正事?他邪恶地说:“铺床叠被。”真是越来越不正经,我呸了他一口。
这天书肆的伙计又给我一张单子,纸张很特别,更特别的是纸上画了一朵风韵饱满的兰花,兰花的下面只有三个字:绛云楼。
去还是不去,我站在深秋的阳光中,望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点发怔,他怎么在知道我在这里,他找我有什么事?
上次不辞而别虽然事出有因,可我还欠他一个解释,电光火石间,我移步绛云楼。
走进绛云楼的大门时我暗自庆幸,有时候,身边没有贴身丫鬟也是件好事,至少像现在我不用编理由打发走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巍颤颤得走进了归来厅,厅内弥漫着一一股焦枯甜腻味道,像极了当年我泡制的乌糖姜茶的气味。
厅中一人,幅巾宽衣,华如春松,目中涟漪微微泛起,嘴角若有若无挂着一丝浅笑。他的样貌没有变,气质也没有变,只是给人的感觉变了,有种经历沧桑世事后的超脱出尘。
他越是心平气和,我越是愧疚良多,可千言万语,也只浓缩成最平成的一句话:“妾身,见过吴公子。”
他平稳的声音中渗着一丝克制的激动:“你来了,你,可好?”亘古不变的问候语。
不知为什么,这简简单单的六字,使我想起从前的美好时光,眼角突然涩涩的,鼻子开始发酸;“多谢吴公子,妾身,很好。”
我想问:你也好吗,可又觉得太矫情,说不出口。
他好像忘记了请我坐下来,也
![[综漫]芳落芳菲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115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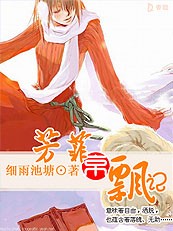
![[综漫]芳落芳菲-芳落(完)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6/1685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