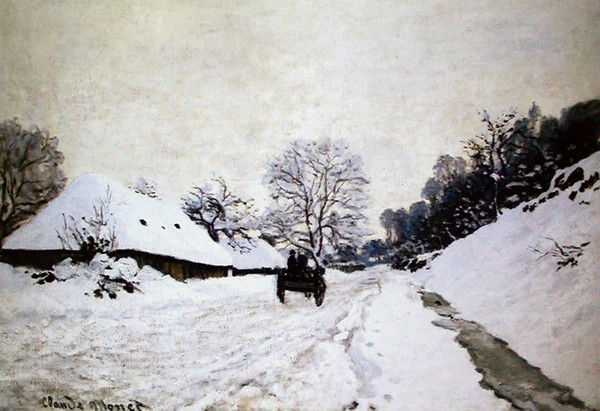在文明的束缚下-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行动或感情。生命运动永远不要降为一个僵化的行动。永远不要有不变的方向。
人的生活不可能有理想的目标。任何理想的目标都意味着机械主义、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不要掰开花蕾去看花儿是怎么样的。叶子自会展开,花蕾会绽放,然后才会开花。甚至在花儿枯萎、叶子凋落以后,我们还是不可能知道花是怎么样的。会有更多的叶子,更多的花蕾,更多的花儿,而一朵花又是有创造力未知的某种表现。你不可能,完全不可能预测那个还没有开的花儿是怎么样的。你不能破坏先开的花儿。即使我们知道了今天的花儿,昨天的花儿对我们还是未知的。只有在物质机械的世界里人才能预见,才有预知、推测和证实的法则。
至此,我们多少掌握了新民主的第一要义。我们多少知道了一个人对他自己来说是怎么样的问题。
其次,一个人对他的邻居来说又是怎么样的呢?由于每个人在他第一的真实里都是一个独立而不可置换的灵魂,不能由任何别的灵魂推测和定义,也就不可能有一种数学化的证明。我们不能说人都是平等的,我们不能说A=B,我们也不能说人都是不平等的,我们不能得出A=B+C。
由于任何事物对本身来说都是唯一的,也就没有什么比较可言。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既不平等也非不平等。当我站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我只是纯粹的我自己。我知道我表现得平等,或者更低下,或者更优越吗?不知道,当我和另外一个只是她自己的人站在一起,而我也完全是我自己时,那么,我只是知道表现了不同性的真实。既有我,也有另一个存在,这是真实的第一点。没有比较和估计,只有对现实不同性的认识。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我可能会感到高兴、生气或者伤心,但还是没有什么比较。只有当我们中的一些人从他自我的整体中分离出来时才可能有比较,比较进入了物质机械的世界,这样就有了平等和不平等。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民 主(14)
因此,我们知道了民主第一的伟大目标,每个人都应该是他本能的自我——每个是他自己的男人,每个是她自己的女人,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和不平等的问题,男人也决不应该去决定另外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存在。
但是,因为每个人都面临着从自在堕落到惰性化和机械化的诱惑,他必须随时准备好保持他的自在而反抗那些已经堕落或者失去自在了的人强加给他的机械主义和物质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为了灵魂本身的自由和本能的自在而反抗机械主义和物质主义堕落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关系着人类原始的完整。如果人类能保持完整和原始,其他任何事物就都能那样了。也就不需要什么法律和政府,同意将是自然的事情,甚至非常协调的社会活动也将完全是自然的。
由于目前处在难以形容的半开化状态,人类不可能把他自己本能的完整从他机械的贪求和理想中区分出来。因此,还必须有法律和政府,但我们看到,也永远不能忘记,法律和政府只是和物质世界联系着的,只反映了财产、财产的所有权和生活的方式,以及人类物质机械的天性。
无疑,过去曾经有过伟大的理想,譬如兄弟之爱、统一和平等。人性中伟大的部分都趋于符合兄弟之爱,以它们独特的方式,表现着它们的统一和平等。理想是多么简单,即使是像平等和统一那样数学化的理想也会有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因此,德国人所说的兄弟之爱以及统一和法国人说的意思从来就不一样。但毕竟还是兄弟之爱和统一。当灵魂产生同样的观念时,它们的方式总是不同的,直至它们到达存在本能的完整性终于破裂的那一点。然后,当纯粹的机械化或物质主义介入时,灵魂就被自动地固定在一个枢轴上,生命的多样性变成了完全机械的一致性。我们在美国可以看到这点。它不是同类的自然集合,而是由一大堆溃散的东西变成完全机械的一致性。
人类已经到达为了更进一步实现他们的理想而打破他们自在生命的完整,堕落到完全机械的物质主义的地步。他们变成了自动的行动体,完全受机械的法则支配。
现代民主完全是这样: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切都很相似。决定所有这些主义的原则都是一样的:财产的所有者,理想化了的组织原则。人作为一个财产的所有者都有他最高的实现目标,他们都这样说过的。有些人说,财产所有权应该由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大多数人掌握,其他人则认为应该由受过教育的、开化了的人掌握,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高见了,对此也没有必要多说了。
。。
民 主(15)
这是最后的理想,这是关于平等,兄弟之爱和统一理想的最后阶段,所有的理想终于堕落到了反映理想真实的彻底的物质主义。
现在谁是财产的所有者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都失去了对财产的把握,就是现实中最根本的财产也由于人失去他完整的本性而消亡了。虽说这很奇怪,但是不可否认,因为现在财产几乎是在消亡了。
那么,希望在哪里呢?因为有了希望,最后的理想才会消亡。终会有那么一天,那么一个地方,人终于会觉醒过来,认识到财产只不过是被人使用,而不是被人占有的。他会认识到占有是精神的一种病态,是本能之我身上绝望的负担。本来就不很重要的所有格代词“我的”,“我们的”就失去了它们所有神秘的意味。
财产的问题只有当人们不再关心财产的时候才能解决,然后它也就解决了其自身的问题。一个人要这样就能帮助他实现自我,一个只是为了得到一辆轿车、坐在里面驾驶的人,势必同轿车本身一样是机械的、没有希望的。
当人类从此摆脱了占有财产的欲望,或者阻止他人占有类似的欲望,那时,只有那时我们才乐意把财产转交给国家。我们现在国有化的方式只不过是换个名称而已,并非方式的改变。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是个无限公司,而不是有限公司。
未来的总理将不过是一个仆人,商业部长只是大管家,交通部长是众车夫的头儿;他们不过是重要的仆人而已。
当人们变成像样的自我,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管理这个物质世界,管理将必须是自然的而不是通过指令进行。在此之前,谈论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现在一切关于财产所有权,无论是个人的、集体的,还是国家的讨论和理想,都不过是对本能的自我的背叛。财产问题必须自然而然地由人类内部的新动力解决。那种新动力把人从身外之物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无牵无挂轻松地走路。任何想预先规定新世界的人都不过是在早已压垮背脊的负担上再加上最后的一根稻草而已。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背脊压垮,我们就必须把财产放到地上,丢下它走路,我们必须站在另一边。当许多人站在新的一边,他们就处在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人类的新世界就要开始了。这就是民主,新的秩序。
好 人(1)
18世纪的法国文学,尤其是18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中有一种令人压抑的东西。一旦我们了解了法国文学,我们就会发现:所有那些轻快的传记、冒险故事及伤感的抒发构成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消沉的文学形式。从根本上说,法国人是生活的批评者而不是创造者。当生活本身已变得相当枯燥时——就像18世纪的法国那样——对生活的这种批评声更是喋喋不休,给人一种颓丧的感觉。
相比之下,18世纪的英国文学则很有生气。斯特恩的感伤主义充满着自嘲,而同一时期的法国感伤主义却在大量地推销,犹如卖不出去的臭鱼。即便有人像伦敦东区音乐厅里的绅士那样,能趾高气昂站起身来,带着某种“优越感”,也很难对雷斯蒂夫?德拉?布雷东纳感兴趣,而只会对聪明的法国人会如此沉溺于感伤主义及淫欲之中吃惊不已。
洛赞公爵生活在我们称之为###的年代。他生于1747年,路易十五去世那年他正好27岁。由于出身高贵,家庭在宫廷中又有显赫地位,使他免受那些“下三流”作者的极度的伤感主义的影响,同时也使他失去了体验这些作者所具有的一些真正感受的机会。虽说他比让?雅克更具备男子气,但就其本身而言还是缺乏大丈夫的气慨。
18世纪的法国文学中人们对性感是如此困惑,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在自己的内心寻找那些固定的感觉部位,并以此来度量将要面临的困境。由于18世纪文学的根本问题是道德问题,也由于在那段时期产生的新侏儒是包括“有感情的人”在内的“好人”,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看看我们对18世纪的道德与善有何感受。
毫无疑问,今天的“好人”是经由像卢梭和狄德罗这样的人的大脑和感情中枢的化学成分提炼而成的,所以,这个“好人”的形象经过了100年后才慢慢地臻于完美。然而,在经过了一个半世纪以后,当我们在他衰落时再去认识他时,便会发现原来他是个机器人。
毫无疑问,人的意识里这个新的小“好人”的形象遭到了扭曲,而这便是导致法国革命的根本原因,这个新的小侏儒很快就会从意识的子宫里走出来,走上生活的舞台。一旦他走上舞台,他便会迅速成长,而且很快也会变得像伍德罗?威尔森那样年老昏聩。尽管如此,正是这个新的小怪物在从时间的子宫里挣脱出来时的骚动,导致了旧秩序的崩溃。
这个新的小怪物,这个新“好人”是绝对理智,不带任何宗教色彩的。宗教涉及到激情。“好人”玩弄机器人的戏法,使自己从激情中解脱出来。他以理智的社会道德来代替对生活的激情。你在物质交往时必须老老实实,必须善待贫穷,必须对你周围的人以及大自然抱有“感情”,大写的自然!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崇拜的,崇拜之类的事纯粹是荒唐之极。但是,你可以从任何事物中获得“情感”。
好 人(2)
为了能从事物中获得良好的“感情”,你当然必须相当“自由”,不受到任何干扰。而要想做到“自由”,你就得设法使别人对你不抱敌意,你必须“善”,当人人都变得“善”及“自由”时,我们便会对一切产生良好的感情。
这就是像卢梭这样的感情炼丹士经化学提炼而创造的“好人”观念的要点。正像任何其他小侏儒一样,这个小“好人”很快就开始畸形发展,随后发展成一个怪物,最后变为一个龇牙傻笑的白痴。现在,这个大怪物正向我们龇牙咧嘴地傻笑呢。
我们都已经是相当地“善”了,我们也都非常地“自由”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想得到什么呢?如此说来,我们该对任何事物都抱有惊人的良好感觉。
最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是好人我们便会装出对一切抱有一种良好的感觉,这也是卢梭之流创造的巨大的龇牙傻笑的感伤主义的最后狞笑。其实,要保持这种狰狞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事实上,我们远远不是对全体事物抱有一种良好的感觉。我们实际上对一切事物都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能获得良好感觉的时候已越来越少了。而在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