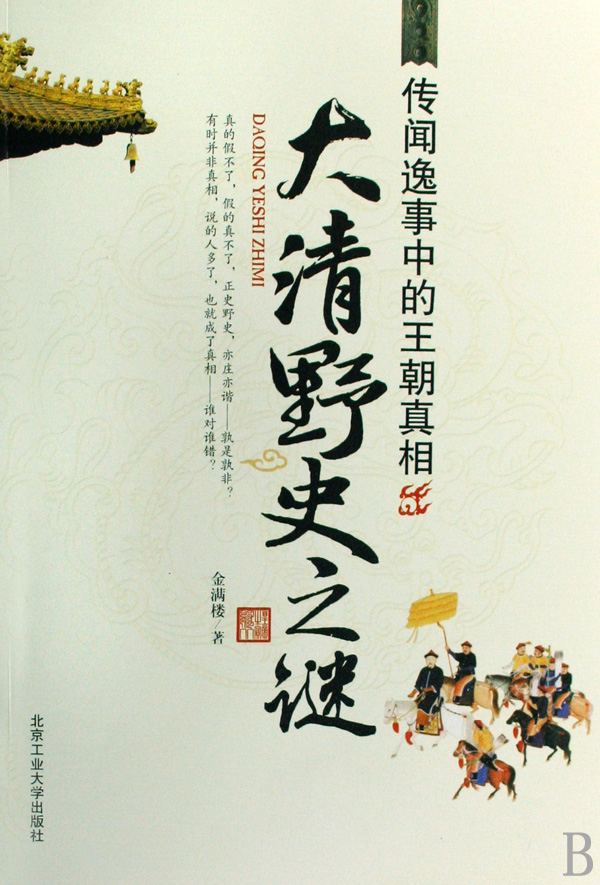百年匪王-第5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这在30万元可是笔巨款。
分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来了,很殷勤地到县政协看望我爷爷,言谈话语间,很是关心款子什么时候到位。
县教育局长来了,请我爷爷到的德顺楼。那个时候的德顺楼虽然还没有上“临朐全羊”,但已承包给个人(后在1991年被祈安哥一次性买断至今)。饭菜十分丰盛,据说上了当时还很稀罕的鲍鱼。
县实验中学的校长也来了,这校长走的是人情路子,七拐八拐,居然续上了他的一个大爷早年曾在山上跟我爷爷干过,说是个机枪手云云,可我爷爷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这些人一客气,反而引起了我爷爷的警觉。有一天差不多半夜,他把电话打到了我单位宿舍的传达室(那时,电话尚未普及),和我关系甚好的传达室大爷又去家里叫的我。
“爷爷,什么事,深更半夜……”
“大事,我琢磨着……”他把县里的表现说了一遍,又说,“这么一搞,我反而不放心。要是把钱打了过来,他们不办正事怎么办?要是让他们吃了喝了怎么办?你不知道,这位副书记够贪的,”爷爷随即压低声音,“你祈安哥要上个水泥厂,他百般刁难,话里有话的说他儿子出国留学需要点钱……”
咦?瞧这块老姜,够辣的……
“说得好,爷爷,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枣庄已经发生过这种现象了,将台胞捐的钱用来办公司和盖宿舍了。”
“所以嘛,我想让你叔叔把钱寄给我个人,就说让我养老的怎么样?”老家伙狡猾狡猾的。
“好主意。这样你就可以掌握主动权了。爷爷,祝贺你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我最后打趣说。
老头子接着说:“谁说是百万,是30万。”很认真的样子。
“好好,30万富翁。”
“这还差不多……”
就这样,30万元很快打到了我爷爷的名下。为这,老人家还专门拿着户口簿去银行开了个户。“累得我够呛。”他逢人便说,“我有钱了,哈哈……”
钱没到了县政府,也没到了教育局,更没到了县实验中学。那些原先对他客客气气的人,见了他也不再理他。有一天,县委那位分管教育的副书记在县府礼堂门口看到我爷爷,却装着没见着的。
我爷爷嘲他啐了口唾沫:“妈了个!”声音很大,估计那位副书记肯定听到了,他本人即使听不到的话,随行的工作人员也肯定听到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吭气的。
我爷爷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末了,又小声来了一句“妈了个”。
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县里的第一大个体户李祈安旗下的一个建筑队开始往崮下村运石料、水泥、砖瓦。问他干什么。他大声说:“给俺爷爷盖别野(墅)。”
很快,全县都知道了,老革命王汉魁要盖别野(墅)。只是到了挖墙基的时候,我爷爷才告诉县教育局,他盖的其实是小学校,说盖别野(墅)是跟你们闹着玩的。
尽管教育局对我爷爷的这个玩笑感到极不高兴,但帮着盖学校毕竟是件好事,教育局的领导还得笑脸相迎,连声致谢。
三个半月后,三排崭新的砖瓦平房建起来了(那时还不时兴盖楼,建材也便宜,水泥4元钱一袋,砖4分钱一块,瓦5分钱一块,沙子论车卖)。我叔叔的夙愿如愿以偿。只是在刻纪念碑时,又多了我父亲的名字。上写:
爱济小学老同学王世荫、王续荫捐建。
看到最后的署名,我忍不住潸然泪下。我朝着台湾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三躬:谢谢您了,叔叔……
还有个小插曲呢。
学校盖好后,还剩下4万多块钱。面对这4万块钱我爷爷犯了愁。这时,崮下村的支书已经换成了穆蛋的儿子,我们不妨叫他小穆蛋。小穆蛋仍是老称呼:“三爷爷,这些钱你自己留着用吧,买点好吃的。”
“去,我吃龙肉也花不了这些钱呀,不行,还得甩出去,不然我睡不好。”
最后,他又帮学校买了个小锅炉,又买了些体育用品。这样一算吧,还剩一万多,学校的校长(是绕弯的三儿)说:“这样吧,三爷爷您把这一万元存到学校的账户上,作为救助贫困学生的资金。”
我爷爷昏花的老眼马上一亮:“咦,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这钱不能给学校。”
绕弯的三儿说:“三爷爷连我也信不过?”
我爷爷说:“不是我信不过你,是我信不过这风气,怎么上边一来人就非要喝酒哩。是来检查教育,还是来检查饭菜?”
这么一说,绕弯的三儿无话可说了:“那您说怎么办吧,老人家,学校里差不多有100多名交不起学费的学生。”
老头子猛地来了一句:“要防止吃‘空饷’!防止吃‘空饷’。”
不仔细听的人,还真听不出“空饷”两个字来,也更不明白他话的意思。
两天后,他把小穆蛋和小绕弯同时找来:
“这样吧,你俩听着。你们马上给我列出个贫困学生名单来,等哪天放学的时候,开个大会。我要给他们分钱,一人一百元,让他们的家长与学生本人同时签字!我要发到户,发到个人,网跟过去在山上分饷一样……”
至此,小穆蛋和小绕弯才明白过来。两位自然不敢怠慢,只好照办。三天后,我爷爷将手中的余款全部散尽。
如今,当年的这批学生中大部分上完了初中,一小部分考了出来,工作遍布潍坊地区。最好的有读了山东师范学院的(现已改为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老家任教。由于基础差,他们没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实事求是。
第六部分
第61章
能上北京不去济南
1986年秋,济南市文联决定要我。条件非常优厚,给一套三室一厅;如评职称,报评副高;同时安排我爱人的工作。
对此,全家都很高兴。
但只有一个人不愿走,那就是我爱人小静。她的理由是:家在枣庄,从小在枣庄长大,兄妹们也在枣庄(她父母已过世,只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怕到济南过不惯。
爱人在家是最小的,从小娇生惯养,我又大她几岁,故平日里处处让着她。爱人不愿去,这下可难坏了我。更重要的是,她放出话来:“如果非要去,就离婚。”
这话把我吓得差点休克。离婚可不是件小事。如果为了去济南而离婚,怕是有点划不来吧。
我爷爷那边倒着了急:“你怎么还不办手续,小心夜长梦多,共产党的事可是说变就变……”
“我……我……”我只好把事情的原委诉说一遍。
电话那头半天没有反应,末了,老头子才说了一句:“那我过去一下……”
第二天,他果然来了。是祈安哥送的他,专为他开了一辆东风牌卡车——他坐在驾驶室,打开车窗——哪怕是冬天,也得开个缝好散汽油味。加上大卡车的座位高,视线远,这样就可以不晕车。以后10多年里,包括他往返于沂蒙与济南,都是坐这种“专车”。
老头子的亲自出马,倒揭穿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爷爷来到后,并不动气,而是在一天晚饭后,同小静娓娓道来:“静儿呀,你虽然文化不高,但也上完了初中,应懂事理才是,新年能去济南工作,是大好事,这对他今后的写作事业肯定是有帮助的。济南是省城,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多人想去还去不了呢?你怎么……”
“爷爷,我怕去了生活不习惯。”我妻子小声说。
“济南到枣庄不过300里,又不是去西藏,怎会过不惯?”
“我……父母不在了,我不愿离开我哥和我姐。”
“这更不是理由,姊妹们大了,都是应独立生活的。再说,过年过节了,你们就不会回来探亲吗?新年的妈妈、弟弟、妹妹也在这儿嘛。”
那时,我弟弟、妹妹已在枣庄矿务局机关工作,并且都已成了家。
“反……反正我是不想去。”妻子任起性来,谁也不好办。
当晚的谈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我爷爷突然神经兮兮地对我说:“新年,不对头,这里边恐怕有别的道道。不然,不会不明‘能上北京不去济南,能去济南不在枣庄’的大事理。要不就是真傻了。
一连几天,我爷爷不再谈这事。他除了逗逗我两岁的女儿娇娇外,就是吃了饭就出门了,直到晚上才回来。
到了第三天晚上,他悄悄来到了我写作的小房间:“地雷的秘密我探到了……”
“行了爷爷,你就别开玩笑了。济南那边又催了。”
“小静有了第三者!”那时“第三者”这名词刚刚流行。
我又差点休克:“瞎扯什么呀,爷爷……”
“是他小时的同学。”爷爷的口气丝毫不像开玩笑的。
“什么?同学?”这又是哪儿跟哪儿呀?
“那人已经在闹离婚了……”
原来,爷爷这几天去搞“侦察”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令我大吃一惊:小静确实跟他们单位的一位男同事来往密切。那人是位科级干部,已公开在闹离婚。这事单位里的人大多都知道。
“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写你的小说。”
“这不可能!”我大声忤气地说。
“你说你大小也是个作家,那人的条件不如你,是吧。”爷爷帮我分析起来,“但你架不住人家整天在一起呀,整天在一起难免会有感情。男女之间就是这么回事!”
仔细想想我有点认了。小静近来是有些不正常,比如讲,提前上班,下了班不按时回来,平时话不多,晚上不让碰,家务不想干,孩子不想看……
“要不我找她谈谈。”
爷爷叹了口气:“没用的。女人在这种事上有一股邪劲,九头牛也拉不回。当年你二奶奶在山上同我闹别扭,就是这股劲,最后还是跟你那四爷爷跑了……”
“那该怎么办呢?”在这类事上,我是个低能儿。
爷爷想了想,一掌拍在写字台上:“以不变应万变!你立刻办手续,不要再耽搁。”
“那她要真的不去呢?”一想到好端端的家要散了,我的心里就……
万没想到,爷爷竟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以为你不去济南,你这个家就能保得住吗?”
我的脸一阵铁青:“这……这么说,小……小静是下定决心了?”
“八九不离十。所以……”爷爷的长寿眉抖了几下,“与其去也是破,不去也是破,那就不如去了。男人,当以事业为重。有了事业成就,还怕没女人吗?凭你这龟孙的条件,咱得找个女大学生!”
没再作任何犹豫,我立刻办了调动手续。
果如爷爷所料,我的婚姻没撑一年,最终还是分手了。分手时,我争取到了女儿的抚养权(爷爷说,咱什么都不要就要孩子)。
半年后,前妻同她的同学结婚。婚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两人过得很好,在此,我祝福他们。
。。。。。。
这段时间里,家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叔叔去世了,死于心肌梗塞。
爷爷听到这一消息时,正在老家,据说,他一听我堂哥打来的长途,当时就昏了过去,亏了祈安哥、刘奶奶及时把他送到了医院。
我接到祈安哥的电话时,正在济南。我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当天就赶回了沂蒙(从济南到沂蒙比从枣庄到沂蒙方便多了)。
爷爷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祈安哥和刘奶奶照顾着他。他瘦多了,那股安静劲就像个还没满月的婴儿。听说我来了,他还有点不高兴:“你来干什么?工作那么忙。”
我知道他心里挺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