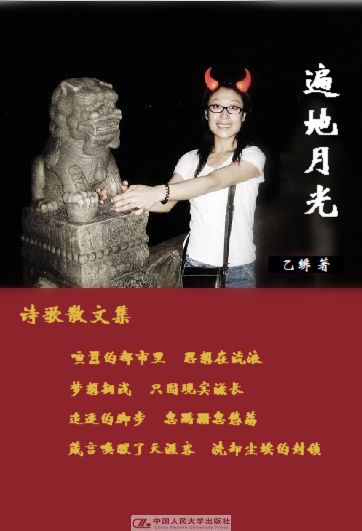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末了的一个先生,即是章太炎先生。他的自以为专长的政治,我不能赞一辞;他的学问,我也一点都不传授到。但我总觉得受了不少影响,革命前后的文字上的复古或者也是一种,大部分却是在喜欢讲放肆的话,——便是一点所谓章疯子的疯气。我所记得的太炎先生,总是那个样子:在《民报》社的一室里,披发赤膊,上座讲书,学理与诙谐杂出,没有一点规矩和架子。诸大弟子分得他的各门学问,分到我名下的大约只是一篇集内不收的《哀陆军学生文》与“政闻社”开会的记事罢了。换一句话,就是我只学到太炎先生的喜欢讲玩话,喜欢挖苦人的一点脾气,这或者不能说是善学太炎先生者,但受感化总是一样,也不得不承认感谢的。这种影响都是天然的关系,在于人力以外,当时也曾遇到《天义报》时代的刘申叔先生,但是我一毫都不受到他的感化,正如在他的《国粹学报》时代一样;其间只有一件相同的事,便是我的字之拙劣不下于刘先生:不过这是我从小如此,并不是那时才学坏的。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译名问题质疑
1951年3月15日刊《翻译通报》2卷3期
署名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翻译通报》二卷二期上有周华松先生的一篇《统一译名和拉丁化》,依据鲁迅的“就用原文”的原则,主张将外来语的专门名词和学术名词,写成新文字夹入汉字当中。这里有两点颇有疑问,所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其一,学术名词都用原文,这事可能与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说就用原文,本是指化学原素那些名称而言,那虽然也属于学术名词,却是专名的性质,万国共通的,它只有拉丁名,拿过来可以干脆地应用。若是别的,即使也是拉丁文,如维他命、盘尼西林、赛璐珞、德律风等,据王宗炎先生的《音译和义译》文中所说,已逐渐由音译转为义译,所以要将学术名词都用原文,与这趋势正是背道而驰。自然有些部门如理化医工的术语,是完全专门性质,音译可能比义译适宜,这须得由专家去考虑决定。但是用它那一种原文呢,虽然原语也同出于拉丁,各国有不同的说法,或是只大同小异,而读起来却各有一套,例如心理学这字的原文,英德读音首尾两个就很不一样,那么以那个为凭呢?周先生说统一译名,这事确实是必要,其中当然有音译义译两部分,假如译语纷歧,不便实多,这也并不限于用汉字的中国,如英文中屠格涅夫的音译便有四五样的拼法,所以统一的工作正是当务之急。义译部分自然不用原文了,有如盘尼西林是音译,义译则是青霉素,若是称它作青霉素,又用拉丁字母拼了,那似乎没有什么意思,反不如仍旧称为盘尼西林了。这样归结起来,可以用原文的,第一是化学元素的名字本来是拉丁文,与罗马人名一样,顶不成问题地可以应用(其中金银铁等也不得不用义译了),至于学术名词全用原文,是否适宜,我觉得还有讨论的余地。对于译名这问题,我大体上是赞成王宗炎先生的意见的,他的两篇文章见《翻译通报》第一卷五六两期上。
其二,人地专名,即是专有名词,照例只有音译一法,古来西土译经高僧的名字都有意义,附加义译,但是鸠摩罗什与佛陀耶舍,至今还是这样叫,没有人叫他们童寿与觉明的了。我前回说音译当名从主人(近重阅王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倪海曙先生早有这个主张了),却仍用汉字来写,我承认中国往往有音无字,译来多有牵强,是个缺点,可是没有办法,要理想的彻底的办法并不是没有,但又难以实行,譬如用原文即是。我们姑且将亚洲非洲的民族除外,单说欧洲的,有受东罗马文化的一系,用的是希腊字母以及从这里变化出来的斯拉夫系字母,有受西罗马文化的一系,用的是从希腊变化出来的别样的罗马字母,前者为希腊、苏俄及斯拉夫系各国(波兰捷克除外),后者为西欧各国,加上波兰与捷克,他们也改用拉丁字母了。就只在这个范围内,要用原文,也就很伤脑筋了。第一,这至少要三套字母,即希腊、斯拉夫、拉丁,对于排印者与读者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若是让步,放弃前两套,只留下末了的,结果是牵就了西欧,论理原是不大公平的。至于事实上呢,我们不说匈加利等国拼法特别的,就只是英德法三国也仍有好些困难,同一个写法的名字可以有三样不同的读音,写出来原是同样的拉丁字母,要读者自己去分别,英国人名照英文读,法国人名照法文读,这在少数知识阶级自然可以办到,在一般读者未免有点为难了。周先生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说明“写成新文字”,不过既然改写一遍,那已经不是原文了,例如英国诗人摆伦,这两个汉字诚然不好,但如将Byron拼音写作Bairn,那与摆伦也只是百步五十步之差,而且英国可能真有姓Bairn的人,更易混淆,不是很好的办法。用拉丁字母的国家,没有把别的用拉丁字母的国人名字改写拼音(即是音译)的,他们都是用原文,只在字母不同的文字里才用音译,所以中国对于外国专名只好用汉字译音,若是译文是用汉字所写的。这倒也并不是恐怕“汉拉并用破坏了原来文字的民族形式”,如有必要时我想原文是尽可插入的,譬如专名译音,欲求忠实,不妨于译音下用括弧记入原文,这如是原来用拉丁字的,那本不成问题,若是别系文字,则用拉丁字对音,有如摆伦(Byron)、屠格涅夫(Turgeniev),普通也是常用的,有时候也可以引用一段原文,这却翻过来于括弧中加上译文就好了。我们查看《鲁迅全集拾遗》中几篇翻译文章,一九二八年的《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一九三年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都用拉丁字母拼写人名加入,不另译音,一九三三年的《海纳与革命》等这几篇,则先译音,于括弧内加写原名,与我们上文所说的办法相同。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于外国专名有两种表现的方式,理论上的是非是别一回事,对于读者那一种觉得方便,那当问读者的意见如何,不是我们所能主观地决定的了。
原意只想关于一两点稍陈意见,不料写得很拖沓了,却仍旧没有能够说得清楚,只好就此结束了。末后我想附带说明一句,对于新文字我别无研究,但觉得改用拼音文字的理想总是很好的,不过我对于使用拉丁字很不赞成,这里并无什么深远的道理,我只感觉它不适用。要拼中国的语音,最好还是用斯拉夫系字母,因为它至少没有用两个字母来表一个声音的毛病,虽然ng这音还是缺少,须得用国际音标里的长脚n来补充才行。它于阿厄俄乌之外,另有耶也育由四个母音,这是别种字母中所少有的,朝鲜的谚文里也有,我一直很是佩服。这与翻译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现在只是顺便说及,所以也就不多赘述了。
翻译与字典(1)
1951年4月15日刊《翻译通报》2卷4期
署名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假如让一个稍有翻译经验的人来诉苦,那么除了自己对于外国文的了解不够、本国文的能力薄弱之外,第一要说的是没有好字典。学过几年外国文,例如英文,当然会得使用原文字典了,《奥斯福简要字典》从前只要三先令半,也就很不差,我们所说没有好的乃是英汉字典。大部分的字查原文字典可以明白,可是名物字那里只有说明,而我们所要的则是对译的名字,这是只在英汉字典上才能有的,所以即使我们有了奥斯福的大字典,这英汉字典还是非有不可,所可惜的是英汉“英汉”原作“汉英”。字典尽多有,而好的却极难得,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说也奇怪,中国人学英文在东亚算最早,邝其照编的一本字典,还颠倒地叫作《华英字典》,据说日本福泽谕吉学英文时,就是利用这本书的,可以够得上说是东洋第一册英文字典了吧。但是到了现在,却还没有好的字典,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光说没有好字典,未免太是笼统,须得说得具体一点才好,现在就引用鲁迅的话来做个开端吧。鲁迅于一九二七年译了荷兰望蔼覃的《小约翰》,在引言中叙述他译书的经过,中间诉说自己力量不够,本来清晰的原文译出来成了蹇涩的文句了,随后又说,“动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难”。这困难原不很大,只要有字典可查,我们的困难是在缺少这种可查的字典。书后附着一篇《动植物译名小记》,这里较具体地说明这个困难,他把德文的植物名字托人查出学名来,然后再查中国名,所依据的是“中国惟一的植物学大辞典”,可是成绩不大好。《译名小记》第二第三节云:
但那大辞典里的名目,虽然都是中国字,有许多其实乃是日本名。日本的书上确也常用中国的旧名,而大多数还是他们的话,无非写成汉字。倘若照样搬来,结果即等于没有,我以为是不大妥当的。只是中国的旧名也太难。有许多字我就不认识,连字音也读不清,要知道它的形状,去查书,又往往不得要领。经学家对于《毛诗》上的草木鸟兽虫鱼,小学家对于《尔雅》上的释草释木之类,医学家对于《本草》上的许多动植物,一向就终于注释不明白,虽然大家也七手八脚写下了许多书。我想,将来如果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之外,还须博访各处的俗名,取其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则别的且不说,单是译书就便当得远了。
我们就上边这两节文章,找个实例来看。例如英文plane tree一字,亦作platan,学名云platanus orientalis,查字典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不去找《植物学大辞典》,只找大书店的有名字典来看吧。在《综合英汉大辞典》上查到plane tree,下注悬木三字。这名字写的是中国字,但是中国人谁也不能懂得,这悬(hsiao hsüan)怎么讲,悬木是什么树。这是难怪的,因为如上文所说此乃是“他们的话,无非写成汉字”罢了,必须将它复原,写成日本文,读作Suzukake no ki,这才能了解它的意思,知道是日本新定的platanus的译名,植物学上也有悬木这一科。悬在日本古时是一种麻制的衣服,在山野修行的方士穿在身上,用以防备竹上的雨露的,这种衣服现今也早已没有了。像长马褂似的一件衣服,与这树有什么关系呢?有人推论这木名应该读音仍旧,汉字写作铃悬才对,植物中有一种小粉团,又名麻叶绣球的,一名铃悬,可以为证,其实这是不对的。悬衣在合缝处钉有若干*结,以防绽裂,形状仿佛是西式大衣上的假扣,悬木的球果与它相像,故有此名,便是小粉团的俗名当初也该是悬,后来因为难懂,所以改为铃悬了。由此可见悬二字在日本已是不容易了解,拿到中国来,怎么能用呢?以前我根据platanus的语源出于platys字,曾译作阔叶树,友人告诉我颜惠庆编的字典上译作枫杨树,疑是根据叶的形状而新制的名目(或云枫杨乃元宝树的别称,此处误用),又听人说,民间俗称法国梧桐,这类洋字排行的名字本来不很高明,但是洋槐西红柿(或番茄)现已通行,从前也有胡麻胡萝卜,与其用悬木,或者不如索性称作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