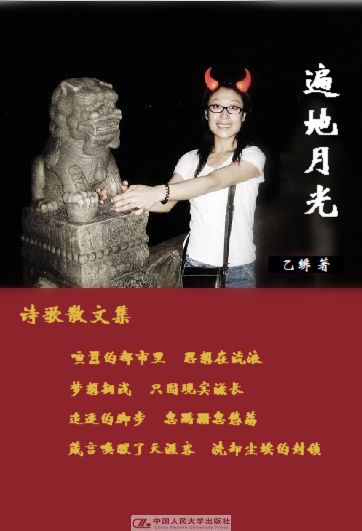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纪生附记]附记系1929年4月10日《绮虹》编者所加。此文系周先生在民国十二年所写,十月十九日者,即该年十月十九日也。我以该文未曾收入《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诸书,而文中所论新文学趋势极简明透澈,且鉴于最近文坛之混乱,因商得先生同意,刊载于此,俾爱好文学者有所参考。(一九二九,春,宣南)
宿娼之害
1923年10月21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子荣
未收入自编文集
宿娼之害,应当分别言之。对于过着恋爱生活的人,其害有二:(1)破坏恋爱,(2)染毒。对于传统地结婚的人,只是染毒一样。因为这些人本来没有恋爱,说不上破坏,而且在性的关系上原是“视女子为玩物”,无从增加轻蔑的程度;“宿妻”与宿娼正是一样,所差者只在结婚是“养一个女子在家里,随时可以用”,不要怕染毒,更为安稳便利罢了。传统的结婚即是长期卖淫,这句话即使有人盛气地反对,事实终是如此。大家恭维宿妻而痛骂宿娼,岂不是只知道二五得一十而不知五二也是一十么?
因此,我觉得前回劝告芜村君的话是不错的。我决不敢对于芜村君的品性妄加推测,但他不是过着恋爱生活,他与老夫人的关系只是性的要求,这是我敢大胆地假定的。现在他既然不满,那么自然只好去宿娼,比另外去买一个妻来宿,比较的还要老实一点,虽然也危险一点。中豪君劝他离婚另娶,当然比命令禁欲好的多了,但看芜村君在家庭里的情形,连阻止他令郎的早婚还没有力量,能够和老夫人离婚么?即使做到了,(这个已经要认为奇迹)另娶一位少夫人,如不是恋爱的结合,那也无非是购置一个可宿的目的物,与宿娼有什么不同,不过名目好听一点罢了。讲到中豪君的提议,在根本上与我的本没有不同,只是中豪君还有点顾虑名目,我则以为宿妻同宿娼一样的不道德,(而且因为大家恭维,或者更为不道德)所以劝他还不如去宿娼,虽然也愿意他因为怕染毒而少去。
中豪君所说的预备办法,我十分赞同,希望大家丢起灵呀精神呀的高调,实地去宣传性道德的改革。
编辑者的删削权
1923年11月2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去年《晨报》副刊上有过一回笔墨官司,被《觉悟》的记者评为编辑失职,他以为足以引起争闹的文字是不应登载的。他的话虽稍偏一点,却很有道理,我想编辑者的删削权至少是应该利用的;近来见了“西大”之争斗,更觉到这个的必要。
大悲先生译错,西滢先生给他纠正,那是极好而且极应该的,但是其中有些挖苦话,倘若我是副刊记者,当替他删节一下,至于学庄先生以下的几篇则更大加以斧削,或者竟不客气的没收。许多苦心孤诣的刻薄话,只在当事人有些影响,在第三者看了只是觉得不愉快罢了,——倘若双方必要纠结下去,不肯罢休,最好的办法还是由记者居中代为传递战书,各方面都可以得到满足。强词夺理的执辩的话,看了也不是愉快的事。其次是随意的猜疑,如学庄先生猜西滢是甲,西滢先生猜学庄是乙,而静庵先生又猜甲乙有什么关系,都是可以不必的。我见了这场恶战,不能不归咎于副刊记者之疏忽,当时只要他肯略加删削,便没有这场口舌,而误译的纠正我们仍能见到。
正如擘黄先生所说,喜欢笑骂别人“寻开心”,是人类普通缺点,很难完全铲除;为了毫不相干的事,我也常喜写几句挖苦话登在报上散散闷。但是我总想守定这个主张,便是宽于责个人,严于责社会,庶几乎不至于有什么过失。倘若偶然失检,便请编辑者给我一个大黑杠,涂去几行,我很情愿。——但这只是限于违反“批评的伦理”的时候,才可如此,倘若借此要来修改我有时所发的偏激之论,那是我对于记者又要抗议的了。
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土之盘筵(二)
1923年7月28日刊《晨报副镌》
[译文]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洋房的前面。一匹乡下人模样的小老鼠出来。)
乡鼠我是住在很远的乡间农家的一匹老鼠。有一个朋友长久住在京里,日前回乡来,对我说京里有各种阔气的东西和好吃的东西,叫我去玩,所以现在上京都去。(走着)的确,这些人家,道路,什么一切,都很阔气。(四面探望着,走着)呀,一定是这家了。(站住)且叫门看罢。……喂,吱吱吱,有人么?吱吱吱!
(一个穿洋服的老鼠从里边出来。)
京鼠:呀,你么?我从那时起就等着你呢。来得很好。是坐火车来的么?
乡鼠:是,是混在货物里来的。但是,到了总站正想下车的时候,在那里有一只大野猫,几乎被他衔住了。真骇死我了。
京鼠:亏你知道这是我的住家。
乡鼠:可不是这里有你的小便气味么。
京鼠:鼻子有这样灵,就是住在京里也站得住了。
乡鼠:但是,我不知怎的总觉得有点恐慌呢。各种的车呀马呀,还有许多的人,这样跑来跑去的。
京鼠:不打紧,惯了就一点都没有什么了。而且,还有许多好吃的东西呢。现在这个人家刚要开宴会了,在厨房里,已经摆着各色好吃的东西。请你到这边来看罢。
乡鼠:不要紧么?不会被看见么?
京鼠:不要紧,不要紧。
(京鼠在前引路,乡鼠抖抖擞擞的跟在后面,走来走去。在同一地方打两个圈子,算是到了厨房。)
京鼠:你看,怎样!这样阔气的器具,不曾见过罢?这个碟子,(这个和下文的银碗都只要假设放在那里就好,无须用实物。)一张要二十块钱呢。……那边的银碗里,盛着上好的干酪。那才是好吃呢!今天盖好了盖子,有点不行,但是或者还有不很合缝的地方也说不定。我就用了这个鼻子,这样的把他掀开,……(这样那样的掀了一会,盖子有点开了。)好了,开了开了!……你看,怎么样!很好吃的样子罢。请随意用罢,我也动手了。好吃,好吃!
(两匹老鼠共吃银碗里的干酪。)
京鼠(停吃):好吃罢,……请你试坐这把软椅。柔软而且温暖,很舒服罢?现在我在那边堆房里的旧太史椅中间做着窠,或者索性在这横边开一个穴,移住到这里来罢。同桌子相近,要偷东西吃也很便当。请你帮一点忙,我们咬一下子看。
(两匹老鼠在软椅的横边,嘎哩嘎哩的咬起来。)
京鼠(突然停咬):呀!喂喂,且住!(竖起耳朵听着)来了,来了,来了!听差进来了!快逃,快快!
(两匹老鼠急忙躲在软椅底下。)
(洋房的听差二人拿着棒梢和扫帚,急忙的出来。)
听差一:那个阴沟老鼠又来了。阿呀,已经啃的这个样子了。真是没有法子。
听差二:可恶的东西,一定还躲在什么地方。把他找出来,打死了罢。
听差一:这样很好。你往那边去赶,我从这里赶过去。……唆,唆!
(两人从左右两面用棒在软椅下撩拨。京鼠与乡鼠逃出。)
听差一:唆,在这里!唆,唆!
听差二:唆!唆,唆!
(两匹老鼠被两人追着,且跌且滚的逃入。听差追着进去。过了一刻,京鼠与乡鼠又出来。——算是在洋房的横边,但不必用什么背景。)
乡鼠: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京鼠:几乎着了他的道儿。真危险极了。
乡鼠:你时常遇见这样的事情么?
京鼠:唔,自然遇见。常常遇见呢。
乡鼠:喂,常常么?
京鼠:那自然。这才是京都呀。有好的事情,也便有坏的事情,时常有可怕的事情,但因此也能够吃到许多好吃的东西哩。
乡鼠:无论怎样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想到这是偷着吃的,我也不愿意了。我就要回到乡间去了。在乡间,只吃那掉在地上的东西,已经尽够过活,而且无论什么人都不至于杀我。朋友,再见了。
[附记]这一篇儿童剧,取材于《伊索寓言》,是日本坪内逍遥所作,从他的《家庭用儿童剧》第一集中译出。关于儿童剧的内容本来有应当说明的地方,现在不及说了。
《土之盘筵》我本想接续写下去,预定约二十篇,但是这篇才译三分之一,不意的生了病,没有精神再写了,现在勉强译成,《土之盘筵》亦就此暂且停止。这里虽然说“暂且停止”,实际上到1924年1月17日刊出第十篇《老鼠的会议》后才停止。——不过这是我所喜欢的工作,无论思想变化到怎样,这个工作将来总会有再来着手的日子。因为即使我们已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来给小孩们讲笑话。
我的负债
1924年1月26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在书房学校里我曾有过不少的先生,但于思想及文字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在外边却有几位的文章言论给予我好些感化,为我所不能忘,现在想约略纪述出来,表示我的精神上的负债。
这些先生里边,最早的自然要算光绪年代通称的“康梁”。政变的时候,我才十四岁,住在东南的海边,不懂得什么,到了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这时候的愉快真是极大,至今每望见梁先生还不禁发生感谢之意。康先生的著作老实说不曾多读,《新大陆游记》作者为梁启超,上句说是“康先生的著作”,盖作者误记。还有点记得,但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仿佛觉得他老人家虽是*,同我们后辈到底隔着一段距离,不必等到做“不幸而言中则……”便已觉着有点隔膜了。
其次,我所爱读的,是严几道林琴南两位先生的译书。严先生著书的全部当时都搜集完全,林先生的也搜到光绪末年的出版为止。那时我相信《天演论》的达旨是翻译的正宗,只是非有极大的才学不办,所以只能悬作理想的标准,严先生译《法意》时也就变换方法,我见他对于文义暧昧的地方,译出原意不加附会,却用注说明未详,这个办法我至今还很是佩服。《英文汉诂》一书虽是大体根据马孙等文法编纂而成,在中国英文法书中却是惟一的名著,比无论何种新出文法都要更是学术的,也更有益,而文章的古雅不算在内,——现在的中学生只知道珍重纳思菲尔,实在是可惜的事。我读林先生的译书,从《茶花女遗事》起,以《迦茵小传》时代为顶点,至《拊掌录》前后而逐渐停止。我虽佩服严先生的译法,但是那些都是学术我的负债书,不免有志未逮,见了林先生的史汉笔法的小说,更配胃口,所以它的影响特别的大。我在民国以前译过几篇古文小说,其中有不少林派的字句,现在还约略记得。洪宪的严先生与五四以后的林先生都不是我所敢恭维的了,但在清末,两位先生译述的事业总是不可埋没,因为他们也正是新文学的先驱呵。
我的末了的一个先生,即是章太炎先生。他的自以为专长的政治,我不能赞一辞;他的学问,我也一点都不传授到。但我总觉得受了不少影响,革命前后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