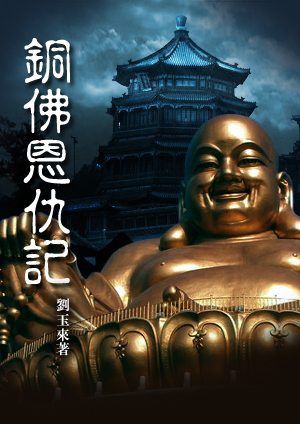李敖快意恩仇录-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社会地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大多了!当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我也不以为异。偶尔时候,我也满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少这些人都口蜜会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笑,并对人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已经走下坡,靠他吃饭的一些国民党,为了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开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只是其中之一),人把这些形式和范畴加到感性的素材上去,,同他反目。这些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根据他们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列出罪名有九,第一条就是“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
最精彩的,是他们在一九七0年七月公布了“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致治安机关的检举信,里头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美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这些国民党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亲笔字迹,公布于下:
1.艺术有价,政治无情。
2.“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颜。
3.接受李敖忠告,把国联向新的路线发展。
4.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坚持。
5.在蒋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用为罗织的张本。最后,他们又造谣说李翰祥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于是,这回生了沈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终于动手,在李翰祥家秘密装上窃听器,并把他约谈。李翰祥对这件事很怄,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回忆说:
他们的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名信,还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是冤枉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李翰祥来台湾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诗”,这种动作,又怎么解释呢?不过,国民党疑神疑鬼引发出来。这件事后果倒非常严重,李翰祥因我被国民党诬陷,以致一再进出警备总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反感、愤感与恐惧,使他自台湾一脱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愚笨的国民党再也没有想想到他们为了整李敖而诬陷李翰祥、约谈李翰祥,竟造成这么深远的损失:他们失掉了这么一位得力的艺术工作者。在台湾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缇萦》,他是相当投合国民党的趣味的。他走了以后,国民党“闻鼓鼙而思良将”,也千方百计拉他回来。党方拍《英烈千秋》的时候,中影的梅长龄保证李翰祥在台湾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话说:“可是,梅先生,谁保证你的安全呢?”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国民党再拉李翰祥,可是李翰祥怕警总,他要国民党军方的最高层人士给他保证安全的信,国民党是从来不会对人认错的、抱歉的,并且还不知自己是老几的向它势力所不及的地方摆高姿势、摆大架子。最后,李翰祥终于用行动去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作了。-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败。当然,国民党是很腐败的,他们不腐败,也下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三十年后,一九九六年,李翰祥在海外报上发表《戏言戏语》,有“我与李敖初相识”等三篇文章写他和我的交往,读了以后,恍然如昨。他提到李敖“伶牙俐齿,风趣幽默,逻辑性强,所以言之有物,令人听之动容”等等,皆写实也。
在李翰祥家作客时,见到他太太张翠英女上,美人儿也,虽岁华老上,余妍犹见当年。有一次在席中谈及李丽华的年龄,我们客人所记得的岁数,都被张翠英否决,而她所说的岁数,都比我们说的小了许多。我们知道张翠英对李丽华素无好感,如今对“影敌”的年龄,竞力加维护,宁非可怪、后来才悟出道理:原来当年张翠英和李丽华固同台演少女戏者也,两人固然争“雌”,但却同庚,替李丽华瞒岁数,就是替自己瞒岁数;把李丽华年纪瞒住,别人就难以类推出自己的年纪,可见为人者己愈有、瞒人者人亦瞒之,年龄互保,人同此心,大家有所保留,亦大好事也。
我卖旧电器找买主,因为演艺圈内购买力强,所以结交此道中人甚多,这些人多好赌,我也因缘随之,以我一表人才,遇赌甚精,所以赢多输少,对生活亦有大补。赌友中有李翰祥的经理外号“刘必跟”者,此人不信邪,每张梭哈之牌,必然跟进,认为可有奇迹出现,这样打法,当然把把过瘾,可是十打九输。有次输火了,开的支票不认账,反倒告我和蒋光超联手诈赌。法官开庭调查,我说:“凡诈赌者,必然联手者交情很深,方有可能。可是我当天晚上才认识蒋光超,难道是我们上辈子串通好的?”被告蒋光超也在旁证实当晚才认识我无误。法官乃问“刘必跟”:“你告李敖、蒋光超诈赌,有何证据?…刘必跟”说:“我那天记了日记,有我自己的日记为证。”我说:“这叫什么证据!如果他日记里记我是匪谍,难道我就是匪谍?这种日记太可怕了!”法官点头,最后间我:“你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在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说着朝“刘必跟”一指,大声道:“这种人牌打得这么糟,凭真牌就可赢他,何须做假牌!”后来我被警总抓去,办案人员告诉我,本来他们想趁机用诈赌罪整我的,因为整我就连带整到蒋光超,并且扣李敖以诈赌之罪,无人会信,乃放弃此议,不了了之。但这一凭真牌可以赢人、谁还要做假牌的赌钱观,却成了我的人生观。虽然是被诬告一场,但名誉受损,也在意中。蒋光超打电话来,问《联合报》登他和我豪赌之事何不解释,我说:“人家说我是‘匪谍,我都不解释,何况是‘赌徒’?”他听了一笑开悟,也不解释了。
我在被诬告诈赌时,已日夜在软禁状况下。一九七0年一月软禁一开始,是由警察以假计程车跟踪的,到了七月十八日,有了新状况-多了一部车。我决定展开报复,我跟他们来一次“捉迷藏”。这次“捉迷藏”捉到日月潭,全部过程,那时刚从铭钏毕业的小蕾留下细部的日记,这是难得的一篇完整记录,我全部附在后面:
好好的一次毕业旅行,却被自己的一句话Cancel掉了,正后悔着,没想到四天后因他们去了趟日月潭。
十八号早上十点多胖来,告诉我说:“从清晨五点起增了部车,刚才我去找罗警员叫他转话给李分局长如在三个钟头内不撤走部车,我定给他们好看。”“罗警员怎么说呢?”“他说:‘我转,我转。’由今天起移居警总了,他们需要二天时间见习。”“你怎么对付他们呢?”“开车子兜着他们乱转,我己叫小八保养车去了,且把油加满,大家斗着看好了。”我不喜欢胖跟他们斗,这事已延续了四个多月了,多一部车固然很令人不快,再斗也不可能将半全部撤走,四个月都过来了,又何在乎这二天呢,可是胖这种人已决定这么做了再说也是白说,只能拼命往好的方面想,二点时他们一定会撤走一部车的,如那时还是二部车再想办法也下迟,就跟胖走小路到菜市,买了些菜回家补魏胖。到了二点,他们一动都不动,胖就决定不让他们知道去一趟台中,后来也把我算了进去,就计划着,怎么样的方式最好,“我先回家提点钱,理好了箱子,等六点钟在侨联宾馆与胖碰头,车子由小八直接开去侨联宾馆,而胖丢开他们去侨联等我。”这就是我们丢了他们离开台北的法子,其中胖花了七十元的计程车钱,包括五十元奖励司机摆脱他们,胖的确是个想得周到的小心人,除了带双使脚舒服的布鞋外,还带了金丝边的眼镜,一箱可口可乐(怕他们在旅馆的水内放毒)。到了三重我多次转身看后都没看见他们的车子,谁又晓得我们已在往台中的道上了。
近七点半到了新竹,吃了晚饭,买了二本杂志,四卷彩色照片、二块话梅(真亏买了)及一罐糖。胖把车子玻璃擦干净,换了布鞋,前后花了大约一个钟头,我们又南下了,一路上真舒服,也许这天是十五吧!月色好得没命,又有凉快的风吹着,并且没有人盯着我们,每次我都说:“有什么关系,他们要跟,就让他们跟吧!”这不是真心话,如果真有个车子跟着我们,就不会有这种说不出的愉快了!一路上,胖告诉我,有车迎面来最好将远光灯换为近光灯,这是种礼貌,且不会刺着对方的眼睛。我就一路留心着看,果然如此,有的车不这样,我就会说句“这车不懂礼貌”。有一次,胖将灯换错了,对方的车立即又换成远光灯,且经过我们时长按了声喇叭,吓了我一跳,原来是那司机报复,人常常都会将别人不经心犯的错,视为有意那么做的,胖就是这种人,我随口说出的话,他一定要解释成我故意气他才这么说的,到了头份,要进入尖丰公路了,可是转了又转就是找不着路,在公路局车站停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又开始找路。最后还是花了八块钱买本大学杂志才问出来,入了尖丰公路,就像走进了山堆,前啊后的、左啊左的都是山,但在这前面没有一点阻挡,路面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