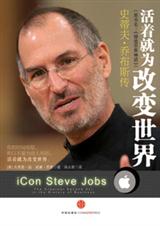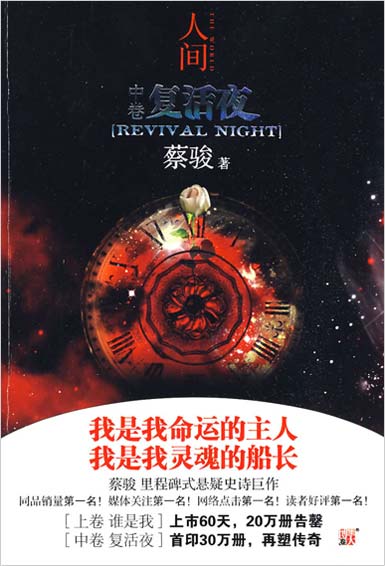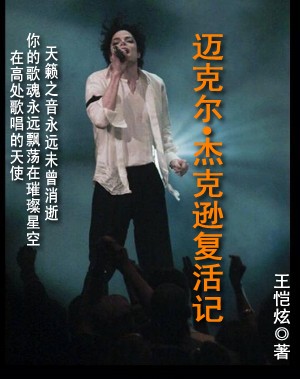复活[列夫·托尔斯泰]-第7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垂下眼睛。
“减刑批准了,您知道吗?”聂赫留朵夫说。
“知道了,看守告诉我了。”
“这样,只要等公文一到,您高兴住哪里去就可以住哪里去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
她赶紧打断他的话:
“我有什么可考虑的?西蒙松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
她尽管十分激动,却抬起眼睛来瞧着聂赫留朵夫,这两句话说得又快又清楚,仿佛事先准备好似的。
“哦,是这样!”聂赫留朵夫说。
“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倘若他要跟我一块儿生活,”她发觉说溜了嘴,连忙住口,然后纠正自己的话说,“倘若他要我待在他身边,我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指望呢?我应该认为这是我的福气。我还图个什么呢?……”
“也许她真的爱上西蒙松,根本不要我为她作什么牺牲;也许她仍旧爱我,拒绝我是为了我好,不惜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命运同西蒙松结合在一起。二者必居其一,”聂赫留朵夫想,不禁感到害臊。他觉得自己脸红了。
“要是您爱他……”他说。
“什么爱不爱的!那一套我早已丢掉了。不过,西蒙松这人确实和别人不同。”
“是啊,那当然,”聂赫留朵夫又说。“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我想……”
她又打断他的话,仿佛生怕他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或者生怕她来不及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
“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要是我做的不合您的心意,那您就原谅我吧,”她用她那斜睨的目光神秘地瞧着他的眼睛,说。“嗯,看来只好这样办了。您自己也得生活呀。”
她说的正好是他刚才所想的,但此刻他已不这样想,他的思想和感情已完全变了。他不仅感到害臊,而且感到惋惜,惋惜他从此失去了她。
“我真没料到会这样,”他说。
“您何必再待在这儿受罪呢?您受罪也受得够了,”她说,怪样地微微一笑。
“我并没有受罪,我过得挺好。要是可能的话,我还愿意为您出力呢。”
“我们,”她说“我们”两个字时对聂赫留朵夫瞅了一眼,“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您为我出的力已经够多了。要不是您……”她想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发抖了。
“您不用谢我,不用,”聂赫留朵夫说。
“何必算帐呢?我们的帐上帝会算的,”她说,那双乌黑的眼睛泪光闪闪。
“您是个多好的女人哪!”他说。
“我好?”她含着眼泪说,凄苦的微笑使她容光焕发。
“您好了吗?”①这时英国人问。
“马上就好,”②聂赫留朵夫回答。接着他向卡秋莎打听克雷里卓夫的情况——
①②原文是英语。
她强自镇定下来,平静地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克雷里卓夫路上身体很虚弱,一到这里就被送进医院。谢基尼娜很不放心,要求到医院去照顾他,可是没有获得准许。
“那么我该走了吧?”她发现英国人在等聂赫留朵夫,就说。
“我现在不同您告别,我还要跟您见面的,”聂赫留朵夫说。
“请您原谅,”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从她古怪的斜睨的眼神里,从她说“请您原谅”而不说“那么我们分手了”时伤感的微笑中,聂赫留朵夫明白,她作出决定的原因是后一种。她爱他,认为自己同他结合,就会毁掉他的一生,而她跟西蒙松一起走开,就可以使他恢复自由。现在她由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感到高兴,同时又由于要跟他分手而觉得惆怅。
她握了握他的手,慌忙转身走出办公室。
聂赫留朵夫回头瞅了一眼英国人,准备跟他一起走,可是英国人正在笔记本里记着什么。聂赫留朵夫不去打断他,在靠墙的木榻上坐下来,忽然感到无比疲劳。他所以疲劳,不是由于夜里失眠,不是由于旅途辛苦,也不是由于心情激动,而是由于他对整个生活感到厌倦。他靠着木榻的背,闭上眼睛,顿时沉沉睡去,象死人一般。
“怎么样,现在去看看牢房好吗?”典狱长问道。
聂赫留朵夫醒过来,看到自己竟在这里睡着了,不禁感到惊讶。英国人已写完笔记,很想参观牢房。聂赫留朵夫就疲劳而茫然地跟着他走去。
26 参观刑事犯牢房。英国人分发福音书
典狱长、英国人和聂赫留朵夫在几个看守的陪同下,穿过门廊和臭得令人作呕的过道,走进第一间苦役犯牢房。在过道里,他们看见两个男犯直对着地板小便,不禁吃了一惊。牢房中央放着一排板床,犯人都已睡了。里面大约有七十个人。他们躺在那儿,头挨着头,身子挨着身子。参观的人一进来,个个都从床上跳下来,铁链哐啷发响,他们站在床边,新剃的阴阳头闪闪发亮。只有两个人躺着没有起来。一个是年轻人,脸色通红,显然在发烧;另一个是老头儿,嘴里不住地呻吟着。
英国人问,那个年轻人是不是病了很久。典狱长说他是今天早晨才发病的,至于那个老头儿,闹胃病已有好久,可是没有地方安顿,因为医院早就住满人了。英国人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想对这些人讲几句话,要求聂赫留朵夫替他当翻译。原来英国人这次旅行,除了要写一篇反映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禁地的文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宣讲通过信仰和赎罪来拯救灵魂的道理。
“请您告诉他们,基督怜悯他们,爱他们,而且为他们死去,”他说。“如果他们相信这道理,他们就可以得救。”他讲话的时候,全体犯人都挺直身子,双手贴住裤缝,默默地站在板床前面。“请您告诉他们,”他结束说,“在这本书里所有的道理都有。这儿有识字的吗?”
原来这里有二十多人识字。英国人从手提包里取出几本精装的《新约全书》。于是就有几只肌肉发达、生有坚硬黑指甲的大手,从粗麻布衬衫袖口里伸出来,争先恐后地来要书。英国人在这个牢房里发了两本福音书,然后往下一个牢房走去。
下一个牢房情况也一样。里边也是那样气闷,那样恶臭;前面,两个窗子中间同样挂着圣像;左边放着一个便桶;犯人也都那样身子挨着身子,拥挤地躺在那里;他们同样都从床上跳下来,挺直身子站在那儿;同样也有三个人起不了床。其中两个勉强爬起来,坐在床上,还有一个躺着不动,对进来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三个人都有病。英国人又同样讲了道,同样发给他们两本福音书。
从第三个牢房里传出来叫嚷声和吵闹声。典狱长敲敲门,叫道:“立正!”房门一打开,全体犯人也都挺直身子站在床边,除了几个病人和两个打架的人以外。那两个打架的人,满脸怒容,扭在一起,这个抓住那个的头发,那个揪住这个的胡子。直到看守跑到他们跟前,他们才松手。一个被打破鼻子,鼻子里直流鼻涕和血,他不住用外衣袖子擦着;另一个拉去被对方拔下的一根根胡子。
“班长!”典狱长恶狠狠地叫道。
一个身强力壮、相貌端正的人走了出来。
“怎么也管不住他们,长官,”班长眼睛里露出快乐的笑意,说。
“那就让我来对付他们,”典狱长皱着眉头说。
“他们为什么事打架?”①英国人问——
①原文是英语。
聂赫留朵夫就问班长,他们为什么事打架。
“为了一块包脚布,他错拿了别人的包脚布,”班长仍旧笑着说。“这个推了一下,那个就还了一拳。”
聂赫留朵夫告诉了英国人。
“我想对他们说几句话,”英国人对典狱长说。
聂赫留朵夫把这句话翻译过来。典狱长说:“行。”于是英国人就拿出他那本皮面精装的福音书来。
“麻烦您给我翻译一下,”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吵嘴,打架,可是为我们而死的基督,却给我们提出另一种办法来解决争端。您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按基督教义该怎样对待欺负我们的人?”
聂赫留朵夫把英国人的话和问题翻译了一遍。
“告诉长官,听凭长官发落,对吗?”有一个人斜睨看威严的典狱长,试探着说。
“揍他一顿,他就不会再欺负人了,”另一个说。
有几个人笑着表示赞成。聂赫留朵夫把他们的回答翻译给英国人听。
“请您告诉他们,按基督教义行事正好相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英国人一面说,一面做出把脸送给人家打的样子。
聂赫留朵夫作了翻译。
“最好让他自己尝一尝,”有人说。
“要是他两边都挨了揍,那还可以拿什么给人家打呢?”有个病人躺在床上说。
“那就让他把你打个稀巴烂。”
“嘿,那就来试一试吧,”后面有个人说,快乐地笑起来。整个牢房里爆发出一片难以控制的大笑。就连那个挨打的人也一面流血,吐痰,一面哈哈大笑。连几个病人也笑了。
英国人不动声色,要求聂赫留朵夫转告他们,有些事看来似乎办不到,但信徒能够办到,而且轻而易举。
“您问问他们喝不喝酒。”
“喝的,老爷,”一个人说,接着又是一片嗤鼻声和大笑声。
这个牢房里有四名病人。英国人问,为什么不把病人集中在一个牢房里。典狱长回答说,他们自己不愿意。这些病人害的都不是传染病,而且有一名医士照料他们,给他们治疗。
“他有一个多星期没露面了,”有人说。
典狱长没有理他,就把客人带到下一个牢房。又是打开房门,又是全体起床,肃静无声,又是英国人发福音书。在第五个牢房,第六个牢房,在过道右边,在过道左边,个个牢房里都是同样的景象。
他们从苦役犯的牢房走到流放犯的牢房,从流放犯的牢房走到村社判刑农民的牢房,再到自愿跟随犯人的家属房间。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到处都是受冻的人,挨饿的人,无所事事的人,染上疾病的人,受尽凌辱的人,丧失自由的人,就象畜生一样。
英国人发完一定数量的福音书,不再发了,甚至不再讲道了。难堪的景象,尤其是使人窒息的空气,显然耗尽了他的精力。他从这个牢房到那个牢房,听着典狱长对每个牢房的情况介绍,只是随口说一句:“行了。”①聂赫留朵夫象梦游一般踉踉跄跄地走着,感到精疲力竭,心灰意懒,但又没有勇气中途退出,离开这地方——
①原文是英语。
27 在流放犯牢房里遇见流浪的怪老头。怪老头的反政府言论。停尸室。克雷里卓夫的尸体。聂赫留朵夫由克雷里卓夫的死引起的感想
在流放犯的一个牢房里,聂赫留朵夫看见早晨在渡船上见到过的怪老头,不由得感到惊奇。这个老头儿,头发蓬乱,满脸皱纹,上身只穿一件肩头磨破的灰色脏衬衫,下身穿着同样破旧的长裤,赤脚坐在板床旁边的地板上,目光严厉而疑惑地瞧着进来的人。他那皮包骨头的身子从脏衬衫的破洞里露出来,显得虚弱可怜,但神色比在渡船上更加专注,更富有生气。犯人们也象别的牢房里那样,看见长官进来,都跳下床,挺直身子站着;可是老头儿却坐着不动。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双眉愤怒地皱起来。
“站起来!”典狱长对他喝道。
老头儿却一动不动,只是轻蔑地微微一笑。
“只有你的奴仆见到你才站起来。我可不是你的奴仆。瞧你头上还有烙印……”老头儿指着典狱长的前额说。
“什—么?”典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