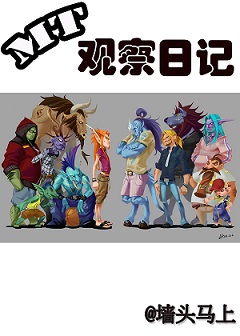冷眼观-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点名队里,一般标脸看仪扬。
呢!至于要问何处人口音好么?此话曾经乾隆你七下江南的辰光,以此询过金山长老。长老当时对乾隆爷说:“乡亲遇乡亲,说话真好听。”今日我听见宝应人说话,虽不过觉犯嫌,却也不甚好听。再证诸考棚里那副联语,决不会是扬州府八属以外九属人撰的。依我说,无论做甚么事,都要习惯但更为佳。那“习惯”二字,直是两情融洽的主动力。他若改过“乡亲遇乡亲,习惯就好听”,这就不错了!何能不问他怎么,只要是个同乡,就硬派他口音入耳呢?
我当下初上船时,自念应世以来,只有这一何一李是遇我恩礼备至的人,其余不是有恩无礼,就是有礼无恩,何以单拣他们这两个人,老天就替我一网打尽呢?此不住如痴如迷,万分懊恼。谁知被两个乡下妇人几句土白,竟把我各种烦闷解脱得十有八九。正要回身到炕上去歇息一回,不意猛听得岸上有人喊叫搭船,我就又坐下身。抬头一看,见是一位苍髯老者,身上背了一柄雨伞同一个小小包裹,脚下赤了一双足,穿着两只麻鞋,在岸上行步如飞的,一头喊着,一头走着。看他那种神理,好像是个走长路的人样儿。无奈本船上水手,都以为他们船是我独雇的,不敢招揽。后来我又忽见那老者指着天对船上喊道:“呔!那船上的人听者,天快要下雷暴了,还不趁早儿把篷下了傍岸,寻一个僻静地段躲一躲么?再停一刻,这只船使到湖心里去,那还了得吗?”原来这高邮甓社湖,又叫做邵伯湖,为淮汇荟之区,俗传下面有所龙窝,是个极容易坏船的所在。大凡吃水面上饭的,多有点害怕,其实是个活沙。当时我就随着那老者所指的地方朝天上一望,仰见一轮红日当空,微风不动,只有一朵形似柳条布式样的墨云,在日缠边轻轻浮过,很不像个要下雨的气候。不意我们船上的舵工也喊道:“伙计们,如今风转了,你们可看见那西北角上挂下雨脚了,我们快点改篷傍岸,仍摇到上河里去罢!”一时各水手,落篷的落篷,驾橹的驾橹。忙乱甫定,雨点子已是同倾盆似的落个不住。我再朝那老者一看,见他还兀自站在那边岸上。此时雷雨被风搅的越发大了。幸而是夏季里,还可招架;倘要换了个严冬落雪,岂不要把整个儿人旋下河去么?
我实在是越看越过意不去,就招呼船家替那老者接了包裹,请他到舱里来,权时躲避一刻。及见他走上船头,一面不慌不忙的卸去外面湿衣,一面就对着我打了一个稽首,口里说道:“老夫打搅了!”便傍近舱门坐下。那一种鹤发童颜,已自令人起敬;再加仓卒之中,竟能不改常度,我就猜着他不是个草野遗贤,定是个山林隐士。不觉站起身答道:“岂敢!岂敢!人到何处不相逢,而且彼此都在客边,就是坐一坐又是甚么要紧呢?但我却有一句话要想请教你:适才像那样的晴天,一轮旭日,万里无云,却非船家因见有雨脚挂下可比,何以你就知道要起雷暴,预先报告我们靠船呢?”那老者笑道:“此老夫平生小可之事耳!凡属天文、地理、兵民、财艺诸学,都有个老先生指教过的,并不是我平空杜撰。”我道:“你老先生的老先生又是谁呢?”那老学者即掀着白银条似的胡子笑道:“老夫的老先生,并非无名下士,就是那万古云霄一羽毛的诸葛亮!”
我听了,止不住大笑起来道:“人家说嘴上无毛,才做事不牢,怎你这么偌大的年纪,也是这样随嘴的打诳语呢?”那老者道:“你估量老夫哪句话是打的诳语?说出来我听,只要真不错,我虽非葛天氏的国民,却也不像别人不服善的。”我笑道:“这还有甚么说头?就算你年纪大,最多也不能过一百岁,那诸葛忠武是汉末的人,离现在已是数千余年了,其中还隔了个晋、魏、六朝、唐、宋、元、明,连本朝共是八代,哪里能够得上他授受的道理呢?”那老者听我回他这一句,他就正言令色的对我道:“我这个老先生,却是同你们从那孔夫子的一样。那孔夫子是战国时代的人,还要在汉末以上呢!难不成你足下也是亲承色笑,会见过他的么?所以从来会做人家学生的,并不用耳提面授,尽可以道统遥传。倘若是不会做人家学生的,即或朝夕琢磨,又属何用呢?”我不提防被他这一回驳,竟把我驳得想不出一句话来同他说。忽听那老者又道:“说起来也不值得甚么,不过老夫幼好兵事,曾得过一部武侯注解的《白猿经风雨占》,以之行军三日前推验三日后,疾风暴雨,百不失一。诸如适才所见日度分野,那几条黑云,他名字叫做『雨师倒海』是主实时有大雷雨的。老夫一时欲庇宇下,故不觉冲口而出,幸勿见笑。”我忙道:“彼此出外的人,正要一见如故才好,哪有会来见笑的道理呢?”说着,那风雨已是停止多时了。船家正自安排酒饭,我就叫他们多一双杯箸,移到船头上去,便请那老者一同坐食。
其时仰观空际,见湿云片片如画,当中推出半轮新月,照映得一线长淮,光明滉漾,正不减昔年与李氏弟兄在秦淮夜宴时风景。遂不觉令人追念筱轩中丞一生结果,竟顷刻万斛愁肠,又平空翻起。及至再去看那老者,也是紧族着两道剑眉,举杯叹道:“唉!风月依然,究竟江山何在呢?”我听了他虽是短短的说了十个字,即已逆料他胸中实有大不得已的事蕴藉于中。我就想拿话去试他一试,因对那老者道:“老先生,你早时可曾经做过甚么营业么?怎么我同你谈了许许多时,竟会忘记请问你高姓大名,贵乡可处呢?岂不要惹你怪我是个目空一切的荒唐人么?”谁知那老者见我问他这句话,便脸上陡然的添出一种愁惨气象,放下杯,拿眼睛对着我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会,重复叹道:“唉!足下莫非是问我名姓住址么?”我道:“正是!正是!”那老者又道:“老夫自入川以后,乡里姓氏不传久矣!足下如果欲为异日纪念,但乞足下呼老夫为四川客,老夫亦呼足下为东道人便了!若交友不以意气相重,龂龂然定欲通名道姓为崇,则不但惧异日为好事者蜚短流长,适足有累清德;亦且老夫年岁不伦,更恐转滋物议耳!今与足下约,彼此只可谈风月,慎勿再效乡间儿女,问里求名,备作嫁娶资也。”
我当时见那老者举止粗豪,已有几分疑惧;再加听他说了这么一大篇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闪烁话,我就格外疑心他是金钩吕胡子一流人物,不觉栗栗危惧起来,生怕言语间或不留心,犯了他们绿林中忌讳,闹出乱子来,岂不要讨船家笑话我是自寻苦吃么?当下就只得装着吃醉了酒的样子,伏在一块船板上假困,不意一时气静神全,竟会由假人真的沉沉睡去。
及至再等我醒来,已是满天凉露沾衣,晓星欲坠,船家正乘着早凉起身收拾赶路,那老者早不知于何时拿了包裹上岸。我就急忙回到舱里一看,幸尚大致无损,只有那老者一柄雨伞,尚倚在原处未动。我就想走过去举起来看,不意沉重得很,再莫想举他得动。看官,试去想一想看,这个又是怀着个甚么鬼胎呢?再者,古今只有烂柯长树,哪里会听过有雨伞生根的?原来他其中却有个道理在内。不然,世传韩淮阴手无缚鸡之力,若我连一柄雨伞都拿不动,岂不是连韩淮阴都不如,直要被人笑我手无缚鼠之力了么?须知言皆有意,事岂无因。要晓得那人的一柄雨伞,除却外面纸皮不算外,所有其余伞撑伞柄,皆系用汉铁铸成,是以一经到我们这文不像个秀才,武不像个兵的人手里拿起来,就格外显得异常沉重了。及我再一展玩,只见那伞柄上还…着“羽异王府制”五个小字,我才猛然如梦初醒的道:“哎哟!怎么我闹上一夜,还是同着这么一个魔王在一道鬼混呢?险些儿是不曾得罪了他,倘若是要惹起了他那魔性,只须举动这柄伞在我那脑袋上碰一碰,那时我还想有命么?怪不得他那一种桀傲不驯的样子,令我至今仍有点越想越害怕呢!岂不也算陪着三十年前的人,经过了一次红羊小劫么?可见李氏家集中,载曾文正平匪记略,奏报石逆在逃的密折上,有:
该匪自举事以来,时隔两朝,祸逾十载,计其中蹂躏一十八省,屠毒七百余城,皆由彼时民不知兵,所以人尽从匪。迨至…枪匝地,烽火弥天,始仰仗七庙威灵,两宫福庇,得以多年积匪,次第弭平。然而江南为中原财赋之区,经此兵燹之余,未免元所大伤,精华尽瘁矣。伪翼王石达开,旧本书生,人尤凶悍,闻其早年曾领乡荐,再试南宫,贼之狡谋,半出所授。当其城困之日,犹敢以同胞革命诸谬谈,与臣数四诗札往还,意在煽惑。迨知事不可为,敌复乘间窜逸川滇一带,为害殊深,似未便以穷寇勿追,稍羁显戮。应请旨敕下沿江沿海,及川滇各督抚将军,一体严拿,务获究办。臣遇见,意谓石逆一日不能就擒,则粤匪一日不能视为肃清,养痈成患,死灰难保无复燃之时;星火燎原,粉饰岂得谓升平之福哉。
云云那些话,不是言过其实呢!而且可知同胞革命诸谈,彼时已见奏报,不过曾文正公深谋远虑,不肯宣布出来,为后人作俑罢了!当时天已大亮,料他既已从容不迫的取了包裹下船,哪里有这柄防身的伙伴,不记得拿了去的道理呢?可想这都是他故意留下来,与人做个绝大纪念的了。”所以我就立意不再痴等,即刻就叫舟子扯起了满帆,一直望宝应进发。
此后便早行夜住,渴饮饥餐,一路上安抵舍下。见着我那妻子,彼此都谈了些别后话,我就忙问他道:“你就要想我回来,又何必写那种扯谎掉白的信去哄骗我呢?内中还怕我不相信,又狠命的砌上了一大篇子甚么被乩方吃坏了的鬼话,你须知我共你是夫妻情分,非同路人可比。若是有这番恩爱,就是不说得病,我也可以回来的。倘要恩断义绝,两不相干,你莫说是得病,即或说是病死,又有个甚么用处呢?再加你别的比譬,或者肚里没有听见过,难不成那列国上一段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你也未曾知道么?就不防我下一趟出门,倘或你真有起病来,写信把我,我倒把你当做仍像前番扯谎,竟不回来,那时你又怎么了呢?所以人家说,无论是夫妻,是朋友,那信实两个字都少不了。不然,又何以从前有势利出于家庭的那一句话呢?”
当下他被我一收拾,竟是哑口无言,只翻着两只又黄又大的白眼,煽了煽的望着我干笑。及至见我说急了,却又撇着嘴要哭,无奈把眼睛挤红了,竟连一点儿眼泪都没有挤得出,只是尽够伸着头,闭着眼,望我发怔。我看了他那种非痴非傻的神理,真是又要好气,又要好恼,怎么一个个只要他离父母过早,来不及受教育,就竟会变成这种样子的呢?罢!罢!罢!我也是同他会少离多,又何必认真计较呢?不如乖乖糊乖乖的,大家胡混一场罢了,当下就一向无话。
不觉在家里勉勉强强的又过了两个年头。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那年已是三十正岁。屈指从十九岁上往金陵数起,二十岁上随李筱帅赴皖南道任,二十一岁前往粤东,二十二岁又由翻东折回桑梓,即于本年冒险北上。那以后二十三、四、五、六、七、八,便都在沪江株守了。所以其中有话即长,无话即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