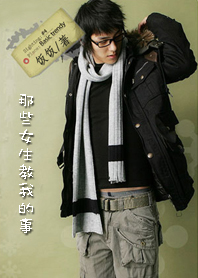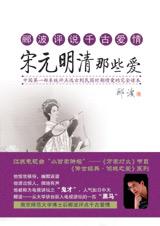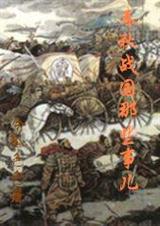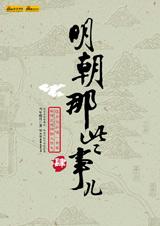明清文人那些事儿-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着远大前程的年轻人的身份,突然一下子就从一个堂堂七品正职,变成了荷冠道衣、优游林下的山人隐士。由于买的是前人的废园,加上处地略偏,当时虽然只用了大约三百两银子,但扩充它重建它的花费又何止十倍!如果你对这方面的细节有兴趣,不妨读一读他后来为此撰写的情文并茂的系列散文《随园六记》,就可发现这简直是个缜密而宏伟的人文规划下的产物。其中既有对中国历代园林精华的广采博取,又借鉴了从意大利传教士那里获取的文艺复兴后期西方建筑的某些样式,更有对自己家乡杭州的著名景物如西湖、断桥、南北峰、苏堤白堤等的移植与复制。如此的洋洋大观,规模气派,再加上园内书仓里庋藏的三十万卷图书,以及“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鹄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这样广告式的自我宣传(参见《随园遗嘱》里的有关自述),自然使它自建成之日起,很快就被目为清代园林艺术的惊世之作,无论达官贵人或平头百姓都以有机会一游为幸。好在这里的主人偏偏又是个喜欢热闹、满脑子开放思想的家伙,于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当时瓢饮簟食、皓首穷经的江南作家群中。“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一直弄到“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为止。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隐士,而是一位迪斯尼乐园,或中华锦绣风情园的业务经理。至于这么多的银子投下去,这钱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随园食事及其他(3)
随园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周边不设围墙,这无论在当初或今天都称得上是惊世骇俗。想想看,好几万身家的财产,全家男女老少奴仆僮婢数百人口的性命,就这么大大咧咧的如同现在城市里的广场或街心公园那样坦露着,甚至连夜不闭户也谈不上,因为根本就无户可闭。将安全的基础全都寄托在小偷可能有的怜悯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蒙贼哀怜而已”。山势逶迤、修筑困难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有人把这归结于主人的开明作风,但我总觉得事情可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他在创作上以“性情”二字号令天下,痛诋考据,反对格律,批判复古等偏激观点,也不能被简单认为是普通的文学思想之争。虽说这观点并非由他首创,不过拾了两百年前袁中郎、江进之他们的余唾,但相比当年公安派那些人一脸书生相,齿尖舌利,争了一辈子只得到个标新立异的虚名,他的玩法可高明多了,可以说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都知道,要在江湖上打天下,成为一代宗师,第一步就先得有自己的门派和一两手看家本事,另外还得有理论,如少林派的易筋经,武当的太极阴阳理论什么的。袁的成功在于他什么都懂,而且都有自己独到的招数。年轻时很早就打出性灵派的旗号,争取到一大批基层作者和文学青年的支持,再以一部理论集《随园诗话》将抢到的地盘加以巩固。更厉害的是,本来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到他手里居然就能变成物质,成为赚钱扒分的绝佳工具。恭维前辈、奖掖后进、收女弟子、编诗话、替人出书写序、和企业家打交道、说某高官的老母亲有天赋诗才,只要他生平愿意沾一沾手的事情,几乎找不出一样是白干的。是啊,谁让他是清代文坛赫赫有名的流派宗主、说话做事管用呢!可以比较负责任地说,性灵派这三个字为他一生带来的收益,应该不低于他全部家产的一半。而现在他居然就将它们这样大大咧咧摊在公众的眼睛鼻子底下,说没有更深的机心和用意在里面,恐怕谁都不敢相信。当然,以他的老谋深算,治安方面也肯定是在绝对有把握的情况下,才敢这样肆行无忌的,凭他跟当地一把手尹继善的交情,以及将市长县长当下人使唤的骄矝,谁敢去惹他啊!随园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没有出过一桩刑事案件,就是很好的说明。
一个在文坛上如项羽那样打算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家伙,这是我自十七岁读《小仓山房全集》以来所一直固有的印象。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这个人,生来就是习惯把自己看成孟子说的“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也”或杜甫“会当绝淩顶,一览众山小”的那一类人。尽管外表谦恭,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内心的自负与狂妄,文学史上找不出几个人来比。从文章里偶尔露出的峥嵘来看,像苏东坡和陆放翁那样的都不放在眼里,至于本朝的同行或前辈,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一代宗师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这就是他广为人非议的对清初两个最有才华的作家方苞和王渔洋的评价。在文学的国度里,他也许一直是隐隐以君王自许的吧?我总爱这样询问自己,而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因此占地数万平方米的随园在他个人的心目中,说不定就是颐和园或承德山庄的一个同义词罢了。包括这里据统计每年总数超过十万人的游客,春秋佳日从城内及四下郊县涌上山来那种热闹场面,扶老携幼、喜气洋洋、流连忘返,与其说这一切出于主人的好客与平易近人,不如理解成精神上的某种与民同乐更恰当一些吧!而如果用围墙圈起来,真的弄成像陶渊明的东篱严子陵桐君山上的钓台那样,那就完全与他当初辞职退下来的本意有悖了。我们不妨可以想象,在那些风和日丽的正午或黄昏,当他站在园中主楼冬暖夏凉室宽大明亮、四周饰有西洋玻璃的阳台上,在十二名侍妾和三十多位年貌如花的女弟子的簇拥下,手持天目山中出产的籐杖,眼戴外国进口的金质眼镜,手抚刚染过的齐达胸前的整整齐齐的长须,慈和,宽仁,居高临下地观赏下面这国泰民安的景象,这时候,想必他在内心,很有可能将自己错认是长安曲江春日的唐明皇或开封城里元宵赏灯的道君皇帝什么的。如果谁对这样的假设感到惊讶,或心存疑惑,那么园中主要景点柳谷正中高悬的那副对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至少可以为我们透露出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何况这对联还出自他的自撰。
随园食事及其他(4)
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随园在袁枚一生名山事业上起到的作用,可以比之于刘备的荆州、谢安的东山、毛泽东的遵义,或者他今天的杭州老乡黄巧灵的宋城景区,是那种典型的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发展速度上直线上升的杰出个案。虽说当时有不少人天真地从风雅、高尚、气节等精神角度来理解,包括我个人在内,最初的时候主观上也很想为他开脱,但很多资料还是表明,筑园退隐只是他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种策略与手段。这以后他对政治的兴趣非但没有半点减少,反而更为积极与热衷。这方面既有《小仓山房尺牍》中大量的与当时朝中权要的往来书信为证,也有他与江南官场位居要津者称兄道弟,长年厮混应酬的实际生活状况可供援引。至于那些下层官员把这里看成是为升职走门路、通关系的最佳平台和捷径,那就更不用说了。不管袁枚本人是否承认,他在随园这一个人生活舞台上扮演的,实际上一直是明代的陈眉公,王百谷那样的山中宰相角色。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乾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最初阶段的经营,这地方的基础建设和精神建设都已显得相当完善,并以它独特的魅力,开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大批的地方赴任官员无不来此讨教做官的诀窍,顺便进献一点儿礼物。而当朝大员外放路过南京也时常对这里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因为这样做既可满足自己附庸风雅的虚荣心,博取礼贤下士的美名,同时也指望能通过此间主人令人羡慕的庞大的社会政治关系网络,为自己今后的仕途前程与舆情打下更牢固的基础。即便彼此从一开始就知道是在相互利用,但和一个名闻天下的诗人打打交道,毕竟有利无害。要知道当时的政治空气中尽管也会时不时的刮上几次沙尘暴什么的,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学术繁荣、文化昌盛的清明时代。连皇帝一生都写了四万多首诗,你想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
他们一般都在距此一里外的红土桥下来,这一礼节在许多书里都有着详尽的记载。把随从、车马、眷属、仪仗等都留在下面,只带上书僮和礼品,轻车简从,步行上山,以示对主人的仰慕与敬重,这在当时几乎已成为一个惯例。尽管不可能有什么官府的明文规定,却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这样被沿袭了下来。说得夸张一点,这似乎又有几分百官上朝在午门外下马的架式了。其中一个人物甚至还是烧鸦片的大大有名的两广总督林则徐。林对随园的匆匆造访据考证已在袁枚死后多年,加上当时这里也早已显露出败像,但我们的总督大人却仍然坚持要循依旧例、并且任凭随从与袁氏后人怎么劝阻也不改初衷。这种隆重礼待与规格,肯定是当初担任七品江宁知县时期的袁枚所难以想象的。从这样的细节与角度,这也说明他对自己人生形象的重新设计与塑造是如何的成功!
当然,偶尔的例外也是有的。倨傲而矜持一一多半藏在谦卑的外表之下一一的子才先生与当时围绕在他身边、跟着他一起混的那帮人──同学、朋友、妻妾、兄弟春圃太守、女弟子、文坛帮闲、娈童歌妓──由于随园文化集团公司(一个玩笑)开办以后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在他们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的视线里,这里的山水林石、亭阁楼馆在某种程度上,也许真的被认为有几分混同于承德的避暑山庄了。哪怕不是在想象中或喝酒喝多了的时候。因此,当长达五十年的山庄外事接待工作中,偶然碰到过有一个五品学士因不懂这里的规矩,坐着轿子冒冒失失就这么一直抬到了山上,引起主人的不悦甚至差点当场开销,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除老袁本人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及此事不说,一个后代崇拜者在他编的那本跟后来李宗吾的《厚黑学》差不多可以媲美的《随园轶事》里,甚至还专门以《某学士》为题列了一个条目。里面公然宣称:“仕隐两不同途,先生退居小仓山,久已将官场习气,一概扫除,是以达官过访,亦必于十里外屏去驺从。某官排道上山,为先生所憎恶”。虽说这后人的马屁功夫实在不怎么样,这么大的官架子摆在那里,居然又有脸说“久已将官场习气,一概扫除“,但从这一事件可以得知,袁当时的权势与骄矜之气已发展到了何等的程度。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随园食事及其他(5)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不妨再举出一个例子来,也许同样能帮助我们加深对上述这一点的印象。这事还是发生在他刚辞职不久的时候。某一天──据袁自述──他从与江宁县同属南京府管辖的上元县衙门干事回来,半路上看见一个因赌钱被衙役押解着去县堂的年轻理发匠,因小伙子长得很帅,“嫣然少年,饶有姿媚”。一下子把这方面的爱好可以做郑桥板老师的袁吸引住了,当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