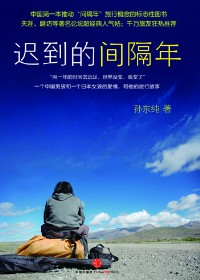素年不相迟-第35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身下,却丝毫不给她适应的时间,开始大幅度急骤运动起来。
每一下都像是凿在她心上。
他大起大落,每一次都送到了最深处。
没几下,素叶的双腿就开始打颤了。
最深处的疼痛很快就伴着熟悉的酸麻而来。
她的身体在冰火双重天上煎熬。
长发随着他的撞击晃荡着。
像是狂风暴雨中近乎连根拔起的芦苇,晃得七零八碎。
年柏彦的大手在她身上肆虐。
女人瓷白的身子布满了红痕。
他伸手拢起了她的长发,绕了一圈然后手一揪,素叶的头便被迫地朝后高高昂起,像是被人安装了马鞍的马,而年柏彦成了骑马的人。
落在她耳畔的是男人粗重低哑的嗓音,他的呼吸混合着木质的冷气一同注入了她的呼吸。
他咬牙切齿地在她耳边冷讽,“搔货,蒋斌进过这里吗?”
说话间,他刻意停了下来。
这是他第一次用这种羞辱的字眼来称呼她,每一次动情的时候,他都在她耳畔温柔厮磨,控制着自己的力道,却又因为晴欲难忍而张口咬住她的耳垂,叫她的名字,叫叶叶……
她不知道他的话是指什么,但这个称呼已足够令她想去死。
但当他说完后,她感觉他停了下来。
体内的滚烫顶着她最深的位置。
这下,她的脸更加惨白,紧跟着只觉得他像是对准了某一点似的再度狠狠地地顶进来。
那个口终于再次被他攻占,大家伙就这么长驱直入。
酸胀再次将素叶占据,又疼又渴望。
她知道他进的是哪里。
曾经他也要求过,他说他每次都要控制着不让自己完全没入,因为他担心她会吃不消。刚开始她不懂,他明明就是进入了还要求什么呢。
后来随着床事经验的加多,她才终于明白他的想法。那是最纵情的一次,她被他逗得不行,就迫不及待主动送上自己。
结果一下子全都冲了进来,她疼得头皮都要炸开了。年柏彦便笑着叫她妖精,然后将自己轻轻撤出了一些,告诉她,每一次要等到她完全适应的时候他才会逐渐加深,但从没真正撬开她最深处的大门。
素叶知道,他指的是子宫。
他要求过,哄劝她说会很舒服,更重要的是,他的子孙不用经过长途跋涉便能落地落地开花。她听着就害怕,摇头说不行。
可今天,她再次尝到了疼。
是那种跟他第一次打开她身体时钻心的疼。
拜你所赐
阳光很灿,像是天地万物都染上了金黄。
海鸥跃过海面时淋着耀眼的光亮,这些永远敢在海面上游飞的精灵们远比人类自由。
素叶从床上醒来时就隐隐听到了海鸥声,这些声音取代了闹钟唤她起床,然后她每一天都会在露台上站立一会儿,静静地数着海鸥经过的数量。
可今天,素叶没有到露台数海鸥。
她醒来时,觉得连眼皮睁开都耗尽了不少力气。
她还记得有一次去泰国玩,跟当地的朋友聊天时聊到了泰国的降头术,素叶没什么宗教信仰,也自然不会相信这些,但出于好奇倒是听听了,毕竟这种也是当地人文的表现形式。
那位朋友提到了其中一种降头术,什么名字她忘记了,只记得是有关复活,说是将断头者的头拼接回身体上,死者就可以复生。然后曾经有一个人,他的妻子跟三个闺蜜一同出游先时遇上了事故同时身亡,他想让死去的妻子复活,但他又迷恋于妻子三个闺蜜的身体,所以他就将他认为的女死者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共同组成了个身体,然后将妻子的头拼接上进行复活。
妻子复活了,可渐渐的察觉胳膊不是自己的胳膊,腿不是自己的腿,就连躯干都不是自己的,当她终于意识到她的胳膊、腿、躯干竟都是自己的三个好朋友的时彻底疯了。
素叶觉得,自己就是被年柏彦拼接过的人。
昨晚的年柏彦更多的像是一种发泄和惩罚。
她的身体近乎都被他捏碎。
她从来没见到过年柏彦这么残暴冷血的一面,一直以来,他都是冷静得令人痛恨,可昨晚他身体力行得让她知道他口中“活腻了”是什么意思。
四肢如脱离了身体,而昨晚,她的灵魂也伴随着他狂野的撞击而飞出了身体,现在的她,连下床时双腿都在打颤。
她全身都在痛。
嘴唇被他咬得痛。
脖子被他掐得痛。
双臂因为他如钳子般的大手的紧箍,骨关节都跟着咯吱咯吱的痛。
尤其是她的胸部。
上面有他的吻痕和大手肆意造成的抓痕。
娇嫩的乳尖被他咬得轻轻一碰也痛。
而她的下半身也不再是属于她自己的。
双腿像是随时都能从胯关节脱离似的,连站立都需要紧紧扶着墙壁。
她的四处也如被烙铁烙过似的,火辣辣地痛。
她忘了昨天晚上她痛得流了多少眼泪,却还记得当他在她身上肆虐时她尖叫、她痛苦地申银,终于连嗓子都哑了。
所以素叶在第二天早上醒来才觉得,年柏彦一定是将她大卸八块了,然后再拼接了上,否则她为什么会觉得全身的每一处地方都不听使唤地疼?
素叶终于熬不住饿的时候已是下午了。
她扶着墙,吃力地走出卧室时始终没见陈姐的身影,还有这个时间在岛上的清洁人员。
别墅里很安静。
静的似乎没有一丝人气。
却布置得十分耀眼。
灿若星子的彩灯早就盘上了庭院,连客厅都充满了中国红的颜色,每一个角落也匿藏着隐隐的光亮,像是从银河上撒落下来的星般璀璨。
十分热闹。
却是指环境。
偌大的别墅诡异极了。
至少素叶这么认为。
她没看见任何人的身影。
如陈姐的。
像这个时间,陈姐早就应该到卧室叫她吃饭了;
又如厨师。
像这个时间,厨师也早就候在餐厅里等着她是否满意的回答;
再如医生。
像这个时间,医生总会来一趟来为她做例行检查。
素叶一直很排斥检查,也讨厌医生,因为她觉得年柏彦做这么多无非就是想要,在保证她身体允许的状况下不停地折磨她,让她生不如死。
可今天,那个令她讨厌的医生也不在。
这个别墅的人本来就少,现如今,素叶突然觉得怎么就剩她一个了?
就连昨晚上像个魔鬼似的差点要她命的年柏彦也不见了。
素叶一时间急急下了楼。
却因为身体的不适,疼痛袭来,她的双腿一软,脚踩空,紧跟着从还有几级台阶的地方摔下来。
她痛呼。
膝盖磕在冰冷的黑色大理石地面上,生疼。
幸好不是从最高空滚下来,否则她必然残疾不可。
她的双臂也贴在地面上,光洁的地面倒影出她苍白的脸。
她的长发凌乱了,遮住了她的眸。
她觉得,自己从没这么狼狈过。
正试着搀着楼梯扶手起来时,男人的脚步声就踩了过来。
紧跟着,是男人的脚和修长的腿。
她吃力抬头。
对上年柏彦那双明暗不定的眸。
他站在那儿,没立刻伸手扶她,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如高傲的君王,在静静看着她如何像小丑似的狼狈。
素叶知道,他就是想要看着她低头,看着她像是个奴隶似的一步步爬到他跟前,跟他认错,跟他忏悔自己是多么的无耻卑鄙。
可是,她的无耻卑鄙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那颗卑微的不能再卑微的自尊心。
而他呢?
他卑鄙到跟她演了那么一场情真意切的戏,卑鄙到恼羞成怒将她囚困在这儿,甚至他卑鄙到令全岛的人都认定她是个神经病患者。
说到底,究竟谁才更卑鄙?
素叶不再看他。
她聪明地选择了无声无息地避开他目光的巡视,为的就是少吃点苦头。
如果再跟他的目光对下去的话,她非得痛恨得对着他破口大骂不可。
可是,对她施加暴行的男人,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只要将他激怒,他可以随时随地令她痛不欲生。
素叶还没傻到自残。
她不会求着他帮忙,也不会奢望他伸手搀扶。
如果说他是她避不开的灾难,那么,她尽量做到视而不见总行吧?
可下一秒,素叶觉得自己像是只小鸡似的被他一下子揪了起来,疼得她直皱眉头,咬住了下唇。
年柏彦低眼,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她的领口。
因为身高的关系,她胸前饱胀的风景也顺势被他尽收眼底。
是深浅不一的痕迹,青一块紫一块,有抓痕,有咬痕,还有吻痕……
年柏彦的眼底颜色浓烈了一层,他看着素叶,她全身无力得像是只兔子,仔细感受下来又会轻易察觉出她全身的颤抖。
细细小小的颤抖,应该是不受控制的。
漆黑长发显得有点凌乱,有一缕还钻进了她的胸口,与她瓷白得却布满爱痕的肌肤相配,黑的更黑,白的更白。
年柏彦性感的喉结上下滑动一下,他微微眯眼,这样一个素叶,一个虚弱得只能贴着他的素叶,倒是令他更有一种想去狠狠蹂躏的冲动。
这样的女人,注定是令男人神魂颠倒的女人。
深爱时恨不得与她夜夜缠绵,就好像是他要拼尽了全力、拿自己的全部来宠爱她都觉得不够的女人。
而痛恨时他还是沉浸在她的体香和紧致的身体上,他厌恶自己的用心良苦,厌恶曾经的付出,可每每见到她,又不受控制地吸引。
年柏彦从未接触过真正的爱情,从未掏心掏窝地去想要疼爱一个女人,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某一天,某一夜遇上了素叶,遇上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女人。
都说真正的深爱是成全是放手。
也许,他不是深爱,因为他的爱已经掺杂了恨,所以,他不能放她走,就算下地狱,他也会拉着她一同陪葬。
素叶被他揪得生疼,胳膊都快被他捏断了。
抬头,忍着疼说了句,“年柏彦,你真想让我死,也得让我吃饱了再死。”
对食物的渴望是人的天性,更何况她现在真的饿得饥肠辘辘了。
她没有辟谷者的毅力,在喝水不吃饭都能从容生活。
年柏彦倒是放开了她。
素叶转身,缓步到了餐厅。
餐厅里依旧没有陈姐的身影,也不见厨师。
餐桌上却早就美食当道。
有些是她经常吃的,有些是她最爱吃的,还有些是她叫不上名字的。
菜品以中国菜为主,其中又以宫廷菜为主打。
虽说从摆盘上没有餐厅那么专业,但从菜品的嗅觉和视觉上看定是绝佳。
冰桶里是年份罕见的红酒,而点缀在黑色桌旗之上的竟是一朵朵绽放的紫色睡莲,每一朵盛开的花瓣都一模一样,神秘的紫配合沉稳低调的黑色,看上去是惊心动魄的美。
素叶愕然,站在餐桌前发愣。
身后,是年柏彦的脚步声。
他靠近了她,大手顺势从身后搂住了她。
素叶的心跟着身子同时一颤,全身僵硬了。
年柏彦低下头,薄唇轻轻压在了她的额角,深深呼吸了她的发香,嗓音低沉磁性,撩动人心。
“有时候我会在想我和你要度过怎样的春节,素叶,拜你所赐,今年的春节还真是让我难忘。”
春节?
素叶的大脑一片空白。
怎么今天就是春节了吗?
正想着,腰间的大手抽离了,紧跟着是男人平静如水的声音,“吃饭吧。”
他翻脸像翻书,冷淡得跟刚刚大相径庭。
素叶一个激灵,这才发觉他在说话时的眼神始终未曾温暖过,他的眼染上了寒霜,就那么,在她对面坐下来,再看向她时,目光威严得令人不敢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