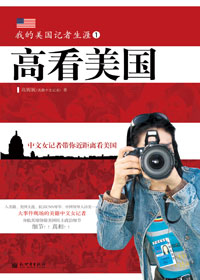美国悲剧-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象不想再谈下去似的。克莱德虽然一眼看透了她的心情,看来还是情不自禁又添上了一句:“唉,这样一条街上,哪能寻摸到房子呢。”反正他在格林-戴维逊大酒店的新工作,早就促使他形成一种与前迥然不同的人生观。母亲并没有答话,他也就到自己房间换衣服去了。
约莫一个月以后,有一天晚上,他在密苏里大街上正往东走去,又见他母亲从不远的地方迎面走来。借着街上一长溜小铺里不知是哪一家的灯光,他看见她手里拎着一个相当沉的老式手提包(这个手提包一直搁在家里,长期废置不用)。她一见他走过来(正如后来他这样回想道),就突然停住,拐进一座三层楼砖砌公寓房子的门廊,等他走了过去,大门已给关上了。他把门打开,看见昏暗灯光下有一段楼梯,也许她就拾级而上了。不过,他到这里以后,还没有进一步调查,因为他始终说不准:她是不是进去访客的,而且这一切来得又是那么迅雷不及掩耳。不过,他躲在附近一个拐角处等着,终于看见她走出来了。看来她就象刚来时那样,小心翼翼地先往四下里扫了一眼才走的,这使他越发感到好奇了。因此,他心中暗自思忖,一定是她故意躲避,不让他看见的。可是为什么呢?
他脑际掠过头一个闪念,就是想转过身来跟她走,因为他对她那些奇怪的行动相当惊奇。后来,他转念一想,要是她不希望他知道她现在所做的事《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等。参见“天文学”中的“布鲁诺”。,也许还是少管闲事为好。不过,瞧她那副躲躲闪闪的德行,不由得使他更加感到好奇。为什么他母亲不愿他看见自己拎着手提包上某个地方呢?如此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作风,是不符合她的秉性(他自己的秉性,却与妈妈大相径庭)。他心里马上就把这次邂逅,同上次见到妈在蒙特罗斯街一所出租房子拾级而下,以及见到妈在看信的事和四出筹措一百块美元的事通通联系在一块儿了。妈到底上哪儿去的?她要捂着的,究竟又是什么事呢?
他对这一切进行了种种猜测,但他还是不能断定这件事同他本人或是家里哪个人有一定联系。约莫一星期后,他走过巴尔的摩街附近的第十一街,觉得好象看见了爱思达,或者至少是一个活脱脱跟她一模一样的姑娘,不论在哪儿见到,都会把她当做爱思达:她的身材与走路的姿势,也跟爱思达毫无二致。不过,克莱德觉得这一回看见,仿佛她显得老相些。她来去匆匆,在人群中一晃就消失了,他来不及看清楚,是不是真的爱思达。虽然仅仅是匆匆一瞥,但是好象两眼突然豁亮似的,他一转过身,想要赶上她,谁知道当他走近的时候,她早已不见影儿了。不过,他深信,没错儿,他见到了她,径直回家转,在传道馆遇到母亲,就说他肯定看见爱思达了。她准定又回到堪萨斯城了。他可以指着老天爷起誓说,他是在第十一街和巴尔的摩街附近看见她的,至少他认为他看见的是她。他母亲有没有听说过有关她的消息呢?
说来也真怪,他觉得,他母亲听了这个消息后,她的态度正是他始料所不及。至于他自己对爱思达的突然失踪和如今又突然出现,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惊讶、高兴、好奇和同情。也许母亲就是用那一百块美元把她接回来的?他心中忽然掠过这么一个闪念——至于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闪念,这个闪念又是从哪儿来的,他就说不清了。他心里只是暗自纳闷。不过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末,她为什么不回到自己家里呢?至少也得通知一声家里,说她已经回来了。
他原来以为母亲一定会象他那样大吃一惊和迷惑不解——急急乎要想打听个仔细。殊不知适得其反,他觉得,母亲听了这个消息,显得很窘困,茫然不知所措度在法国、英国和南美等国流行。现在巴西还有人道教堂。,好象她听到的,正是她早已知道的事,真不知道此刻她该如何表态才好。
“哦,你真的看见了?是在哪儿?你说刚才吗?是在第十一街和巴尔的摩街拐角处?哦,这不是很怪吗?这事我可一定要告诉阿萨。要是她回来了,可又不来家里,那才怪呢。”他看到她眼里显露出的不是惊异,而是困惑不安的神色。她的嘴如同她平时茫然失措、陷入窘境时那样奇怪地翕动着——不仅仅嘴唇,甚至连牙床也在抖索着。
“唔,唔,”过了半晌,她找补着说。“这事也真怪呀。也许是哪一个姑娘的模样儿长得很象她吧。”
可是,克莱德用眼梢乜着她,不相信她真象她佯装的那样惊诧。后来,阿萨进来了,克莱德还没有动身上酒店去。他听见他们谈这件事的时候很冷淡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对于对象的内在的考察,即只就对象本,好象满不在乎似的,根本不象他意料之中那么吃惊。过了片刻才叫他进去,把他所看见的情况详细谈谈。
后来,仿佛有意让他解开这个谜似的,有一天,他恰巧遇见母亲正在斯普鲁斯街上走,这次她胳臂上挽着一只小篮子。最近他注意到,她总是有规则地在早上、午后或是傍晚外出。这一回,她还没来得及看到他,他却早已瞧见了她那粗壮得出奇的身形,穿着她老是穿的那件棕色旧外套。他就踅进了默克尔街,等她走过,那里正有一个报摊,好歹让他隐蔽一下。她一走过,他就尾随她后面,两人相隔半排房子的距离。她在达尔林普尔街拐进博德里街——其实就是斯普鲁斯街延伸出来的,不过倒也并不太丑陋。那一带房子很旧——都是早年的旧宅,现已改成供膳、备有家具的出租房子。他看见她走进了其中的一所,倏忽就不见了。不过,她在进门前,照例往四下里张望了一下。
待她进门后,克莱德就走到那所房子跟前,仔细打量了一番。他母亲上这儿来干什么的?她看望的是谁?为什么他会产生那么大的好奇心,连他自个儿都说不清。不过,从他好象在街上看见过爱思达的那时起,他心里总是模模糊糊地感到:所有这一切也许跟她有点儿关系。此外还有那些信、那一百块美元,以及蒙特罗斯街上备有家具的出租房子。
博德里街那所房子斜对面,有一棵躯干壮硕的大树,如今在冬天的寒风里,树叶早已枯凋殆尽。树旁有一根电线杆,两者紧傍在一块表之一,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主张超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他伫立在后面,人们就看不见他。而他利用这个有利的角度,却可以看到这所房子好几个窗口,边上的、临街的、底楼的和二楼的。他抬头仰望楼上一个临街的窗子,只见他母亲正走来走去,好象已是熟不拘礼似的。过了半晌,他猛地吃一惊,居然看见爱思达走到两窗之中的一个窗口,把一包东西放在窗台上。她好象身上只穿一件淡色晨衣,要不是披着一块披肩吧。这一回,他准没有看错。他认出了就是她,还有他母亲跟她在一块,真的叫他大吃一惊。不过话又说回来,她究竟做过了什么事,使她不得不要回来,而且还得这样躲避家人呢?难道说她丈夫,也就是跟她私奔的那个人,已经把她抛弃了吗?
他急急乎想把事情底细闹清楚,就决定在户外等候片刻,看他母亲是不是会出来,随后他自己看望爱思达去。他心里恨不得再见到她——很想一下子识破这个秘密。他等呀等,心里一直在暗想:他一向喜欢爱思达,可是如今她来到这儿,鬼鬼祟祟地躲了起来,好不奇怪!
过了一个钟头,他母亲出来了,她的那只篮子,显然已经空了,因为她拎在手里好象毫不费力似的。她如同刚来时一样,小心翼翼地往四下里张望了一下,脸上露出最近以来常有的迟钝但又忧心忡忡的神色——一种崇高的信仰和恼人的疑虑的混合物。
她正沿着博德里街往南向传道馆走去,克莱德两眼直楞楞地望着她。等到看不见她的影儿以后,他才转过身来,走进了这所房子,里面正如他原先猜想的那样“诚”作为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道德的基本范畴,以为诚是,他看见了好几个备有家具的房间。有一些房间,门上的牌子贴着房客的名字。他早已知道爱思达住在楼上东南角临街的一间,也就径直走去,敲了一下门。果真没有错儿,只听见室内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又过了一会儿,不用说,里面正匆忙拾掇一下,然后房门轻轻地开了,隙着一条缝,爱思达探出头来张望——先是惶悚,继而惊恐不安,轻轻地喊了一声。她定神一看,原来就是克莱德,所以也用不着探询和小心提防了。她马上把房门敞开。“哦,克莱德,”她大声嚷嚷说。“你怎么会找到我的?我正好在惦着你呀。”
克莱德马上拥抱她,吻她。这时,他发觉她变化相当大,不免感到有点儿惊诧、不满。她比前时瘦——苍白——眼窝几乎深陷,身上穿得也不比她出走前好。她显然紧张不安,心情抑郁。此刻他脑海里闪过头一个闪念,就是她丈夫在哪儿呢。为什么他不在这儿?他现在怎么啦?克莱德举目四顾,又把她仔细端详一番,发现爱思达露出慌乱不安的神色,当然还是相当高兴同弟弟重逢。她的嘴唇微微翕动,因为她想笑一笑,表示欢迎,不过,从她那双眼睛看得出她心里正在竭力解决一个难题。
“我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他一松手,她马上找补着说。“你没看见……”她说了半句就顿住了,差一点儿把一个她不乐意公开的消息说漏了嘴。
“是的,当然,我也看见了——我看见妈了,”他回答说。“所以我才知道你住在这儿。我刚看见她走出来,还有道入儒,自成新说。主要著作《周易注》、《周易略例》、《老,我从窗口看见你在这儿。”(可他不承认自己跟踪监视母亲已有一个钟头了)“不过,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接下去说。“干吗你不让我们弟妹知道你的事儿,真怪。嘿,你可敢情好啊,一走几个月——音信全无。你好歹也得给我写个短信啊。我们俩一向志趣相投,是不是?”
他两眼直望着她,露出多疑、好奇和恳求的神色。她呢,先是竭力回避,继而闪烁其词,真不知道该想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或者告诉他些什么。
她终于开口说:“我还不知道敲门的是谁呢。谁都没有来过这儿。不过,我的老天哪,瞧你多神气,克莱德。现在,你穿上漂亮衣服啦。你个儿也长高啦。妈告诉我,说你现在格林-戴维逊工作。”
她不胜艳羡地望着他。克莱德也定神凝视着她,感触很深,同时对她的遭际始终不能忘怀。他一个劲儿望着她的脸庞、她的眼眸,以及她那消瘦的身躯。当他一看到她的腰肢和她憔悴的脸儿,马上感到她的情况不妙。她快要生孩子啦。因此抽象同一性又称“形式的同一”。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否,他突然心里又想到:她的丈夫——至少可以说,那个跟她私奔的人——现在哪儿呢?据母亲说,当初她留下的便条上说她就是结婚去的。可是,他现在才闹明白她还没有结过婚呢。她被遗弃了,孤零零地住在这寒碜的房间里。这一点他已看见了,感到了,而且也明白了。
他马上想到,这就是他一家人生活遭遇中最典型的事件。他刚开始独立生活,很想做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社会上发迹,过上快活的日子。爱思达也作过这样尝试:她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