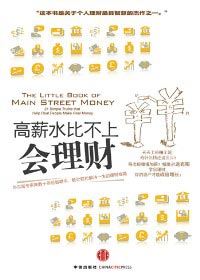杨柳不如春朝绿-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天,我和父亲一起去了房屋中介,递交了房屋买卖申请。
回家的路上,他一语不发,卖掉环城北路的房子对我们来说是继母亲生病后第二道晴天霹雳,虽然房子卖掉后母亲的治疗费用有了很大的保障,但是我们却失去了为我们遮风挡雨、已经和我们的生命融为一体的精神支柱。
进屋后,父亲开始收拾东西了,一副准备随时搬走的态度。
很快的,我们接到了买主的电话。
“卖掉之后我们只能去住分给妈妈的小房子了吧。”我手握着筷子在碗里来回搅拌着,却一点感觉不到饿,只能一两个饭粒往嘴里送。
味如嚼蜡。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母亲的病治好,其他的都不是事情。”
虽然我和父亲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相同的,舍不得这房子的心情也没有异样。
家里的电话响了,他放下碗去接电话。看他的表情好像在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但是他却没有和我说,放下电话后在他的脸上出现了少有的兴奋表情。
回到饭桌前,他眼神矍铄的看着我:“太好了!”
(谈判)
下午根据约好的时间,我们等到了如约而来的买房者。
当时他们却提前来了一个小时。
来看房的是一对中年夫妻,听到敲门声后我走过去开门,但还没有开门的那一刻,透过门缝隙里传进来的浓厚香水味让我不禁出现眩晕的症状,双手扶着门把手后我深呼了一口气,而门开了之后更加验证了我的嗅觉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扑面而来的气味几乎快让我当场晕厥。
中年男子西装革履,看样子文质彬彬,我初步判断身价最起码在五百万左右,进门后他们绕过我直接走到父亲的面前,男子从怀里掏出精致的名片盒,从里面取出一张名片递到我父亲面前:“杨先生是吧?你好,本来和中介约好一起来看房的,但是没有中介的话,我想对于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父亲是不动这些的,只能愣愣的点点头,低头看了一眼名片上的名称:云天传媒公司总经理顾昀,走到父亲身旁后我也看到了上面写的文字,不禁大吃一惊。
但随即对我自己的眼光有了充分的肯定。
进屋后的交谈中顾昀从头到尾都压制着父亲,我在一旁看着却插不上嘴,本来我们在中介那里估的价格是83万,但是他们报给顾昀的价格是87万。
“我看这样吧,我直接向你买,手续部分的问题我可以全程办妥。”
顾昀从烟盒里取出了两根烟,分别递到我和我父亲面前,我们纷纷摇头表示自己不会抽烟,他便将一根烟递到唇边,取出看似很高档的打火机点燃了唇上的香烟。
浓烈的呛人气味让我和父亲很难适应,他侧脸咳嗽了两声小声问着:“你出多少?”
“85万。”顾昀吸了一口烟蒂,然后吐出大量的气体:“怎么样?这个价格很不错吧?”
最终父亲同意了,随即顾昀示意了一眼身旁的中年妇女,她从手中名牌包里掏出手机拨了一通号码放在耳边,不一会儿电话就接通了:“你好,是房屋中介吧?我和我老公商量了一下,现决定不买了,所以今天就不来看房了。”
话音刚落,房屋中介的销售员原本还想问清原因打算再争取一下,可是却被她无情的挂断了,随即她摘下了鼻梁上的太阳眼镜用那稍微高亢的声调对我父亲说: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午就去办手续吧。”
就这样,我们告别了我父亲一手建立的巢穴,搬到了耿桥新村。
(转机)
把环城北路房子卖掉的事情,我们没有和杨思提过。
事实上我原本是打算告诉她的,但是杨思在学校是没有手机的,为了这件事我也不可能专程打个电话到学校或者二叔家。即使她有手机,我也不知道号码。
父亲告诉我母亲的病有了转机,这瞬间让我明白了那天他接完电话后的那种惊喜之色是从何而来的。也就是因为这个消息,让父亲更加确定了卖掉房子的决心。
在病房里我们三个吃完了饭,父亲起身想要拿着碗筷去刷,我压着他的肩膀站了起来:
“我去吧。”
也许是听到了好久没有入耳的好消息,卖房在我心中所产生的阴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在医院后面的水池边,我看到秋萦。这段时间,我第一次笑得很开心。
“看你的心情很不错哟。”她扬起眉毛同样甜甜地笑着:“我有幸能分享吗?”
我把碗筷放在水池里,习惯性的从她旁边拿过洗洁精挤出一点在碗里,脑袋里运转着应该怎么和她说这个好消息才会让这个“好”字凸出的最明显,正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秋萦一把抢过我手中的洗洁精微微瞪着银铃般的明目:
“没事吧你?挤这么多干什么?”
低头一看才发现,我的碗里已经有了半碗容量的洗洁精了。
然而秋萦的话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开心,但是从她的表情看得出她也在替我感到高兴:“好久没看到你这么释怀的笑容了。”
“哪有。。。”我拧开水龙头,流水哗啦啦的冲刷着碗里的洗洁精,我拿着洗碗布在一个个在盛着很多洗洁精的大碗里洗着,不知不觉泡沫越来越多,溢满了大半个水池。
“对了,上次你借我的复习材料我还没有还给你。”
最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最起码好几次想起来要把那本应付高考很重要的复习材料交给她,然而每次出门的时候都将它遗忘在我的床头柜上。
想起来的时候都忍不住敲了敲自己的脑门。
秋萦却不是很在意这件事,双手灵活的洗着面前池子里的碗筷,侧着笑脸看了看我后又低下头去:“没关系,里面的内容都是我整理出来的。”她伸直了纤细的食指对着太阳穴指了指:“原稿在这里。”
同样是大脑,我和她的差距却是这么大,我不由自主的摸了摸额头,对我们之间的距离只能是咂嘴兴叹了。
不知为什么,秋萦突然扭过脸目不转睛、直勾勾的看着我,看的我关在心脏里的小鹿突然间急剧不安分起来。慢慢的,秋萦伸出手触摸着我的额头。
这一刻,洗碗布在我手里捏着,不断有水从我的指缝间流淌下来。
她将手放了下来摊在我眼前笑着:“你刚刚把泡沫弄到额头上了。”
(焦急)
赌梭哈的时候千万要记住,在双方最后一张底牌掀开之前不要因为面前的牌面有任何喜忧之情,因为就在你认为你赢或输的的概率是百分十九十九而不在意那区区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时,恰恰就是那渺小的半分之一。
足以有一百八十度扭转你面部表情的力量。
我清清楚楚记得这一天是星期四,阳光不怎么亮。
父亲早早的就拿着准备好的手术费去医院付钱,而我在学校里虽然上了一天的课,表面看起来和平常人没有任何的异样,内心却难以压抑翻腾的激动之情。
再过几天,母亲即将回到我们的家了,不仅是她,连我们也会一起告别这个该死的医院。
下午最后一节课,物理老师讲的什么我根本就听不进去,我只顾时不时盯着黑板上挂着的钟,数着一圈又一圈。我敢说,这是我生平最不专心的一堂课。
终于,秒针到了我期盼已久的位置。然而事实上早在五分钟前我就已经收好了我桌面上的所有东西,等待着铃声到来拔脚冲出门的那一刻。
铃声响了,我刷的一下站了起来,讲台前的老师没有对我的行为有所反映,手中的讲义瞬间飘落到地上。这时所有人的的眼光都聚焦到我身上,包括被我这突然的举动惊呆的老师。
望着其他人桌面堆积像碉堡一样的书堆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太傻了,忘记了自己是准备高考的高三学生,像我们这样的人,教室拖堂早已是家常便饭了。
环顾四周后我注意到老师不怒而威的高压眼神,慢慢区下自己的膝盖,坐会原位。
物理老师弯腰拾起地上的讲义放在讲桌上看了看我们,缓缓开口:“接下来。。。”
我明白了:看样子她是不准备放我们回去吃晚饭了,心灰意冷的我将手伸进桌肚里摸处物理的课本和相关材料放到桌上,课代表似乎也有意识,准备起身去开教室的灯了。
“下课。。。”
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物理老师说完后放下了手中的粉笔拍了拍手,随即开始收拾讲桌上的材料。直到教室里开始出现收拾书本、小声说话的喧闹声,才确定自己没有幻听。
同桌用肘部顶了顶我:“杨冶,你挺有种的嘛,居然用这种方式抗议拖堂。”
哪里有空去理他,我将书本放回桌肚后直接从窗户上调到走廊,直奔医院。
至于教室里的同学看到我的行为后有些什么评论,我已经顾不上了。
(打击)
寒冬的夜晚总是来临的很早。
我在路上带着小跑奔着医院的方向而去。可能是因为奔跑产生的热量缘故,在西北风呼啸中穿行的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寒意在肆意折磨着我已经冻红的耳朵。
暗淡的路灯折射着我不断拉长和缩短的影子。
在医院走廊旁的长凳上,我发现了父亲无声无息的垂着头坐在那里。
“爸。。。”我喘着气站在原地看他脚边放着他出门时握着的袋子,从袋子的饱满度来看里面的钱应该还在里面,这令我非常诧异,走之前他说这钱是给母亲做手术用的。
听到我叫他后,他缓缓抬起头满眼绝望的看着我。这样的眼光冻结了我原本发热的身体毛孔,直觉告诉我:他的表情能够透露给我的信息绝不是好消息。
拖着沉重的步伐,我坐到了他的旁边,侧脸看着从袋口处依稀能够瞥见的一沓沓红色成捆钞票。钱没有送出去,等于直觉告诉我手术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变数。
就这样我们坐了很久,我始终不敢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惧怕着,恐惧着。
双手相互用力搓着,不知不觉已经搓到了很烫的地步了,然而我依旧重复着这个动作,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可以舒缓自己紧张的情绪。
尽管即使这样做也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
“心脏。。。”过了好久,父亲终于开口了,听到他的声音后我连忙将耳朵侧了过去,生怕自己听错了任何一个字,而因此弄错了自己的判断。
低沉的声音好像是喉咙处吊了几百斤重的哑铃阻止他的声带说出那个击溃了我的话语:
“心脏没有了。。。”
终于,早已潮湿的双手停止了揉搓。短时间内我的灵魂仿佛被抽空一般,耳朵里甚至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忙音,我无力的靠在了椅背上。
可就算如此,身受沉重打击的我还没有放弃希望,伸手握着父亲的手臂无力的晃了晃:“没关系,还可以等下一个适合的心脏,全国这么大,总有办法可想的。”
话是这么说,可是从我本人口中说出的话连我自己都不抱有希望。
父亲没有回答我,晃他手臂的力气慢慢加大了一点。这时我注意到父亲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张白色纸张,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经由我刚才的举动从他的手中滑落到地上,安静的躺在冰冷的地板砖上。
没有发生任何的声音。
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去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