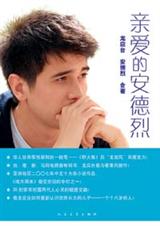亲爱的爱情(重生演艺圈)-第6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闭嘴!”这是傅君颜对副导唯一的回答,他的语调特别冷,清淡而严厉,手上的动作没有停,嘴里却慢条斯理的对我说:“宝贝,不要害怕,我们能出去。现在去对副导笑一笑,告诉他不要紧张。然后把你的另一只高跟鞋给他,让他和我一样敲窗子的四个角,坚持一下,车窗一定能破。相信我,只要流沙不淹没车窗,我们就能爬出去。”
我点点头,小心翼翼的把身子探上前座,试探的推了推颤抖的副导,照着傅君颜的话安抚的朝他笑。可副导却没有理会我,也没有接我递给他的高跟鞋,而是开始发呆,并且非常诡异的,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剧烈的咳嗽。
我有些害怕,但还是努力笑着试探着说:“副导,你振作一点好不好?不要这个样子……”
傅君颜听了我的话也侧过头,语重心长的说:“副导,天助自助者,像你当年一样,一心想着走出去就能出去。”说着,手中依旧有序的一次次敲击着车窗玻璃的四角。副导听了,却突然直直的望着傅君颜,完全安静了下来。他突兀的摇摇头,缓缓的坐直身子,回首空茫的再看了我们一眼,就趴在方向盘上,不动了。我眼皮一跳,知道,这是放弃的姿态……
我又轻喊了一声:“副导?”副导却只是趴着,一动不动。
转过脸,傅君颜挺直着背挡在我面前,他没有一丝动摇,敲击车窗的动作连贯而沉稳,这里的空气因为车的下沉和沙尘的溢进而变得越发稀薄,傅君颜嘴里却不慌不乱的提醒我:“宝贝,感觉头晕的时候自己掐人中,坚持一下,马上就能出去了。”我的脑袋渐渐也有些发沉,这时所有的声音都变得无比清晰,甚至刺痛耳膜。终于,就在近乎绝望的边缘,哗的一声玻璃粉碎成无数个小块,许多流沙也顺势滑了进来,车子下沉的速度明显的更快了。
傅君颜见玻璃碎开了,就转过身急忙把我往前一让,他说:“宝贝,快往外爬。”然后用力把我往车窗外面推,这时可以活动的空间已经非常小,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让我脱掉棉袄。而他的力道太大,掐的我手脚生疼。不停有沙灌进我的嘴里,我被呛到咳嗽,风凄厉的吹着,我浑身打着哆嗦,其实爬出车的那一瞬很快,我却觉得似乎已经很久了。^/ /^最终我迷迷糊糊摔在沙地上,只剩下大口大口的呼吸,狂风刮着我的脸生疼,我竟然也不觉得难受。
我迟钝了半秒,才趴在地上望着在车里,我只能看得见半边脸的傅君颜。我见他伸手去拉副导,却被推开。副导开始疯狂的哭笑着喊:“我娘来接我了,我爹娘来接我了……”他笑着笑着,却咳嗽的越来越厉害,手依旧怪异的掐着自己的脖子,然后猛地口里吐出白沫,整个人开始剧烈的抽搐抖动。
我清晰的看见傅君颜眼底一痛,再次伸出的手还僵在半空中,这时车子的下沉越来越快,我顾不了那么多,只是近乎失控地喊他的名字:“君颜!”傅君颜听见我的呼喊转过身,朝副导伸出的手缩回,毫不犹豫的从身后拿起我的棉袄就往外扔,接着又在后座抓起两个水壶扔向窗外,我看他拿水壶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果断的开始往车窗外爬。
流沙的速度太快了,我几乎是爬着过去拉他的手,这时整辆车迅速地被没顶。最后,傅君颜只有两只手露在窗外被我死死的拽着,而他的身体全部被埋进了沙里。
我开始害怕,几乎是疯了一样拼命的拉着他的手把他往外拽,眼泪忍不住的就往下掉,那样的心情太复杂,我甚至有一刻在想,他要是没了,我也不活了……当终于,傅君颜从沙里爬出来的时候,他几乎像失了所有力气一样瘫倒在沙地上一动不动,整个人剧烈的咳嗽,口鼻里全是沙。
我不管不顾的哭着爬过去死死地抱着他,捶着他的胸口就喊:“傅君颜你疯了吗?你疯了吗?你救人就算了,你浪费时间扔衣服做什么?扔衣服出来做什么?”
他又咳了几声,才有了些力气伸出手来回抱我,我听他平静的笑着对我说:“呆河豚,你怕冷。”我听了,抱着他的手一松,只觉得哽咽的说不出话来,像被人掐住了心脏最柔软的地方,半天,也只有喘息。
我撑着自己的身子,手上不停的用围巾替他擦脸。可是,怎么擦也擦不干净,我们俩身上到处都是沙,根本没有干净的地方。终于,傅君颜压住我的手,微微摇头,他无奈地说:“傻孩子,别哭,我们只有两壶水了。”我无力的望着他,额头沉沉的靠在他肩上。
我们筋疲力尽的就这样倒在沙地上,四周黑漆漆的,身下的流沙也似乎很柔软温柔。谁也无法想象,就在刚刚的那么短的时间里,它是怎样无声的就吞噬掉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周围能入耳的,只有风声和彼此的呼吸声。四下一片冰凉,温暖的,也只有我们彼此身体的温度。
然后傅君颜慢慢的蹲起来站直身子,起身捡起抛在了不远处沙地上的棉袄,回来,蹲□默然的看着我,轻轻的揉了揉我的发,把棉袄披在我身上。才又走了几步,背对着我弯身去捡水壶。
我的心下一片混乱,才迟钝的在脑中不停的问…副导呢?副导呢?真的没了吗?
我近乎呆滞的看着眼前的一切,身体开始后知后觉的颤抖。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我趴在沙地上,僵硬的伸出手,徒劳的在沙地上挖了又挖,可不管我用多大的力气,却只有流沙划过我的手心,其他的什么也没有,眼前的沙地,也一点变化都没有……
傅君颜这时才回到我身边,他手里拿着最后从车里抛出的两个军用水壶。他看着我双手抓着一把沙怎么也不放发愣的样子,眼底滑过深深的心痛。
他把水壶放在一边,似乎怕吓着我,轻轻地喊了我一声,才蹲□双手死死的握住我的手,我听他无比温柔地说:“不要怕,我在这里。宝贝要乖一点,来,跟着我一起,松开手,放轻松。”我就抬起脸望着他,跟着他一起缓缓的放松力道,流沙从指缝中划过,化为虚空。
他朝我鼓励的点点头,伸手拉我起来,然后把我搂在怀里,无声的一遍一遍拍着我的背。可傅君颜满手都是沙,我也好不了多少。然后,我看他微微侧过脸,望着车子被埋没的方向,久久的沉默。
我僵硬的抿着嘴忍着泪,心里还存留一点侥幸,红着眼眶颤抖的问他:“副导刚刚,也许是晕过去了对吗?我们挖他出来好不好?也许,也许能有救的……”
“他死了。”傅君颜闭了闭眼,毫不留情的否决了我无望的幻想,他眼底沉重,怅然的把头搭在我的肩上,一字一句条理清晰的开口,他说:“副导有严重的哮喘,吸进了大量的沙尘,本来就可能导致呼吸不畅,可那并不致死。但他最后出现了严重的心肌梗塞现象,又或许是他自己把自己掐死的……我只可以肯定,当我爬出来的时候,他确实已经断气了。”
说着他顿了顿,才继续道:“我想,是他内心的极度恐惧,加速了他的死亡。而且,宝贝你要明白,我们徒手,是没有办法在沙漠里挖出一辆车的。”傅君颜平静的说着,他松开环着我的手,僵硬的扬起唇角安抚的对我笑。我因为他的镇定安然而觉得安心,却实在不喜欢他这样沉重的笑容……
然后,傅君颜退开一步看了看我,摸摸我的头,伸手取下我脖子上的围巾,搭在手臂上。接着微微垂首认真的替我穿棉袄,细心拉上棉袄的拉链,又把棉袄领子立起来,尽量的拉拢,不让风漏进去。然后拿着挂在手臂上的围巾看了看,手抓着围巾的两头就开始用力,很快,哗的一声,围巾被撕成两半。
他拿起一半围巾毫不犹豫的盖在我发上,像阿拉伯妇女的装扮一样的,把布妥帖的缠绕了几圈,遮住我的脸,最后只让我露出了一双眼睛。然后傅君颜又把剩下的围巾撕扯成两半,他蹲□,拍拍我的手让我撑住他的肩膀,捧起我赤着的脚丫,用围巾细细的包裹。我这时才后知后觉的想起,自己是赤着脚的。
我撑着他肩膀的手微微用力,他似乎知道我心中的波涛汹涌,手上为我缠脚的动作没有停,仰着脸,沉静的眸子望着我,依旧那么黑亮光明如星空浩海,他哄着我说:“宝贝要委屈一点,我的鞋子你穿了太大,在沙里走不方便。夜里冷,白天热,宝贝就先穿我做的布鞋。等我们走出去了,我赔你很多双好看的鞋子好不好?”
我点点头,红着眼说:“傅君颜,我要很多很多……”
他点点头,呼出一口气来,把‘布鞋’稳妥的绑好,站起来,隔着围巾摸摸我的脸。然后他回身,望着身后平静的沙地,垂睫低声说:“来,我们给副导鞠三个躬吧。”
我点头,想起副导,却还是觉得胸口压抑着一块大石,闷着难受。半响,忍不住仰起脸问:“如果我们走出去,找到人,他们能不能把副导找出来?一个人被关在那么狭窄的车里,他该多害怕呀?”
傅君颜没有回答,而是极深的望着我,他搂着我走了几步,然后我听他开口唱:“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这是副导最爱的歌,从电影开拍,我几乎天天都能听到他唱,从最开始的好奇,到后来的耳根磨出茧。却不知道最后一次,是在这样凄婉的情景下,傅君颜双眼泛红的唱出来的……
我们对着沙地三鞠躬,傅君颜沉默了一会,才转过脸看我。他的羽绒衣被留在了车里,身上穿的衣服并不多。但他拉起我的手,手心却很温暖。我听他说:“宝贝,趁着天黑,我们要赶路了。”
我点点头,紧紧的握着傅君颜的手跟着他走,只是偶尔,我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回首,望着那个方向,那一片黄沙。那里面埋葬着一个中年男人,他年少时费劲心力的离开这片土地,人到中年,却以这样突兀而惨淡的方式回来……
因为不时的回头,我们走的很慢,傅君颜突然拉着我的手停下,他自言自语的说:“我们刚到新疆,副导代剧组来接我们。我看他待你温和,从车里捧出来早就准备好的哈密瓜给你解渴,所以才多关心了他几分。我还答应他,餐厅开张的时候要给他哥哥捧场……”语落,他却伸出手掌捂住我的眼睛,拉过我往后回顾的身子,他说:“宝贝,别回头,我们走。”那一声,带着太厚重的苍凉,像是对我说,也像是对着他自己说。
深夜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特别冷,傅君颜用围巾把我裹的那么紧,可风吹起的沙尘还是偶尔刺疼我的脸。脚底隔着围巾,也仍然有刺骨的凉意。而傅君颜,没有穿棉袄,只穿着一件鸡心领羊毛衫和白衬衣,那些,在这温度零下的夜里,根本无法御寒。
可傅君颜怎么也不让我把棉袄脱下来两个人一起披,我要把遮住脸的围巾取下来给他,他也不肯要。他说:“宝贝乖,不要闹,你冻坏了怎么办?”
那么温柔的语气,却让我好难过,我就一直在无边的黑暗中跟着他的脚步,仰望着他的侧脸,心里好怕好怕他被冻坏。走了很久,我们到了一片戈壁滩,傅君颜终于停下脚步,他拉着我仔细的在黑夜中观察戈壁的走向,又抬眼望着天上的星星再一次确认方向。然后侧过脸问说:“累不累?”
我摇摇头,知道沙漠的白天要经历暴晒和高温,更不好走。只是问他:“傅君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