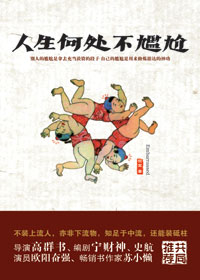乡关何处-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山谷中怎么也无法听见昔年纯净咯咯笑声的余响了。我更无法想象,外婆、父母的亡灵,如果真如传说需要回收他们在人世间的脚印,他们又该怎样再次翻越千山,来重觅这个黑暗的青石深巷啊。
二
不管怎样变迁荒芜,我以为,有故乡的人仍然是幸运的。
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人的故乡何在,他们许多都不知所云。他们的父母一代是有的,但到了这一代,很多人都把故乡弄丢了。城市化和移民,剪断了无数人的记忆,他们是没有且不需要寻觅归途的人。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这样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
“故乡”一词所能唤起的温馨,非仅其风景全殊,乃因那一曾经的所在,有着自己牵肠挂肚的故人。即便岁月淘换,如杜诗所说“故人日以稀”;甚至还乡的道路尽头,最后只剩下你自己凄惶的影子在夕陽下卷曲着往事;那故乡依旧还是足资埋骨的。我的故乡过去传说的赶尸佬,就是要把那些充满乡思而流落异乡的游魂,千里迢迢也要接回家山。可见从屈原开始,我们那一带的人都有怀乡癖。
楚文化向来巫风很盛,与齐鲁的史官文化对应,可以称为巫官文化。溯其源自,这种巫风大抵应该出于山地民族的巴人。巴巫并称,就像今天地名存留的巴东和巫山相对一样。巫是一种神媒,可以通过歌舞而沟通自然与神灵。巴人(今土家族)的巫风传承由来已久,虽经历朝羁縻压制,但在我的童年,还能在乡下寻常感染到那些神秘民俗。
巫师在我们当地又叫端公,似乎是因为他们做法事时的一个重要仪程而得名——他们要把烧红的犁铧用赤手端起。端公有很多法术,于少年的我常常是无解的。但经常的耳濡目染,往往也深入心灵。记得有一个端公的儿子,因为时代原因不能继承父业,只好当了工人。就是这个会念咒止血的大人曾经对少年的我说——如果你长大后不能让家乡扬名的话,那你就没有资格埋葬在家乡。
也许他原本只是在对我进行一种理想教育,对我而言,却似乎被一个古老的咒语所锁定了。若干年来,我几乎行遍天南海北,用哥们马松的诗句来形容——把天下道路走成了拖鞋——但是我依旧未能走出这一咒语的情结。如果我不写出那片土地上的故人故事,有几人曾知那一穷荒僻野,更有何人知道故土上那些真切的荣辱悲欣。如果没人知道那些默默无闻而又可歌可泣的地名和人事,那我若干年的寄生和成长岂不是一种虚无和负罪。到真正树老叶落之时,我确恐无根可归了。
三
23岁的我自以为霜刃在握,可以问剑江湖了;收拾琴书,仓促揖别故乡山寨,兀自闯入了别人的城市。那时的人知道敝乡的甚少,不免要多费口舌才能说清洒家的来路。我曾经在一首诗里说——君问深山深几许,无言我自上层楼。浮云有尽家何在?旷野无垠望不收。落日犹从岭树坠,大江原自故乡流。几回遥指雁归处,迷眼峰峦即首邱。
90年代中旬,劫后孤身再来到别人的首都乞食之时,故乡偶尔也曾遗忘在出逃的路上。那时确确乎只剩两袖清尘了,胸中的万古长刀早已为险恶世事所磨损。我借住在朝内小街南拐棒胡同某大杂院的一个偏房里(梓夫说是肖复兴的旧居),初次深刻地体验了北方冬夜的刺骨。那时,我常想起沈从文初来北平卖文时,郁达夫第一次去拜访这个来自边城的无名作者,看见他吸纳着清鼻涕,用长满冻疮的手在抄写稿子。郁达夫临别不忍,掏出仅有的几个大洋放在了桌上。每每在深夜想起这个故事,总要惹清泪几行——人世间的滴水之恩,于异乡人来说,都是可以湿透青衫的。
十年京华厮混的我,久疏了故人,故乡也在望眼中迷离而稀薄。至于身经的故事,在一个杯弓蛇影的时代,只能悄悄地刨土埋存。楚人闻一多的诗句谓——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我想那时首善之区的酒色灯影,正渐次漂淡着我的恩仇。
一个打小便奢望文章立命的男人,被青春革命的洪流所裹挟,几番载沉载浮之后,却可能要以一个“不法书商”的身份终结余年——这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显得荒诞而悲剧。出山又二十余年,上半截心脑埋在故土,下半截身子飘荡在异乡。
一转眼惊青鬓雪,再回头俟黄河清。转顾半生来路,学殖荒疏而马齿徒增,如何敢面对那一方日渐沦陷的故土啊;那些失散的亲友故人,那些漫漶风化的人间故事,都在暗夜里鞭策我几近麻木的神经。于是,终于在2006年,我决绝地挥别了京门。垂老投荒,原只为心中还耿耿然竖着一支狼毫斗笔,那上面浓濡着的陈年血泪已然如漆。世道往还,该轮到我们这一代泼墨大书了。
四
为了还债,终于完成了第一个散文集《江上的母亲》。这是平生初选的第一部拙作,在台湾出版。
香港祖国的出版家,深知内地出版的艰难,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读到我的故乡,又再度编次了我的选集。这个册子,增添之后更名为《拍剑东来还旧仇》——书名来自于我多年前的旧诗——两袖清尘一枕愁,飘零身世等浮沤。白头休废名山事,拍剑东来还旧仇。
写完了母亲之后,我便开始写父亲。在拙著《父亲的战争》里,我想极力反思土改。我担心父亲的亡灵在天上不肯瞑目,怕他骂我作践了这一堂好人物。于是,我不得不把剧本再次转变为小说,借以还原我的创作初衷和历史真相。
就长篇来说,这是我的处女作。同样的故人故事和故乡,构成了我的叙事。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出于虚构,似乎又源于父亲的身世和故乡的种种传说,源于我们渐渐厘清的乡村史实。故而下笔有情,无论正邪敌我,我都把他们还原为人在写——这个世界原本只有人,敌人只是各种时代的政治定型而已。我们时代的文学,只有在进化到一视同仁的时候,似乎才具备了人性和神性。
现在这部长篇也终于在大陆面世了,可惜由于受了剧本结构的影响,拙著在这里显得近乎通俗——不免沉陷于一些悬念冲突和对白之类的技艺。于纯正的文学而言,我实感汗颜。如果有心的读者仔细品味这些关于个体的悲剧和时代的厄运等等,也许还能谅解我的粗糙。
在是非恩仇二十年的特殊年份,能够同时推出这样三本书作为祭奠,于我肯定是欣慰的。我相信我所有亲长的亡灵,都会为此而略感慰藉。虽然还未报人间已伏虎,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坚信,我才愿如此苟活于斯颓世。迅翁当年写完一部书之后说,“窗外是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我在生活,我还将生活下去”。这样的中年情志,我于现在,算是略能体悟了。
这个世界多的是著作等身的人,几部微著的出炉,远不值得嚣张。之所以还要添足这样一个注脚,的确是要向读者诸君谢恩。说实话,没有这些年你们的鼓励奖掖,我真难有激情自说自话。迷失于这个时代的同道,往往只能拿文章当接头暗号;仿佛前生的密约,注定我们要在今世扺掌,然后一起创世,或者再次站成人墙,慷慨赴死。
┃ ┃
┃整理 ┃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 ┃
┃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