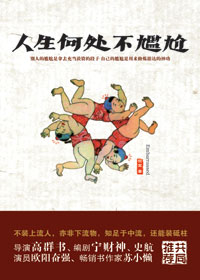乡关何处-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接近完美的居室竟没有一个区域可以置放一张单人床,哪怕是折叠式的。最后,只能在那不足四平方米的餐室铺上一层地板胶隔潮,然后席地而卧。
就这样,面对高的天阔的海,我又有了这么个栖身的巢。
房虽褊狭,却得天独厚;出门数十步便是南渡江的入海口。每到黄昏,往江边漫步而去,便可望见沧海落日的悲壮画面。而渔归的樯帆如林,泊满了江湾,仿佛打开了无数巨大的折扇。隔江即海甸岛,林木葱郁中掩映着一些旧式房屋,俨然还是渔村模样,并无特区洋场之状。海面上刮来徐徐轻风,吹面欲潮;而沿岸的椰树依旧静如处子,只那凤凰花热烈地摇曳着满枝烂红。
夜凉时分,独自回到小室,冷水浴罢,即可裸裎打坐于地,或依一隅,乱翻几叶闲书。想到魏晋名士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也不过如此,便不禁哑然失笑。
南迁本为下海赶潮,原不曾想到在那天涯海角做一安分守己的读书人,故而未尝携书前往。到了其处,却发现凡能形成生意的事皆有捷足先登者,身着警服,反觉备加寒碜。百无聊赖,仍只是躲进小楼,寒泉配食,自命书生了。遂一任旧习,关饷即往书肆,渐渐地又依墙砌起书城来。
之后,内地的友人去得多了,小小斗室竟成了江湖游子的兴隆客栈。相识或不相识的多有慕名或转介而来借一枝栖者,念及同是天涯沦落之客,皆一并接纳,隐然有当年及时雨宋家庄之风。惜乎阮囊羞涩,无法做到樽中酒不空,然而水泡即食面,却不致有断顿之虞。大家乐得有此危巢,免了流寓街头,便戏称为“也是家”。想到人生逆旅,得心安处即是家之理,便借了这句戏言移做斋名。
“也是家”中四壁萧然,别无长物,却偏多蟑螂壁虎。由于只能席地而卧,往往这些尤物便惊扰了许多客梦。不得已,大开杀戒,几至尸横遍野,渐渐算是肃清了“君侧”,可以高枕无忧地读书了。
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大兴开发的喧嚣岛城中,人们无往不为商,开口即谈钱,是怎样容忍了我在那些台风海雨的呼啸之夜,去静心地读《夜航船》之类闲书的。当现在再重新翻阅其时在当地报纸上所开的“海客野语”专栏上那些闲文,自觉曾是怎样的不合时宜呀。然而在当时,确确乎是在那邻海小楼上,几卷书一壶酒,压住了心头多少浮躁,也淡化了多少浪迹天涯的朋友的客愁。
那个著名的龙年的清明节,我曾只身独往岛中儋县的一个僻乡中,去凭吊东坡书院的遗迹。想到千年前那个流放的诗人,亦曾艰难地在此穷荒之地筑起一座书巢,交游野老,取火传薪,其乐也并不减于那些游宦神京的日子,便有了异代知己之感。书生命蹇,蓬转萍飘,原是自古而然的。但我知道,在那仆仆风尘中,在那一担行囊里,只要(也肯定)还携着几卷诗书,那么,无论怎样遥远而寂寞的驿程,也终不至于太过难堪了。然而,换个角度而论,一代一代行脚万里的文化人,最终却走不出他的书斋,也实不知是幸抑或不幸?
未几便是辞职,我又不得不悄悄揖别“也是家”了。在那个夏日黄昏,我站在渐行渐远的海轮甲板上,回望南渡江口椰影丛中仍闪烁着灯光的小窗时,不禁怆然泣下。“也是家”终于也毁于一场时代的风暴了,而哪里又是我的家园呢?在那夜色浸黑的海面上,我隐约感到正立足于一片动荡龟裂且在塌陷的土地上,新的流放仿佛已经开始。
四、握火亭
80年代末年的记忆充满了乱离,其兵荒马乱的印象似乎接近龙应台笔下的1949年。我单人一骑关河千里地赶回鄂省。那时多没有电话,投亲靠友也无须预约。一些老友至今记得我当时的常态是——上衣袋里插一把牙刷,两手空空,兀然就来了;次日留下几件脏衣服,穿着主人的衣服就走了。那时,哥们儿之间,连短裤都是可以互换的。古人所说的“望门投止”,大抵就是这样的温暖和仓皇了。
次年,我不好意思再辗转于友人沙发,便在武昌的黄鹤古肆街首,租下了一个亭子间。这原本是鹤楼下的一条仿古商街,建在蛇山之麓,紧邻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抱冰堂。张之洞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典出古语“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取的是其茹苦自励之意。我这间砖房楼下乃铺面不能住人,悬空吊了半层搁板,可以席地坐卧,起身几可触瓦。可以想象,在炎都江城,那确有握火之感。遂名此斋曰“握火亭”,也有附骥励志的自诩。
阁楼铺上廉价地毯,起居待客都在其上了。每次还山,都要搬来积年的藏书,渐渐满地书墙可以坐拥;仿佛置身于时代狂飙的风眼之中,竟有一番意外的宁静。
萧窗风雨之际,不免亦有独居者的惶恐。那时我的枕下,伴随着一柄藏刀。想起书剑飘零枕戈待旦的一些词来,便不免长夜苦笑。某夜捶门声急,却是熊红伉俪来访。他们怀抱一个婴儿惊疑道——你门前谁扔下一个孩子?我顿时疑惧,以为必有骗局陷阱。色变,抢过孩子端详,觉得面目姣好,慢慢竟看出哥们儿李斯的模样。待这丫大笑闪身出来,才知道他们合谋戏弄老夫。
作为烟厂采购员的我,那时悠闲得近乎无聊。一群同事拿着一张晚报的征婚启事来和我打赌,说我要是能追到此主,可以输我一席大酒。我看那条件,确实不凡,争强好胜之心顿起,便修书一封让他们寄去。未久,得复函相约某日于汉口舞厅门前。窃喜,传告诸友。众皆潜随,我按约定办法手持诗刊傻等,果见一女高头大马而来。对上暗号,她不要我买票带我直入舞厅,门卫见之恭称大姐来了。我心下肃然。
入座,经理又来献茶寒暄。之后我们彼此拿出证件验明正身,看是否如信中所言。我接过她那眼熟的印着国徽的派司,翻开果然是市局某处的警员。她坦承接到上千情书,选择五个见面,我是其一。她是认真的,我却盘算着如何从这场赌局里抽身而逃。当夜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结束,我无奈被要走座机号之后便去吃哥们儿的大酒了,哪敢再续这场危险的游戏。
几天后,她和另一女警突然敲响了握火亭的木门。我并未告诉她地址,惊疑询问,她笑曰——有你电话就够了。我调阅了你的资料,觉得你没有说假话;你这人还不错,带朋友顺路来看看你。
当夜,俩着装女警借走了我的两本书,以便再来有借口。之后,家父来住院,吾母移来小驻。再之后,我被密捕于大街上。而书,她们还没来得及还。
之后不久,大姐就接走了父母,搬走了我残存的书籍杂物;又一个书斋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朋友后来来信说,我失踪之后,他曾经路过我的门前,他说“看见你的母亲在斜陽下磨刀,白发枯槁,似乎有泪水滴落在磨刀石上。我不忍去打扰她,便默默走了”。
记得那年秋望寒山,我曾经填词怀念这个鹤楼下的短暂客居——小街画栋,记青琐邀月,当年曾住。红毯朱帘书四壁,高卧独听风雨。席地谈诗,拈花赌酒,斗室留佳侣。黄昏吹笛,有人尝识清趣。倏尔鹤往云飞,曲犹未散,迁客无归路。瞩目青山秋色里,掩映旧时门户。灯火阑珊,笙歌缥缈,槛外空凝伫。凭篱惊问,百年身寄何处?
那时在阁楼上,最爱来席地对卧的是李斯。这厮经常三更半夜和嫂子一言不合,便私奔来此,且奇怪地要和我酒后笛箫对奏。我们少年时都是在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待过的,乡下孩子胡乱会一点民乐也是常事。但手艺荒疏已久,这会儿再来深宵吹笛引鹤,确确乎太杀风景。派出所只有在此际,实在听怕了我们的“我爱北京天安门”,才会来拍门求饶。
关于握火亭的故事,还有个结尾。那个女警后来又通过我的一个警界哥们儿找到了我,请我去吃麦当劳,并带回了当年借走的书籍。我抱歉地玩笑说,当年确实不是想打进敌人内部而接近你的,只是朋友们的一个赌局。她也豁达开朗,笑说我现在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先生就是当初那五封信的主人之一。
尘世间的际遇,于我算是略显一点奇特的。冥冥之中我和一些房屋的缘分,似乎始终难以久长。只有朋友和书,磕磕绊绊地总能伴随终生。虽然也会走丢一些,散佚一些,但留下的绝大多数,都是要白头偕老互送花圈的了。
12.故乡·故人·故事——关于拙著几种的注脚并答谢天下同道
一
故乡利川,看地图在中国的中部,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十分偏远。它是鄂省伸进渝界的一只脚,且是湖北海拔最高的一个县治。在古代,这里乃巴国的腹心,也因此民俗至今犹带巫风。巴国亡得太早,没有留下什么太值得一说的典章文明,于是自古以来,这里的人民就被视为化外蛮夷。
我在最近所写的利川赋里,这样描述它的区位——荆南重镇,鄂西雄关;土苗边城,尊名利川。河山横断,北枕峡江夔门之险;风物卓异,南控潇湘武陵之源。巴人祖居,西邻涪万峻岭;楚国故地,东下江汉平原。天接湖广以远,南北植物交汇;地托云贵之高,东西经济界连。人文介乎蜀楚,民俗肇自夷蛮——看上去似乎不免有因故土情怀的溢美,但仔细考察,却也能大抵坐实。
我出生于本地汪家营镇属下的鱼泉口村,那曾经是川鄂两省的界碑所在。据说从我家赁居的老宅走出去百步,就进了渝地的石柱县。可是我在利川生活了二十几年,竟然却从未去看过那个传说中两省赶集皆汇于此的老街。我大约两岁多便被父亲用箩筐挑出了那里,因此记忆中毫无屐痕。也因为即便在利川,它也算艽野僻地,所以一直到背井远游,都未曾去回顾过那个民间称为“西流水”的小村。
去年返乡,两个姐姐和我要走一趟重庆,不经意间开车就经过了这里——全家一别45年的地方,大姐还依稀能辨认。她急忙叫停车,大家一起下来站在公路边。路畔是向西流的河道,却已枯瘦如泪痕;河对岸便是一排老式的土家吊脚木屋,大约也就只剩百米长度了。看得出来,几乎每一家都是颓壁残垣,全无人间烟火象。不到半个世纪,一个曾经喧哗的古镇,就这样悄然地土崩瓦解了。
隔着时间的暗流,大姐遥望着风物迥异人事全非的对岸,眸中含泪喃喃自语——我们家就是那个老屋,那是甘家的大宅,那时是这里最好的吊脚楼啊!完全看不出来了,那些人呢?他们去了哪里?怎么会整整一条街就搬空了呢?河水怎么也不见了,童年上学,爸爸每次都要目送我过那个桥,那时觉得这是好大的一条街一条河的,怎么现在完全不像了呢?
对于有记忆的两个姐姐来说,目睹这样沧桑的故地,遥想那些艰难却举家齐全的温暖日子,此际必定是残忍的。而我,似乎连梦境中都未浮现过这个陌生的荒村,幻想过多年的小桥流水人家,突然直面的却是这样的一片荒凉,心底竟有几分不敢相认的漠然。
但我深知,曾经的合家居留是命定的存在。我的胎盘肯定按乡俗,也曾悬挂在对山的某棵树上;襁褓中的初啼毫无疑问曾经喧嚣过这个死寂的夜空。而今中年还乡,早已无从辨认哪一棵树是父母的手植,山谷中怎么也无法听见昔年纯净咯咯笑声的余响了。我更无法想象,外婆、父母的亡灵,如果真如传说需要回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