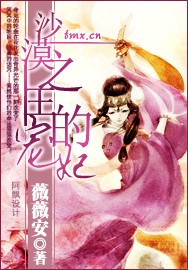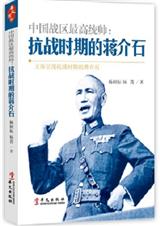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印刻文学生活志》六十一期,《朱天心答朱伟诚问》这或正是朱天心的“法则”:不断插入的旁注,旁注的页沿再被插入延伸了更汹涌语义与无数张“我记得”的禽鸟俯冲快速变换调焦的层叠回忆照片。一开始我们以为那轻灵(而且显得不够多以组成“伪辞典”)的小章节是数独式的填字游戏(误解的词);或如唐诺在朱天文《巫言》的长跋中提到的,吴清源所说“当棋子不在正确的位置时,每一颗看起来都闪闪发光”的星空。……但我们很快就大汗淋漓地发现,每一刹那被朱天心填进空格(或挟起抽换掉)的数字,每一枚被她放进那次叙事那个位置的棋子,都像将要引爆一场连续液态炸药的第一粒灼烫的硫磺,或是核分裂核融合千万次方扩散(无法收回的地狱场景)第一个塌瘪崩溃的原子。
这时,《神隐》展开了,插入“第二次”的另一个“第二次”(以及等比级数或如连续引爆的“误解的辞”)的“旁注”沙沙编织起来。波赫士所谓“两种(或两种以上)庞大隐秘、包罗万象的历史”。
黄锦树当年在《从大观园到咖啡馆——阅读/书写朱天心》一文中,以小章节分项定义且论述的“都市人类学”——包括“资讯垃圾”(一方面显示朱天心“一篇写尽一种题材”的惊人企图;另一方面却又透露出她作为都市社会中资讯/垃圾处理机的深沉忧郁);“蛮荒的记忆”(黄文引《去年在马伦巴》)中慢慢退化为爬虫类的拾荒老人,及《鹤妻》中在“台湾男袜业发展史”、“近五年家电史”、毛巾史、洗衣粉史……物化的世界里为了抗拒男性对她的遗忘(在死前、死后)以商品填满所有隐蔽的角隅,“彻底异化为一个更加静默他者”的鹤妻解释,朱天心“以取消时间纵深度的方式来诠注都市文明中断裂的现前,把在时间共时化中消失的历史还原为神话,人类的历史从“蛮荒—文明”转变为“蛮荒—蛮荒”;“历史”、“巫者:新民族志”(“作为巫者,他们进入神话的时间,进入由无数的‘死亡’堆彻成的‘过去’。在叙述着神经质的旁白、解释性的叙述中,作者援引心理学、哲学、人类学的论述,举证历历……透过类比……”)如今重读,仍奇异地具有如此新鲜、强大的诠释效力。
“神隐”,即是穿过宛如昨日重现的垃圾坟场、老灵魂多年前彳亍作人类学观察的原始部落旷野、神话的时间(这时我们领悟朱天心式的,波赫士之一个以上的“包罗万象的历史”之构建)……如那只变貌成腐烂神的河龙,偿还时间/物质/人类学式庞大城市记忆债务地,哗哗吐出这一切“变老”噩梦的造梦材料。
作为读者,我们原本从《古都》那些一趟趟“埃米莉的异想世界”式的城市蛮荒里乖谲、暴走、颠覆性的“出走/离场/伪物质史”召唤而起的“抒情—愤怨—滑稽”复杂情感,在《漫游者》那黄金印记,如同《百年孤寂》老邦迪亚率族人在一片“长征者的皮靴陷入热腾腾的油滩”,“像梦游般走过悲哀的宇宙”的“寻父之途”梦中沼泽的乱迷、哀恸与神秘性之后,似乎印象的判准朝向朱天心小说的抒情与“愤怨著书”(王德威先生语)倾斜。我似乎也惯性地在阅读朱天心小说的预期舌蕾上,忽视了那些其实荒谬滑稽,难以言喻的鬼脸,一直到《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不,应该说是跟随着第一章之后的第二章,我们被那强大抒情力量带引,愈陷愈深的浓愁耿耿,凭吊伤逝之情裹胁,却在某些段落出乎意外地噗哧笑出声。(啊?怎么搞的?)
我不很能厘清这种混杂了抒情、愤怒同时古怪滑稽的情感是怎么进行的,或如巴赫汀曾在《讽刺》这篇短文所作之界定:以其真正的形式而论,讽刺是纯粹的抒情——愤慨之情。
讽刺并非作为一种体裁,而是作为创作者对其所写现实的一种独特态度。
……所有这些笑闹的节日,无论是希腊的,还是罗马的,都与时间——季节的交替与农耕的周期有着重要的联系。笑谑仿佛是记录这交替的事实,记录旧物死亡与新物诞生的事实。所以,节庆之笑一方面是嘲讽、戏骂、羞辱(将逝的死亡、冬天、旧岁),另一方面同时又是欣喜、欢呼、迎接(复苏、春天、新绿、新岁)。这不是单纯的嘲笑,对旧的否定与对新、对美的肯定紧密交融,这种体现于笑的形象中的否定,因而具有自发的辩证性质。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这整部小说当然是环绕着“时间”这一主题进行复奏式的辩证,形式上它在章节间违反现实(或阅读惯性)之逆转、倒带、不同钟面的景框跳跃、停格(微物之神出现)……形成一种小说时间默契的挤迫与松脱,高度期待而骤转虚无,一种(看不见的钟表)机械意象侵入的错置感。在对时间的辩证本身,它所形成的“纯粹的抒情——愤慨”又远比古老农耕节的时间想像要严酷残虐许多:因为衰老(或将逝的死亡)并不是欢欣迎接新生的递嬗旋转门,它是一幅巨大的文明场景将被遗忘(石化、废墟化、天人五衰)不为人知的秘密抢救行动。小说家让人瞠目结舌的追忆幻术相反地是在“对旧的(等价时光之无限延展)怀念,对新、对美的质疑”,在极窄如“站满天使之针尖”的时间切点之上打开。而各章节间的辩证互相颠倒、逆反……
(这正是“第二次”的力量所在。)
大江健三郎在《小说的方法》第七章《仿讽及展开》中,提到俄国形式主义者关于“延续小说事件”,讨论“怎样通过叙述事件的方法让事件的整体像物那样深深地印在读者的意识中?”“被‘陌生化’的事件又如何成为我们‘明视’的对象?”“怎样开拓出与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发展不同的途径?”
史科拉夫斯基指出:
主题这一概念经常与事件的记述以及称为内容的叙述相混淆,但是,内容只不过是构成主题的素材。
……艺术的形式不是靠日常生活的动机形成的,而是通过艺术本身内在的法则来说明。延长小说的做法不是靠纳入对立者,而是靠置换几个部分而得以实现的。作家通过这个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构成作品方法背后的美学法则。
换言之,即《项狄传》作者史丹在扉页引伊比德提斯的话:“推动人类的不是行为,而是关于行为的意见。”
大江在这个章节中,举了《堂·吉诃德》中,几个“小丑看穿了欺骗作弄他的所有诡计,立刻在内心世界颠倒了两者的关系”,滑稽性模仿的例子(包括主仆两人被作弄骑上木马且糊弄那是可以在天空飞翔的滑稽机关;包括桑丘作为狂欢节小丑当上“岛上的总督”;包括挺身保护引起众怒的牧羊女……),如何“通过显露对既有手法的仿讽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小说结构”。最感人的一段是写到,意识到自己不久人世的堂·吉诃德把朋友们召集到病床边,对他们说:我确实曾经疯过,但是,我想做一个正常人死去。
他的仆人,一直扮演给堂·吉诃德这种疯癫的冒险泼冷水的桑丘,这时却着急地劝他:啊呀,我的主人,您别死呀!……您别懒,快起床,照咱们商量好的那样,扮成牧羊人到田里去吧。……假如您因为打了败仗气恼,您可以怪在我身上,说我没有给驽马系好肚带:害您摔下马来。况且骑士打胜打败,您书上是常见的,今天败,明天又会胜。
大江写道:“在此之前,正像堂·吉诃德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一直是疯癫的冒险。可是,对守护在病床前看到堂·吉诃德垂危的桑丘·潘萨来说,已经不用担心自己再次被拖入冒险的行列,他获得了新的感受。真正给自己封闭的农民生活带来活力,使自己的生命焕发生机的正是与堂·吉诃德所进行的冒险。桑丘·潘萨认识到日常生活的自己与其他农民一样精神正常、碌碌无为,通过充满活力的自我解放,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想像力活跃的世界。”
或如波赫士在《另一次死亡》里那个死了两次的达米安,提出了两个时间版本:一个是一九四六年在恩特雷里奥斯去世的懦夫;另一个是一九○四年在马索列尔牺牲的勇士。
达米安战斗阵亡,他死时祈求上帝让他回到恩持雷里奥斯。上帝赐恩之前犹豫了一下,祈求恩典的人已经死去……上帝不能改变过去的事,但能改变过去的形象,便把死亡的形象改成昏厥,恩特雷里奥斯人的影子回到了故土。他虽然回去了,但我们不能忘记他只是个影子。他孤零零地生活,没有老婆,没有朋友;他爱一切,具有一切,但仿佛定在玻璃的另一边隔得远远的,后来他“死了”,他那淡淡的形象也就消失,仿佛水消失在水中。
一九四六年的版本则是:
达米安在马索列尔战场上表现怯懦,后半辈子决心洗清这一奇耻大辱。他回到恩特雷里奥斯……一直在准备奇迹的出现。……四十年来,他暗暗等待,命运终于在他的临终的时刻给他带来了战役。战役在谵妄中出现,但古希腊人早就说过,我们都是梦幻的影子。他垂死时战役重现,他表现英勇,率先作最后的冲锋,一颗子弹打中他前胸。于是,在一九四六年,由于长年的激情,佩德罗·达米安死于发生在一九○四年冬春之交的败北的马索列尔战役。
波赫士说:“《神学大全》里否认上帝能使过去的事没有发生,但只字不提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那种关系极其庞大隐秘,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取消一件遥远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取消目前。改变过去并不是改变一个事实;而是取消它有无穷倾向的后果。换一句话说,是创造两种包罗万象的历史。”
“第二次”的力量:不论是大江所说的“想像力活跃的另一个世界”(堂·吉诃德主仆针对“现实”或庞大骑士传奇牧羊人小说所发动的);波赫士所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创造两种完全不同,却各自包罗万象的历史”;或纳博可夫在《幽冥的火》中炫技展开的“小说之于诗的肿瘤式话语增生繁殖”,一个妄想症者脑中汹涌冒出的“不存在王国历史”。朱天心在《初夏荷花时间的爱情》启动的小说时间,绝不仅仅是我们那个年代所谓“开放式结局”如芥川的《竹薮中》或符傲思《法国中尉的女人》,“几个不同版本之情节”。那更接近于昆德拉谈论卡夫卡时所提出的“赋格”——拉丁词原意是“飞翔”或“追逐”,同一主题在其他声部模仿、变奏、形成各声部相互问答追逐——“我把我的歧路花园留给许多未来,而不是一个未来”,是的,但朱天心在这每一座拆掉重搭的歧路花园里,天啊她打开了“小说不只是故事,而是关于人类行为之意见的全部话语”的潘多拉盒子:想像力、历史、记忆、虚构的权柄、哲学的雄辩……“第二次”并不是与第一义篇幅相当而情节不同的“另一个故事”,而是“小说的全部”——作为晚近愈见泛滥的所有将小说变成冰雕婴孩仿冒货(卢卡奇说的:“小说有一个孪生兄弟:通俗小说”?)的陈腔:“现在的小说家愈来愈不会说故事了。”或者,某些只在第一义便完成小说阅读之生产与消费的懒惰读者轻率下标:“认同焦虑”、“城市书写”、“身体/性别”……的那些小说;甚至她如哪咤刚烈寡恩在抛甩着那些(包括她自己写过的小说)曾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