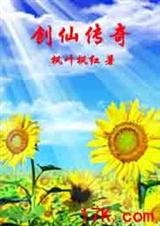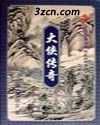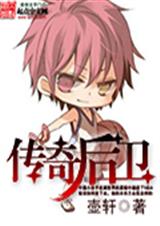亦舒传奇-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亦舒通过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告诫读者,特别是女读者:身为女性,要处世立身,惟有学会自己保护自己,而最有效的自我保护,是在经济与人格上的平等独立。
在亦舒看来,真正男女平等在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女性的独立自主不仅要经济独立,还要精神独立,唯其如此,才不致于沦为男人的花瓶。
像《我的前半生》、《独身女人》、《胭脂》等作品,亦舒都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去昭示:求人不如求已,靠自己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方能如鱼得水,自由驰骋,无拘无束,享受人生。
《憔悴三年》更是一则现代女性与命运、环境抗争而最终能更好地生存。生活下去的都市文明最生动的“传奇”。
作品中的刘玉容是平平常常的都市女性,一份苦闷的工作,菲薄的收入。最不幸的是,丈夫离开了她,留给她一个两岁的孩子,娘家环境欠佳,也不容她回去。
而那位黑衣女子,却是死神的化身。
作品的故事发展就在这两个女子之间展开。
生活累人,同事互相倾轧,刘玉容真的就想一了百了。
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有什么在等着你。”“前程掌握你自己手中,何用假他人之手。”
一言惊醒梦中人。
有伙伴当然好得多,并肩上路。但像刘玉容不然一身那般奋斗而成绩骄人的,也大不乏人。
世上凡事均需付出才能得到,这世界还算是公平的。
也许,只有勇者才会默默地过最平凡的生活,不间收获。
在这个短篇中,最不可思议的,是亦舒把死亡的化身写成那么一个形象。一个沉郁的故事,用了她一贯的幽默无忌辛辣犀利的彩笔,而画出了一抹明亮的色彩,确实是很有励志作用的。
连死亡女神都可以是这付模样:
甘七八岁年纪,大热天,穿黑色套装,却态度从容,笑脸迎人。她通身打扮考究到极点,一副珍珠耳环发出晶莹的光芒,衬得她肤色更为明亮。
亦舒还会去写传统小说惯常见到的“歹角”吗?
当然不会。
生活本身就不是黑白分明的,也不一定是灰色的,大都是“椒盐式”的。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中的人,自然也是“椒盐式”的。
她从不在文字上谴责什么人,只是把一个人的想法,做法写出来,把一个人的性格写出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他有他的缺点和惹人厌处,也有他的优点和惹人喜处。
《喜宝》中,喜宝的出卖自己令人齿冷,但她那么执着在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中保持自尊,又令人。已生同情。
当勖存姿说:
“也不止是物质,情感上我还是依靠你的。你为什么不能爱我:“
姜喜宝回答:
“我在等你先爱我。”
“不,你先爱我。”
勖存姿很困惑:
“为什么,有什么道理我要那么做?你为什么不能先爱我!”
一个为金钱而出卖自己的女人,是没有自尊可言的,喜宝在出卖自己之际,并没有要求自尊,她可以忍受侮辱,甚至掌捆。喜宝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出卖的时候,她不要求什么自尊,只是买卖。
但当说上面那番话时,他们讨论的,并不是买卖,而是爱情,这是截然相反的东西,在爱情面前,喜宝需要自尊。
她是一个矛盾的人,却有着真实的人性。
亦舒很擅长写这一类活生生的人,这也是她的故事耐读的关键之处——总是在变化转折中。
在《两个女人》中,谁知任思龙和她的外表反差那么大。
一身洁白的衣衫,显示的就是高洁吗?她一样有不为人知的不堪。
就如施扬名的变化,也有客观环境的不如意。
亦舒关注入的本能在外界力量冲击下的种种反应,留意不同人格间的纠缠与摩擦,并无心表现个人与集体的冲突,更很少扫描个人如何归附时代潮流。在她的一个接一个的爱情故事中,读者只能嗟叹,却无从怨艾。
对世界摒弃道德感的投入,却时常露出陌生迷惑的神情,是亦舒在创作时的一个特色。假如透过狭隘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窗口,便会对她的作品发出指责的口吻,从而遗落许多闪光之处。
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从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
张爱玲这一段话用到亦舒的创作历程上,也是相当的贴切的。她的作品并不是耸立在现代都市的神话与寓言,她对现实的真切描绘和对都市中的小布尔乔式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嘲弄,有为疲惫的心灵寻找短暂停泊地的努力。
悲天悯人与鞭挞入里是她的心理走势,嬉笑怒骂的背后潜藏着她的良苦用心。根扎在中国,渊源于民族,虽饱浸欧风美雨,可念念不忘的仍是这些。
我们与其苛求她给我们带来什么现成的答案,倒不如在细读她的作品后,随意联想。
亦舒传奇……繁与简
繁与简
要有一双非常聪明的眼睛,看到平常事物不平常之处,剔出来,详加形象,方有显著效果。
亦舒《眼》
亦舒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别具一格,她似乎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
人的生命是伴随着一种遗忘了的经验开始,又伴随着一种虽然参与但又无法了解的经验告终。
叙事观点便成了创作小说的最基本的方法。
亦舒小说的叙事观点是多种多样的,既能以旁观者的身份从外部来刻划人物,也可以摆出无所不知者的架势从内部去描绘他们,既能把自己置身于小说之中而对其余人物的动机不予理会,也可以采取别的折衷态度处理。
而她最擅长是运用第一人称写作,揉合白描、象征、巧合、悬疑、反讽和蒙太奇诸种手法,变化多端,生动有趣。
《玫瑰的故事》、《我的前半生》、《风信子》、《人淡如菊》、《没有月亮的晚上》、《我这样的爱她》、《胭脂》、《香雪海》、《朝花夕拾X曼陀罗》等等,均是由“我”讲述故事的主干,这个“我”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很是奇妙。
有时,我们会想,为什么作者要采取主人公自述的艺术格局来写这些小说?是因为它渗透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吗?这样写,可以让自己更自由地投入,更自由的倾诉吗?对此,我们不该作出主观臆断。重要的是这样写,确是做到了让人物的心理自由与情感自抒相互交融,尽情挥洒。
《玫瑰的故事》是亦舒最为有特色的一部作品,它的结构曾让许多人赞赏过。
全书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我”做主角。同一篇小说之中,用了四个第一人称来写,而第一人称的身份又各自不同,这是流行小说写作中较少见的例子。所以,给人很强烈的新奇感。
出奇制胜的效果,光是从这四个不同的“我”身上,亦舒已经如期收到了。
四个部分中的“我”,身份又是迥异不同的,他们各自以自己的眼光,勾勒了玫瑰的某一个生活片段。当他们不是主要的叙述者时,他们仍会出现,但仅仅是配角罢了。
每一个“我”的描述都可以独立成章,但必得四部分连接在一起,才能完成玫瑰一生的情爱生活。它们是有机的整
体,却没有传统小说头尾必得相依的过分的依赖性。“我”作为作品的叙述者,并不见得是个完全的无所不知者。像在第一部《玫瑰》中的“我”是玫瑰的哥哥黄振华,在他的视线中的是少年时代的玫瑰。玫瑰和周士辉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但玫瑰和庄国栋的相恋,开始如何,结果如何,他当然就没有那么了如指掌了。第二部《玫瑰盛放》中的“我”换成了博家敏,他也只能在他的立场里知道自己对玫瑰的苦恋,却也不太清楚玫瑰是如何和他的哥哥“好”上的。第三部《最后的玫瑰》中的“我”是周棠华,玫瑰的未来女婿,带着玫瑰的女儿从美国回香港,见到了玫瑰,才惊讶地发现玫瑰并不是她女儿父亲口中的玫瑰。但也是仅此而已,玫瑰的内心世界,他是不了了之的。第四部《再见玫瑰》中的“我”是罗震中,玫瑰是他的继母。在身份未明之前,他却把她当成了梦中情人,中间又拉扯着庄国栋,他只能无望地沉迷在没有结果的单恋中。而玫瑰,依然是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封闭而满足地生活着,外来的力量最终还是改变不了她。
这样的结构很精彩,亦舒很早已经懂得在适当的时候留下空间,不把话说满,常意在言外,让读者去体会、回味。
小说技巧中最复杂的问题不在于按某种公式行事,而在于作者使读者接受观点的能力——“我”的介入,无疑帮了亦舒很大的忙,读者在阅读之余,会倍感亲切,从而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她常常于叙述当中加入自己观点的议论,产生显著的情感效应。
复杂的故事有复杂的层次,《玫瑰的故事》,几乎写了玫瑰的一生。故事里面套故事,人物众多,却杂而不乱。
黄玫瑰的几次恋爱自然是主线,她跟庄国栋,她跟方协文,她跟博家明,她跟罗德庆,都通过不同的视角写得清楚明晰。
而在玫瑰的每一段恋爱中,又加插了她身边其他人的恋爱,这种故事结构,如同弦乐四重奏,呈现出一种多层次的美。
黄玫瑰和庄国栋的恋爱期间,哥哥黄振华和苏更生也开始恋爱。
玫瑰和庄国栋的那一段情似乎无疾而终。听说庄国栋结婚,玫瑰失恋。
所以黄振华说,人生苦短,一刹那的欢乐,也就是快乐。第二天马上打电话给苏更生,情绪很罗曼蒂克。
玫瑰的失恋,反而帮助了他认清了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和苏更生之间的情爱开始如火如荼。
谁知结婚前夕,他们到纽约去注册,遇到了玫瑰的新男友方协文。方协文一声贸贸然的“表舅母”,黄振华才知苏更生曾经结过婚。
情海生变。黄振华大失方寸,苏更生却保持着一贯的理性:
她站起来对我说:“我有什么要你原谅的?我有什么对你不起,要你原谅?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不满——太不幸了,你大可以另觅淑女。可是我为什么要你原谅我?你的思想混乱得很——女朋友不是处女身,要经过你伟大的谅解才能继续做人,女朋友结过婚,也得让你开庭审判过——你以为你是谁附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太庞大了!”
这一对是欢喜冤家,终于还是结了婚,但依然有故事,分了又合,合了又分。
玫瑰和博家明相爱时,插入了博家敏和咪咪的婚姻生活。
是博家明先碰到了玫瑰,一见也神魂颠倒,情不自禁。此时他身畔已有一个咪咪。
咪咪是那种喜欢一个人就全心全意,死心塌地,不管受多少委屈的女孩子。博家明移情别恋,她还是包容他。
但玫瑰不爱博家明,爱上的却是他的哥哥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