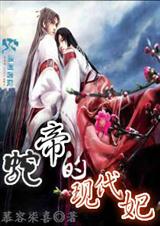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ジτ氚敕饨ò胫趁竦叵质档慕粽殴叵担斫飧鋈擞笥肜诽跫辉市硭斐傻谋纭?刹卧摹度辍返谑碌诙谝约敖诼贾欣主煸频奈恼隆�
(3)试从题材、人物塑造、结构和心理描写等方面,评论《子夜》的艺术特色。
本题和第1、4题有些部分可以互相参照,但应当紧扣着《子夜》来展开分析,而且是偏重小说艺术的分析。谈论题材和结构时要点是“革命现实主义”模式和“史诗性”。人物塑造注重“阶级和时代内涵”的“典型”。心理描写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以及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即从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中刻画心理性格,等等。最好还能分析上述这些特点中可能包含的艺术上的得失。可以参考论文节录中乐黛云和王晓明两篇文章摘引。
(4)试论茅盾小说创作的史诗性特征。
可参考《三十年》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其中有较详细的分析,但不要照搬教科书结论,尽量结合自己阅读茅盾小说的印象与感受,从艺术分析角度去发挥。首先必须明确何谓“史诗性”,它既是一种审美追求,也是一种思维模式,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茅盾小说中“史诗性”的源头来自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以书写历史的视角和方法来进行文学创作是这一潮流的重要特征。茅盾小说的系列性和编年史特征,注重题材和主题的时代性,以及对“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广阔的历史内容”的追求,是讨论“史诗性”的主要论点。应当结合创作实例来谈,除主题和题材外,还可从人物、情节、结构等方面加以评述。如果能把“史诗性”的形成及其影响放到所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并讨论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起落沉浮,可能使论述更具文学史的视野。
【必读作品与文献】
《蚀》
《子夜》
《春蚕》
【评论节录】
茅 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乐黛云:《〈蚀〉与〈子夜〉的比较分析》
王晓明:《潜流与漩涡》
▲茅盾谈《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在我病好了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进行得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我打算从这里下手,给以形象的表现。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当时,他们的“出路”是两条:(一)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二)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
实际上写这本书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开始的。我向来的习惯:冬天夏天不大写作;夏天太热,冬天屋子内生着火炉有点闷人。一九三○年冬整理材料,写下详细大纲,列出人物表,男的女的,资本家工人,……他们各个人的性格,教养以及发展等等,都拟定了。第二步便是按故事一章一章的写下大纲,然后才开始写。当时我的野心很大,打算一方面写农村,另方面写都市。数年来农村经济的破产掀起了农民暴动的浪潮,因为农村的不安定,农村资金便向都市集中。论理这本来可以使都市的工业发展,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农村经济的破产大大地减低了农民的购买力,因而缩小了商品的市场,同时流在都市的资金不但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增添了市场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而是投入投机市场。《子夜》的第三章便是描写这一事态的发端。我原来的计划是打算把这些事态发展下去,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但是在写了前面的三四章以后,夏天便来了。天气特别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书房在三层楼上,尤其热不可耐,只得把工作暂时停顿。
直到“一二八”以后,才把这本小说写完。因为中间停顿了一下,兴趣减低了,勇气也就小了,并且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大,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不写农村了。把都市方面,(一)投机市场的情况;(二)民族资本家的情况;(三)工人阶级的情况,三方面交错起来写。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起来,就不能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面的衬托了。不过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比如同黄色工会斗争等事实,黄色工会几个字是不能提的。
本书为什么要以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呢?这是受了实际材料的束缚,一来因为我对丝厂的情形比较熟习,二来丝厂可以联系农村与都市。一九二八——二九年丝价大跌,因之影响到茧价。都市与农村均遭受到经济的危机。
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他们联接呼应。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抄袭旁人的。巴尔扎克,他起初并不想作什么小说家,他打算做一个书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一个朋友讲好,两个人合办,后来赔了钱,巴尔扎克也得分担一半。但是他没有钱:只得写小说去还债。他和书店订下合同,限期交货。但是因为时间仓促,经常来不及,他便想下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先写一个极简单的大纲,然后再在大纲上去填写补充,这样便能按期交稿,收到稿费。我不比巴尔扎克那样着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样作。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两千字的大纲。
(录自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研究资料》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蚀》与《子夜》的比较分析
事实上,《蚀》不仅没有做到“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恰恰相反,它强烈地表现著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如对孙舞阳、章秋柳这类“时代女性”的同情和偏爱就是一例。作者多次强调这类人物虽然表面上都显得轻率放纵,浮躁浪漫,但实际上“却有一颗细腻温柔的心,一个洁白高超的灵魂”,而且“思想彻底”,“心里有把握”,她们神往于反抗破坏冒险奋斗,醉心于戳穿假面,揭露真相;她们也渴望牺牲自己,做一点有益于别人的事,但她们不知道怎样去做,而且她们不免利己、自私、崇尚感官的享乐,“不愿在尝遍生之快乐的时候就死”,想在“吃尽了人间的享乐的果子之后再干悲壮事”。革命的被叛卖在她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愈的创伤,她们觉得自己受了骗,“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甚至理想的恋爱都是骗人的勾当”,她们不愿“拿着将来的空希望”,“为目前的无聊作辩护”,不愿作渺茫的将来的奴隶而愿执著地粉碎一切现实的束缚,她们声称:“既定的道德标准是没有的,能够使自己愉快的便是道德。”于是恣意追求一己的快意和刺激:“我们正在青春,需要各种刺激,需要心灵的战栗,需要狂欢。刺激对于我们是神圣的、道德的、合理的。”她们憎恶平庸,厌恨周围停滞的生活,她们始终不能和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社会妥协,而且挣扎着不愿在那灰色的生活中沉没。作者说:“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不是革命的女子,然而也不是浅薄的,浪漫的女子,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写的失败。”她们的可爱、可同情,就在于她们奋不顾身地想脱出那几千年来形成的腐败社会秩序,英勇反抗封建统治强加于人民,特别是妇女的道德镣铐(她们的浪漫、追求“性”的解放正是这种反抗的歪曲表现)。她们曾满腔热情地投入伟大的人民革命,革命的失败和她们自身的弱点使她们终于又被抛出革命的轨道,回到原来的旧生活,她们拼命挣扎,虽然并无结果,但毕竟远胜于屈服、苟活、乃至同流合污。“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作者写这一切,决不是用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态度,而是充满了赞赏与同情。
《子夜》也不是只表现作者思想概念而不寄托作者感情的作品。吴荪甫是一个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活生生的形象,而不是什么“本质”的“化身”,作者写《子夜》未必经过一个独立的逻辑思维阶段,这部作品和“四人帮”提倡的“主题先行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茅盾在创造吴荪甫这个人物时,决不是把他作为一个“反动工业资本家”来处理的。相反地,他是在塑造一个失败的英雄,一个主要不是由个人的失误而是由历史和社会条件所必然造成的悲剧的主人公。作者曾对他的命运深感遗憾和惋惜,并激起读者同样的感情。这倒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子夜》发表当年,人们还无须顾忌或回避什么时的真实感觉。例如朱自清就曾说:“吴、屠两人写得太英雄气概了,吴尤其如此,因此引起一部分读者对于他们的同情与偏爱,这怕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的吧。”侍桁称《子夜》为“一本个人悲剧的书”,他说,“这个英雄的失败被写得象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的死亡一般地使人惋惜”。其实作者自己当时也并不隐讳这一点,他在作品中明确地说:这个“魁梧刚毅,紫脸多疱”的人“就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1977年版,90—91页)在作者看来,他正是那一时代英雄传奇的理所当然的主角。正因为这样,《子夜》第一版,扉页上印满了纵横交错的“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一九三○年的中国罗曼司)的图案。是的,不论吴荪甫的主观动机如何,他的愿望是抵抗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实现自己国家的工业化。这正与我国整个民族的历史愿望相吻合。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是一个刚毅顽强、讲求效率,最恨拖沓不中用者的“铁铸的人儿”。无论是才干、人格、气质、风度,他都远远超过粗俗鄙陋的赵伯韬之流,然而他却惨败于后者之手,这不是他本人的过失,而是无法抗拒的社会和历史的必然。从他的败亡,我们也看到了某些比较美好的事物的被毁灭。因此,作者对他的主人公的同情、赞赏、遗憾、惋惜,以及通过这个形象所激发的读者类似的美学感情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当然,这是就他和官僚买办的关系而言,他和工农的关系是另一个问题)。作者显然不是用一个“反动工业资本家”的概念来指导吴荪甫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