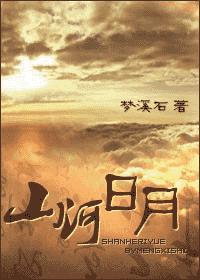昭昭日月-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此恃强凌弱乘人之危真是令她鄙薄。
她灵机一动咳嗽一声惊动了旺儿回身,见是她旺儿忙伸手阻拦:“三小姐不能进,大公子和庶民昭怀对弈,不许人打扰。”
她笑容温然的扶了风吹乱的鬓发说:“驸马老爷到了。”又叹息一声,朗声说给屋里的大哥听,“老爷猜是大公子贪睡不曾起身,执意要亲来给大公子请安。”
她随后递个眼色给珊瑚,示意她速速去报信,一个眼神珊瑚明白究竟,转身就跑。
仆人也觉得情势不对大声向院里嚷:“大爷,老爷就要过来了。”
这才听到一阵仓乱的声音,咣当一声门被踢开,鼻青脸肿狼狈不堪的几人衣衫不整披了长袍,提了罗裤,跌跌撞撞的争先恐后夺路而逃,看似大哥那些狐朋狗友,权贵家的纨绔子。
羞得春晓掩面“呀!”了一声转身,守门的爪牙顿时如鸟兽散。
她立在院里,屋里鸦雀无声,一阵心悸,屋里发生了什么事?
犹豫片刻,她转身想走,却听到大哥一声嚎叫。
忍不住进去看个究竟。
靠窗的竹榻上衣衾狼藉,绫罗衣衫扔得满地零乱,枕头横亘在地,伴随着断裂两截的棍棒,马鞭和麻绳,似是有过一场拼斗搏杀。
雪白一团凝脂夹杂青紫半掩绛罗袍,一阵蠕动,几抹残血的□脊背缓缓抬起又跌落在地,发出痛楚的呻吟,哼哼如猪叫:“昭小三儿,你有种!”
“大哥!”春晓惊叫了迎上,大哥被缚住了双手侧身在地上,赤着膊,下身却是一条令人啼笑皆非的宽大蓝花染布农妇裙,露出两条毛茸茸粗壮的小腿,向角落里缩藏。
春晓惊得心突突的乱跳,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表妹来得可真是巧?”挑衅的声音,含了愤恨,话音在颤抖,是那种听来源自脚下的地动山摇。
她寻声望去,桌案上盘腿坐着锦王昭怀,松松的一件荼白单衫打结在右肋下,露出一段胸颈。落魄中,他呆滞的目光望着手中一柄长剑,拇指食指捏了剑刃细细掠下,一寸寸擦拭着剑锋上的血迹。
“殿下,你的臂……”
他左臂上绸衫撕裂一道口,殷红一片血染单衫,伤口还流血,却毫不在意。
春晓急忙上前要为他包扎伤口,紧行几步靠近桌案时脚下突然一滑,如踩丝帛,身子一晃险些跌倒,定神低头微提罗裙去查看脚下踩到何物,绣鞋旁,黑绒绒密匝匝一团物,光顺亮泽如丝如帛。
渐渐的,她神情凝滞,后背发寒,目瞪口呆。
乌发,一团漆黑的长发散落如滑柔的乌锦,铺陈眼前地上。
一个闪念,她猛然抬头望向桌案上静坐弄剑的昭怀。
他凝神静气的一寸寸轻拭剑锋,目光中掩饰不住失落彷徨,眼中流溢着莹澈的光,一汪寒潭般满是幽凉。
但他脑后那一头为之骄傲的长发已不见踪迹,只剩一截斜齐的断发散在耳后,让她想起大哥用来戏斗的秃尾巴鹌鹑。
春晓周身冰冻一般,牙关打颤,忍不住惊问:“殿下,你脑后的发!”
他默然无语,苦笑侧头,依旧在抚弄那柄长剑,呢喃道:“去问你兄长。”
一跃下了桌案,手中长剑直指墙角蜷缩的明至仁。
“不可!”春晓惊呼去阻拦,一把握住他手持利剑的腕子。
那骨骼都坚硬如铁,青筋暴露,血脉都似要炸裂。
昭怀虚了眼深望她片刻,她频频摇头,却无语以对。
他苦笑,只剩了苦笑,手中利剑狠狠向地上一戳,那奢华的剑铋上镶嵌的红宝石莹光跃动不定,如一颗心摇摆不定。
这剑不是昭怀的。
“滚!”他牙缝中挤出一字,明至仁不及松绑连滚带爬溜走,只在转瞬间,昭怀一把拔起地上的利剑,春晓只喝了声:“住手!”
但见那柄剑已被昭怀不假思索的掷向大哥至仁,一声惨呼,春晓闭眼,旋即是沉寂。
再抬眼,那柄剑深深插入门框,摇摆不定,大哥却瘫软在门槛边。
“大哥还不快跑!”春晓气恼的骂,大哥恍悟过来,爬出门帘外。
“你,你的伤。”春晓撕扯下罗裙一条为昭怀扎伤,他却从她手中缓缓抽出伤痛的胳膊,沉了脸哑声吩咐:“走吧!”
可是他的伤,他的断发,没有什么再比地上散乱如漆的发令她痛心疾首。她曾恨过那五尺长张扬的发,如今看它被斩断时,仿佛一珍贵的名玉被当面打碎。
他红肿着眼,从佛龛长明灯前取来火种,蹲身松手,一阵焦糊味道扑鼻,嗤啦啦火光一闪而过,青灰满眼。
没了,就如此断了,了了,没了。
春晓心头的惆怅失落远不逊于昭怀,她不知如何去安慰他,而昭怀俯身坐地无语时,脑后那齐齐的短发就在她眼前晃动,令她心里一种难言的痛,一下下,如针在刺扎。
“是我大哥做的?”她哆嗦声音问。
“不!不是他。”
“那是谁?”
他苦笑摇头,旋即是冷冷的惨然,抬脸看她,那神色真是冷冰冰的看来陌生。
“断了好,断了,就绝了念想,脑后从未如此轻松。”
朝阳满院的窗外,鸟鸣清幽,生机盎然,只他这里枯木难逢春。
父皇,一切都拜父皇所赐,他不如一头狗,被践踏得毫无尊严,他是什么皇子?他如今是庶民,比庶民都不如的奴仆?
他苦笑,心里只剩了恨意,他在那冰冷冷的京城唯一能依靠的家,唯一的父亲,竟然陌如路人。如果生在贫民小户,也不至如此。
他的头埋下,藏在臂弯间,后背起伏不平,却极力掩饰失落伤悲。那曾高贵如主人一般的长发,一去不归。静静的,没有声音。
那伤感油然而生,揪扯心怀,她情不自禁伸出手,缓缓探出,犹豫片刻,却忍不住去抚摸他脑后的断发。那残缺的发松柔,预示着它的主人应是个性格温顺的人,她忍不住缓缓拍哄他,如拍哄自己的小弟弟妙儿。
纤纤青葱撩开鬓旁乱发,尝试去为他拭去腮边的泪,他却一把揽住她的臂,只枕在冰凉湿滑的颊旁,隐隐啜泣。她安详的抚弄他的发,徐徐的,想给无助的他一丝安抚。
他去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她的心一慌,但那束缚紧迫得不容她挣脱,而那炽热的头就紧紧贴在她身上,不知不觉中,感受他的悲哀。
空气凝滞,那悲哀仿佛侵袭进她的胸臆,眼泪也倏然流出,潸潸流淌,仿佛那断发之人是她自己。
他终于从她怀里挣扎起身,侧头掩泪,咬咬牙,羞惭道:“让表妹见笑了。”
而她反是一阵尴尬,窘然陪笑,无语以对。
呜呜的呻吟声来自外室,被捆扎如粽子口堵巾帕的小太监如意在桌下角落奋力做声。
扯开堵嘴的帕子,如意哇的一声大哭失声:“殿下,殿下,我们去寻皇上做主!”
“寻谁个?”昭怀惨然问,目光呆滞。
“皇……皇上……”如意的声音渐渐没了底气,只剩哭泣。
明至仁的咆哮又浮现耳边,一**,如海浪呼啸奔来再戏逐退去:“昭怀,你以为你是什么?我二舅小妾生的个家生奴才,还拿自己当殿下了?不知自身斤两就这个下场,让你看清自己是什么货色!”
他闭上眼,泪水汹涌,极力将这些污言秽语关拦在心门外。
小如意惶然问:“殿下,大公子他们可曾打伤了你的筋骨?”
明驸马和长公主果然来到天都峰别院,陪了福安老太夫人姗姗而来。
至仁扶了昭怀踉踉跄跄出现时,众人都惊得瞠目结舌。
明至仁脸上一块破皮的青紫,昭怀却是一瘸一拐手臂缠满白绫扎着伤口。
明驸马大惊失色问:“你们两个,这是……这是如何搞得这般模样?”
昭怀谈笑自若道:“郊外,路遇无赖,幸好大表兄搭救。”
明至仁频频点头如鸡啄碎米,没有再多言语,神色恍惚。
“殿下,你的头发!”福安老夫人一声惊叫,身子晃动几下险些昏厥。
她颤抖着手指了昭怀,昭怀脑后发髻勉强挽个髻在头顶,参差不齐不及肩长的一头碎发,原本五尺长如瀑布般流逸的乌发无影无踪。
惊得明驸马和公主愕然无语,许久才惊喝一声问:“头发哪里去了?”
昭怀不耐烦般抿嘴一提眉头含糊道:“不过被几个泼皮无赖斩断了头发,又不是斩断了命根子。”
“三儿!”长公主暴怒:“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明白你父皇如何看中它。这是掉脑袋的罪过!谁干的?”
“断发还能再长,父皇再见昭怀猴年马月了。几个泼皮无赖,昭怀已经教训过了。”昭怀嘟哝着,满不在乎。
明驸马咽口气,将信将疑追问至仁:“老大,这是怎么回事?”
“儿子哪里知道,三殿下在凤州上上下下得罪这许多人,恨不得将他食肉扒骨的不计其数,谁知他连无赖都得罪上。儿子又不是三表弟贴身小厮,处处跟去伺候他。”至仁懒洋洋的语气没有声调。
“是谁放三殿下出府的?”明驸马一声怒骂,目光扫视半周,仆人们慌得周身战栗。
“是昭怀的不是,一意孤行出了府,怨不得旁人。”昭怀随口应着,早已近前几步贴在福安老夫人怀里,仰头含笑细心宽慰安哄着痛哭流涕的老夫人。
只是福安老夫人看他一眼,就侧头落泪,不忍再回头看时,又不禁眼泪婆娑,一发难控。
“奶娘不必伤心了,麟儿的话也没大错,头发断了不能续,养几年就好。只是这消息绝不许传去皇上耳边。”
长公主转向在场众人喝令:“若是谁个长舌多言,定不轻饶!”
福安老夫人哆嗦着手抚弄那几绺断发,触及时如烫扎般又收手,泪就不曾断,自言自语叹气:“父子冤孽呀,冤孽,该不会真被隐太子不幸言中?”
“奶娘!”长公主惊得制止,目光中都含了隐隐的恐惧,昭怀好奇的目光仰视福安老夫人,福安老夫人避开他的目光。抚弄他的面颊道:“皇上最是疼哥儿,罚哥儿在这里不过是敛敛哥儿的性子,待皇上气消了,自然接你回京的。”
昭怀却扮出一脸灿烂的笑,深抿了唇带了几分羞怯道:“老寿星,昭怀不想回京城,凤州真是山清水秀,孙儿在此得了一座田庄,这几日同晚秋妹妹教了农户在种胡瓜,那些大旱干涸的土地引来河里的水可以种地,待收成时一定让老寿星亲口尝尝麟儿亲手种的胡瓜。”
昭怀认真的样子还带了几分稚气,福安老夫人的泪水不停,拍哄了他嗔怪:“哥儿还安了心一定要做个庄稼汉吗?”
“没有春种一粒黍,秋收万颗子的农户,哪里有父皇的万里江山?庙堂之上指点江山是为父皇尽忠,辛勤耕耘田间也是对父皇尽孝呀。”
长公主扫视他一眼冷笑,翕翕鼻子骂:“就属他鬼大,奶娘你也信他的鬼话?”
明驸马却是不发一言,沉了脸打量昭怀,目光又迅忽如箭射在鼻青脸肿的儿子至仁身上。
至仁慌得避开父亲的眼色,掩藏心里的局促不安。
番外免费赠送《麟儿》
应各位亲的要求,奉上一小段麟儿的番外,博大家一笑。
瑞脑香清凉之气润肺,长公主在绣榻上观看荣妃为皇上亲手绣的龙袍,评点着线脚针法,却听内侍通禀:“皇上驾到。”
众人起身迎驾,也不曾留意床榻上玩耍的小麟儿。
“哎呀”一声惨叫,迎了皇上进殿的众人听到三殿下一声惨叫,快步敢来。
床榻上麟儿揉着屁股翘了小嘴立着,围着猩红的如意肚兜,露出白嫩如藕节的腿臂,他撇撇嘴,委屈的哽咽:“父皇……针扎到麟儿。”欲哭又强忍下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