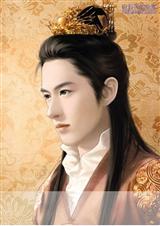民国铁树花-第1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救命的声音,以为发生了意外,顺着声音奔进白敬斋的房间,只见老爷蹲在三姨太胯下手里拿了根针在扎她,三姨太剧烈的挣扎着,他不由自主心疼地喊了声音:“老爷……”
124。主仆之争,三姨太出走
白敬斋正聚精会神猛听背后管家在喊他,骂道:“小赤佬,想吓死老子啊?你来干什么,滚滚滚!”他张开双臂试图挡住三姨太赤条条的身体,三姨太在他背后又哭又跳,就如一串腊肉在风口挂着,手臂伸展到了极致夹着那张惊怵的脸,向管家求救:“疼死我啦,管家救救我。”
管家站着没走,想要保护他喜欢的女人又不敢违抗主人,他只听过三姨太控诉白敬斋弄女人的毒辣手段,没有亲眼见识过,这回三姨太触目惊心的被主人用针在刺下身心疼不已,战战兢兢说;“老爷,您就放了三姨太吧,她这是犯了什么大错,好歹也跟了你十多年,这般残酷她怎么受得了?”管家一向察言观色,对白敬斋惟命是从,现在居然敢顶嘴,三姨太光着身子也不回避,白敬斋怒不可遏,呵斥道:“你想造反啊,敢乘机看我女人的身体?小心把你解雇了,快滚。”管家听要解雇他,怯生生地转身要退出去,三姨太实在忍受不住白敬斋没有人性的折磨,豁出去了,大声道:“管家,你不是男人,口口声声说喜欢我,你喜欢的女人被人摧残还无动于衷?快救我,我答应跟你远走高飞。”三姨太把宝押在了管家身上,她不怕了,死的念头都有。
管家楞了楞,前几天他们还在说离开白府的事儿,三姨太犹豫不决,说:“我跟你走,你却没有个象样的地方让我住。”管家说;“我这些年积攒了不少钱,完全有能力租个房住,以我多年管家的经验和资历找个大户人家重操旧业不是难事。”三姨太一直担心自己曾经被人轮 奸和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遭遇,是男人都会忌惮,问:“你了解我的过去,现在说得好听,等玩腻了就要嫌弃我的不干净了。”管家再三保证,他是真心的,自己的条件能够得到大老板姨太太的青睐那是万幸。
白敬斋听出了味道,瞪起眼珠问:“什么什么,你们早就有奸情在商量逃跑?”说着转身捏住三姨太下体,恶狠狠的使劲,那绣花针本来就那扎着一下刺得更深,三姨太的惨叫声惊天动地,撕破了喉咙,管家冲过去推开白敬斋道:“我不许你这样对待她。”
力量大了点,白敬斋踩到躺椅的脚身体失去平衡跌倒在地,骂道:“你这个下人敢动手打主人?我看你不想活了。”抓起桌上的饭碗过去砸管家,他六十七岁的人哪是管家的对手,躲开后顺势脚一拌白敬斋又倒在地上,管家膝盖顶住他肚子,拳头雨点般往他脸上抡去,嘴里骂道:“我叫你欺负三姨太,你他妈的老棺材,我忍你很久了。”
白敬斋如泄了气的皮球,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能向下人求饶:“管家别打我,别打我,我认输认输。”
门外有几个女佣探头看到这情景,头缩回来都不敢吱声,更不敢贸然进去救老爷,看管家这劲头,谁进去说不定一块挨揍,这个管家平时对别的下人动不动训斥,对女佣人不管好看难看走过去捋一下占便宜是经常发生的,女佣们见他是老爷的红人惹不起,都躲着他,这种事情最好谁也没有看见,少惹为妙。
三姨太这厢还吊着喊管家把她放下,管家收住拳头对白敬斋说:“躺在地上不许动,别让我杀你。”白敬斋鼻青眼肿的忙说:“我不动,我不动。”就像街头斗殴的小流氓,一方被打得服服帖贴的,这回眼睁睁的看自己的女人让管家身体上摸来摸去,乳头上绣花针拔掉时,三姨太一惊一乍的带着半分的忸怩,管家嘴上去替她含住冒血珠的伤口,三姨太很享受的抱住他后脑说:“你真行,这疼硬是被你弄得痒飕飕的,还有下面你也这般跟只猫似的。”白敬斋看了真想挖了自己眼睛。
管家催她穿好衣服说:“你去收拾收拾我们赶紧走吧。”三姨太说:“我去自己房里拿首饰和钱,你把这老东西扒光衣服跟我一样吊起来。”她走出房间时门口的女佣全部四处逃开,跟看到鬼似的,三姨太一点也没发现,径直去自己房间,这些年她积攒不少的钱,有部分还是当年二太太走时遗留下归了她,都押着箱底,她不喜欢放银行,认为不安全,而且放别的银行于老爷的面上过不去,放自家的宝顺洋行似乎觉得还是老爷的钱,哪天一不高兴就不让她取了。
管家打顺了手,蹲在地上连抽了白敬斋几个巴掌,问:“你是自己脱,还是我动手?”白敬斋怕是被打得伤了元气,从来没有遭受过这份罪,讨饶说:“哇哇哇,你不要再打我了,我自己来。”
白敬斋很配合,脱光了衣服自己站在悬着的绳子底下,两手腕合在一切,被绑后自觉踮着脚尖双臂举起,可是他有肩周炎手臂弯曲着举到耳朵这再也上不去了,管家年轻时干过粗活力气大,抓住另段绳子往后拉纤似的一使劲,白敬斋的肩胛骨嘎巴一声瞬间双脚悬空,疼得嗷嗷叫:“哎呀,我的骨头断啦,求求你让我脚踩踩地好不好?”管家说:“老爷,不是下人要这样对待您,怪只怪您刚才对三姨太忒狠了,您就忍着点吧,我去自己窝里整理行李去。”白敬斋感觉自己笨重的身体渐渐往下坠,手臂已经脱臼,哭喊道:“你是我老爷,可怜可怜我这老头子吧。”
管家去自己房间拿行李,两人磨蹭了些时间后各自拖着一只大箱子放客厅里,回头望院子里静得跟往常别无二致,管家说;“我已经把他吊好了,他不会追出来,我们走吧。”三姨太既然决定离开就不会轻易饶过白敬斋,十几年里被他的轻慢与折磨这一刻她要全部还给他。
她冲进房间,白敬斋就像只褪了毛的猪猡挂在屠宰场里,说:“我要以牙还牙。”拿起地上的两根绣花针在他面前扬了扬又问,“你想知道被扎的滋味吗?”
“不,不想。”白敬斋直摇头。
三姨太太得意地问:“刚才你在扎我时的那副满足表情哪去啦?”白敬斋求饶:“三姨太,三姨太,看在我们十多年的夫妻感情你就放过我吧,我这么大年纪禁不住这等折磨的,你,你放了我,我对你既往不咎。”三姨太啐了他口说:“呸,你还对我既往不咎,看我不弄死你。”白敬斋了解这个女人十多年里一心想当正房,便说:“三姨太,只要你放下我,我们马上去结婚,你不是要当正房太太吗?等结婚了,我白敬斋全部的钱都是你的了,我死后你就是上海滩的老板了,好不好?”他望了望门口管家没有进来,低声说,“总比跟着那个穷瘪三流落街头要强啊。”
三姨太不会相信他的谎言,冷笑道:“你想让我当第二个二太太吗?是你雇癜大爷把她和老宁波杀掉的吧?你的那些事我全知道,相反老娘的事你一件也不知道,现在可以向你坦白了。”三姨太不仅要在肉体上折磨他,还要在心理上让这个死要面子的男人窝心一辈子,她回忆起来:“五年前,我与郝小姐的争斗中被她蒙着眼睛捆在床上,你知道谁轮 奸了我吗?是你的家丁,十几个人哪,可以说白府几乎所有男人都糟蹋过我,结果我怀孕了,我不知道谁将是孩子的爹,可能那十几个全是吧?唯一不可能的人是你,是老天让你白家绝子绝孙,哈哈哈。”
白敬斋气得要去踢她,腿一动手臂关节就像刀在刮他骨头,嘴里骂道:“你这贱人啊。”
三姨太似乎认为刺激得还不够,接着说:“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怕被你发现,我去找你认识的那个朱伯鸿老板,我陪他睡觉,他帮我找人打胎,打胎的老军医也玩了你的女人,后来,我为了让轮 奸我的家丁保守秘密,委身给了他,让去摆平他们,可以这么说吧,我与管家睡了至少四年,你白天在上班,我在他房间里让他享受主人的姨太太,没看出来吧,蠢猪?你眼里只知道那个姓郝的,现在人家也抛弃了你,想想吧,为什么你的两个太太都与人有奸情?”
白敬斋被羞辱得嚎啕大哭,哀号道:“我白某前世作了什么孽啊,正是奇耻大辱……”
三姨太得意地道:“先别急着哭,尝尝美妙的滋味吧。”白敬斋收住哭声杀猪般喊道:“不要,不要,三姨太不要啊。”三姨太满脸微笑一根绣花针往他绿豆大的乳头平静的穿进去,白敬斋浑身发抖,绳子带着他左右摇晃,手臂疼得麻木了。三姨太很满意,从心底里释放出强烈的快感,举起另外一根放在他眼前说:“还有一根,你说扎哪儿?快求我,快,叫我主人,哈哈哈。”白敬斋乖乖的喊道:“主人饶了老奴……”
三姨太笑得前仰后合,一副胜利者的状态,拍了拍他红肿的脸说:“你现在知道后悔了?我向你求饶时,你不是反而变本加厉的摧残我的吗?好,让我来学学你。”
管家总担心白敬斋这一惊一乍的会被其他人听见去报警,所以在跑到大门口明着与看门的闲聊着,实际上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白府这条小路的尽头,如果有警察来很远就可以看见,如遇意外可以从白府的后面逃,警察来这也是家事,万一弄出人命就是刑事犯了,他回到房间里催促道:“三姨太,差不多就可以了,别到警察来了我们走不脱掉啊。”
白敬斋听到警察二字本能的大喊道:“警察救命!”三姨太拣起地上的小裤衩往他塞进去,说:“讨厌,闭嘴吧你,让我好好的爱抚爱抚你。”说着玩世不恭的捧起他的胯下物,软绵绵的早缩了一点点,她拉了拉,白敬斋知道她的意图嘴被堵住想求饶也没机会了,眼睛直盯着她手上的绣花针,三姨太聚精会神的找位置扎,白敬斋吊着躲来躲去,管家看了也心惊胆战,暗想这女人可真够狠的,平时没看出来,也盯着针,整个房间仿佛被一种可以预见又无法准确去感受的恐怖气氛所笼罩,白敬斋和管都提了个心,三姨太神情淡然的样子蹲下身,绣花针以最慢的速度刺了进去,针尖从另一头穿出,白敬斋“啊”的一声昏厥过去。
白府的院子很深,门口的守卫听不见里面的声音,见三姨太和管家两人拖着行李箱子出来,欠身打招呼:“三姨太、管家,你们这是出远门啊?”管家装腔作势训斥道:“胡说,我这个下人如何跟女主人结伴出远门,成何体统?三姨太有两箱子私货送给别人,我是保驾。”门卫拎不清,问:“那老爷不是有车嘛。”三姨太镇定地说:“老爷一会要出去,别多管闲事,这不是你下人可以问的。”
两人大马路上叫了黄包车直接去火车站,至于去哪里路上商量。
他们走了,房间里一片寂静,白敬斋醒来,疼痛已渐渐适应,几个刚才逃走的女佣轻手轻脚不约而同的回到客厅里,大家面面相觑,一人问:“人走了?”另一个说:“大概是的,我看见他们拎着大箱子走的,看来是私奔了,三姨太跟管家早就有奸情了,你们不知道吧?”那人先是颇有些得意道出了秘密,又打打嘴说,“当我什么也没说啊。”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妈子是白府最早的下人,二十多岁时就来了白府,那时这院房还刚刚造好,白敬斋的大太太还在世,她是老爷的贴身丫鬟,受宠过,现在老了,被发配到厨房负责买菜洗菜,一般她不会出现在客厅,这是白府的规矩,每个下人都有自己活动区域,刚才是一名女佣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