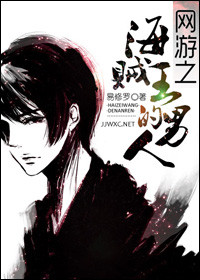说谎的男孩与坏掉的女孩-第9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也没达观到去劝他说那是自费力气。
所以我偶尔窥看伏见的脸色,并选择在这个情势下闭口静观。
唯一成立的感想就是他大概会命令洁先生或菜种小姐打扫吧。
不过多久时间,那对夫妇也回来报告试验失败。
唯一多花了一点时间的,就是所有的人终于实际理解了自己目前置身的立场一事。
以上,尚未褪色的回想结束。
而在我上映这段过去的期间,现实仍在持续进行。
丢下说了一句「俺去一下厕所」就走进通道上空房间的茜,剩下八个人前往确定杀害景子太太的凶器是否还在。顺着客厅的正面通这走到底,然后不是朝看得见陈尸处的左手边,而是往右手边转。在尽头的墙壁两边角落,分别摆了一个看似放置扫除用具的破旧置物柜,以及一个乳白色的保险箱。到底是怎么个搭配法啊?是把湿抹布锁在保险柜里面,还是这家人自有独特的打扫方式?
耕造先生领头打开保险箱的开关,漫不经心地输入四个数字。1OO6啊会是十月六日的意思吗?我这个外人想破头也不可能想出这密码代表什么意思,不过以他这种粗枝大叶的密码管理方式来看,如果是长年住在这屋子里的大江家人,说不定有办法打开保险箱的锁。
耕造先生取出一把古老的黑色左轮手枪,将手枪摊在众人面前。感觉很像是一把才发了三发子弹,生涯就告终的玩具手枪。
但前提是玩具手枪得要发射得出超越音速的子弹。
耕造先生不知为何,以一副「枪不是还在吗」的表现把手枪秀给我们看,接着调查里面的子弹数量。
「弹夹里还剩下三发。总共可以装六发,所以刚好用掉一半吧。犯人从那扇窗户射击景子,然后把手枪放回保险柜才离开现场的吧。」
耕造先生得意洋洋地展现构不成说明的对话。
「总共有三声枪响,该不会两发射偏了吧?」
桃花质疑。耕造先生回答,「或者是,为了谨慎起见,多给了她致命一击。」这个人也真是的,太太都被人杀害了,这态度也未免太冷静了吧?或者该说是冷淡?说不定他们夫妇之间的关系不像南瓜,而是像青椒不,问题不只出在两人之间的关系。桃花或茜也没发出一声悲叹,对于家里出现尸体这档事,也没表现出乱了阵脚的模样,从她们的态度,感觉她们家人之间带有点距离感。这是否证明这家人之间的交流并不像电力系统般润滑、顺畅而毫无阻碍呢?
这么一来,就算亲人之中出现杀人案的被害者与加害者,也不会觉得不自然或感到遗憾了。
「这把手枪怎么样?就交给我保管吧?」
耕造先生用客气的口吻提出这个无理要求,听者全都默不作声,只以鄙视的视线送出响应。
「这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东西。」他补上构不成理由的借口。
「怎么可能答应啊!」众人以桃花的意见做出总结,对耕遥先生的建议嗤之以鼻。
就算他是这房子的主人,看来他也没有可以抵抗八人反对意见的权力和胆量。
耕造先生搞了一身腥后,心不甘情不愿地把手枪放回原处。
(或许)夺取了人命的道具,被收回按键式的保险箱里。
姑且不论个人管理的问题,在场没有人举手提议要把枪毁掉。
就算这把手枪是凶器,开枪的犯人就在我们这群人之中的可能性极高,也没人提议这么做。
说得也是。
如果没有不见一把刀,或许会有人提议要破坏这一把枪。
手枪比剑来得厉害,开枪比冒着被枪打的风险来得安全。
手枪在他人手里可是件凶器。
但在自己手里,就变成可靠的武器。
我们边营造出有些异样的空气,边走回餐厅。
「咦?你们把我丢下,自己先跑去?」不合时宜地表达不满的茜也回来了,九人再次展开动口不动脑的会议。
周遭并没有其它住户,农田也被贾地和出售屋取代,无法寄望从窗户发出精神饱满的喊叫,向其它百姓要求救援。而且也很难预估外面有谁会担心这些看来不需要电话、没有朋友的大江家人。伏见她似乎也没写下字条告知去处,换句话说,我们在这种内陆土地上,面临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只要具备那道高耸围墙,就算万一有人经过房子前,也没办法看到景子太太的尸体吧。
这样子就像进了一人独居的公寓里的厕所,结果门因为地震而卡死打不开的封锁状况吧。势必要早点脱离这困境,以免因封锁而断绝粮食供应,演变成残酷地夺取生命的要因。
「吃的东西我想让菜种管理,反正我们没有人会做菜,这件事就交给能有效运用的人吧。」
于耕造先生的提议,这次并没有出现异议,所以我才心想要不要让伏见成为后补人选。结果瞥了明显变乖巧的邻人一眼,看到她正低头互相搓磨着两个大拇指,就算视线和我对上也只是摇头,宛如从没参加方才的对话。她摇头是想要拒绝什么。
「嗯嗯是的,我会努力的。」
菜种小姐稍微缩短语尾的拖长音,接下了这个任务,她重复点头的速度也比昨天快。于是耕造先生把厨房的钥匙交给菜种小姐。
「可是啊,犯人为什么要破坏玄关?」
桃花无力地低语,好似不期待得到任何响应。隔壁的茜听了,「唔嗯」地环抱双臂思考,所有人都盯着她,期待她能说出什么好答案。
不久后,茜果然给了个好答案。
「为了让我们无法进出。」
「我想也是。」桃花无法接受地用手撑着额头。
假若景子太太是被枪打中,那么窗户上的削痕就是子弹掠过的痕迹,而房内墙壁上没有卡着子弹或受损,代表那是从屋内发射的。
换句话说,杀人犯也被关在房子里。
只不过,杀害景子太太和破坏玄关的犯人是否为同一人,到现在还不清楚。
但如果犯人在我们之中,应该就是在发射会产生极大音量的手枪前,便先将门破坏的吧。
不让出主导地位的耕造先生又拉回话题提议:
「等一下要回房的举手,不好意思,我要把房门锁上。」
他用手指勾起桌上那只串着钥匙的铜环。
「剩下的人看着我锁门,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安全你觉得还会有人被杀?」
桃花插嘴。耕造先生带着「妳是在乐天个什么劲」的语气劝告他的女儿,「是有那个可能性吧。」桃花大概无法当个没经验的旁观者,主动做出反驳。
「那锁上的钥匙要给谁保管?」她变成更加挑衅、彻底叛逆的女儿。
「喔喔由我保管。」
「爸,你还没学够教训吗?」
桃花先行制止父亲的主导权、自尊心及立场,狠狠瞪着他,以让他不敢再说第二句话的气势镇压他。
耕造先生隐隐啧了个舌,将他正要说出口的「那当然」吞回肚子里。
「交给其它人保管,由当事人自己指名。」
耕造先生用放弃的口吻,迅速说明该如何处置。这种场合下,哪有我能托付钥匙的人啊?我自己房间的钥匙该怎么办呢?
「那快点决定要不要回房间吧。」
耕造先生逼迫众人做出各自的决定。这时伏见以视线寻求我的意见。要伏见她自己决定这件事,很残酷吗?尸体似乎为她带来寒气和颤抖。
「我要在房子里稍微逛逛,妳要一起来吗?」
我才说到一半伏见就点头,总共让头上下晃动四次左右。
结果举手的是汤女和持续默祷、保持沉默的贵弘。
除了举手的两人,这结果让大江家的居民都感到惊讶,尤其是耕造先生。
「贵弘,你要回房间?」
「是的。」
贵弘不动摇也不慌张地向父亲表达坚决的意志,不知大江家的人有没有看出他怪异的行为。
如果他只听从双亲的命令,那么应该不会自发性地采取行动才是。
「不行,你得和我一起调查这房子。」
耕造先生命令贵弘的意愿应由他来管理,但是
「我拒绝。以这种状况,接下来我不能只听你的命令。」
贵弘贯彻自立与反抗期,平静地抛开昨天的忠犬姿态。
耕造先生张大的嘴巴,因舌头饰演着不断打颤的爬虫类而无法阖上。
圾夫妻只是瞪大眼睛看着少爷的急速成长。
桃花也因哥哥的态度睁圆了眼,茜则做出「哦?」的暧昧反应。
而当事人贵弘对谁都保持中立,接着再次闭上眼睛。
「你是怎么了?今天很怪喔!」耕造先生对儿子的成长表达极不爽快的异议。
「不如道,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贵弘始终以和式淡雅风味带过话题。
「」
由站在客观立场的我看来,很难察觉到底有多么不寻常。
人会改变这种小事,有什么好不可思议的?
环境改变,精神也跟着一变。
看来这个家的主人还没有自觉,这房子已经朝异常的方向踏出十步了。
就这样,众人丝毫不努力修复崩解的调和,反而依照各自的想法开始活动。我本想对伏见说这感觉挺像放学后的社团活动,却被她的严肃表情阻拦。
洁先生和耕造先生休息一会儿后,为了找寻逃生口而在屋内东奔西跑,但我觉得要使用强硬手段逃离是很困难的,不然犯人不会只破坏玄关就满足了。犯人应该是想让大家都逃不掉,在一夜之间杀害所有人,这么一来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大门对犯人来说应该也不成问题。
汤女说要回自己的房间,于是在她进房后,我们从外面将房门上锁。汤女依照规定,列席见证上锁的八人之一,在那之后指名我为保管她房门钥匙的人。我为了参加信任扮家家酒的游戏接下钥匙,取得同意后将汤女反锁在房内。
「为什么是这家伙,这样真的好吗?」耕造先生以感情论事,不经思考地责备女儿的选择,但汤女露出以妖艳为目标航向远洋的表皮,硬是决定要这么做。
贵弘依照他叛逆期般的宣言将自己关进他的房间,钥匙交给茜保管。菜种小姐前去准备饭菜,桃花跟茜则两人去了餐厅。
而我和伏见现正在屋内彷徨徘徊,找看看地上有没有掉面包或饭团。
骗你的。
打从发现景子太太的尸体后,伏见就没离开过我身边,反倒是紧抓着我的衣服袖口死搂着我。是因为近距离看到尸体而感到害怕,还是为了被枪射击时我能兼当墙壁挡子弹才选上我?我想应该是这其中一个吧。
这次我没准备酱徽,我也怀疑自己能不能在枪战中生存下来。虽然我这个人彻头彻尾都是个谎言,但我还是接受伏见十分不安的事实,不干涉她举猴子和我玩紧黏在一起的游戏。
在这没什么好欣赏的旅途中,我们俩在做什么呢?我们只是在悠闲地乱晃。麻由的事是让我的肌肤吵闹得直起鸡皮疙瘩的原因。为了忍耐,我只好驱使静不下来的脚底,以发泄想跳跃的冲动。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她身边啊?
由至今的倾向看来,空房间里不存在我要找的东西。我为了宝箱被乱藏一事感到愤慨,再加上探索没个性的空间只是浪费时间,因此中止这种行动,改变策略方针,决定卧薪尝胆地(预定如此)等待能探索有人住的房间的机会。因此,时间便从竞争对手沦落为惹人厌的混帐。总之就是没事干。事情没有明确的段落,也看不到解决的方法或日期。对于我来说,死亡的感性早就被污垢与鲜血的肉冻包裹而无法运作,这就像是要我做卷白纸的工作一样无趣。比起杀人事件,麻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