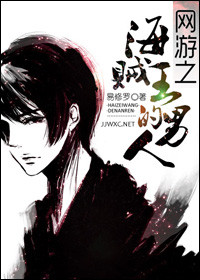说谎的男孩与坏掉的女孩-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长濑同学?」「不是啦。」「透?」「现在不是啦。」
长濑蠕动嘴唇说着约定两字。啊,我懂了我懂了。
「你脸色很差耶。」
「突,突然不太舒服。」
长濑把手掌往裙子上擦了擦,步伐不太灵活地绕到病床旁。就在此时她似乎发现正把我的手当抱枕睡觉的麻由,眨眼的速度突然提升不少,而被麻由压着的我也冷汗直流。如果麻由现在醒来,要我的命可能比踩扁路边杂草还简单。
「去外面聊吧!」
我这么提议后,不等待长濑回应就直接起身准备外出。我放下漫画并谨慎地移开麻由的手脚后拿起丁字拐,在左脚套上比脚大上一号的超大拖鞋,穿上一点屁用也没有的防寒外套,几乎以竞走的气势火速离开病房。在病房门口回头朝房内一看,看到把棉被当挚友的度会先生脸上浮现茫然以及没有恶意的惊讶目送我们离开,似乎是被我的女性关系吓到了。骗你的。好,我终于渐渐恢复了平静。
长濑毫不匆忙、轻轻松松地跟在我身旁。
「我不赶时间啦。」
客观地看着我慌张的样子,反而让她更加冷静,从声音都可以听出她的从容。
「你以为是谁害我这样的。」
「我不认为是我害的啦。」
她丢了个落落大方的回答给我。我只撇了她一眼,什么也没回答。
「不过,如果要出去外面谈,我原本还期待你是不是至少会借我一件上衣御寒哩。」
长濑表里如一的失望语句里暗藏些许恶意。
不过我不管是意识、情绪或脑袋都没有反应,情感也是。
「喔?怎么一副难为情的表情。我只是来探病,要你担心我还真是不好意思啦。」
就是啊!如果你今天有乖乖上学,难道不会自己准备上下学穿的保暖衣物吗?我在内心悄悄精制了一杯加入一匙恶意的吐槽。
走到走廊尽头的楼梯时,我烦恼着该往上还是往下。最后做出的结论是往上或下并没有太大差别,因此决定上顶楼。不知道是担心还是因为看不下去撑着丁字拐的我每爬一阶都得花上一点时间,长濑展现亲切的态度问道「要不要我帮忙?」但是我慎重地加以拒绝,不过通往顶楼的门是长濑开的。
这是我在住院生活期间第二次上顶楼。这个医院占地中最接近宇宙的地方,有萧条的黄绿色长椅和大量洗好的衣物曝晒在冷风中,而现在又多了两个人一起曝晒在冷风里。虽然头顶上是一片晴朗无云的青空配上一轮太阳,降下的却是让人全身发抖的寒气。这里除了我们之外当然没其他人,所以这样正好。
「好冷啦。」
长濑吸着鼻涕诉说她的不满,裙子底下的大腿紧紧黏在一起。
「不能去咖啡厅吗?就算只给我水,我也愿意忍耐啦。」
「不行,要是被朋友知道,脸就丢大了。」
「你是刚进入思春期的国中生吗……」
长濑有些不悦地放弃这个念头,和我比邻坐在长椅上。长椅支撑两人的重量,夸张地吱吱作响,长濑的屁股坐下时发出的声响比较大,应该是我的幻听吧?
我深吸了一口气,让肺部充满宛如含有冰粒的寒冷空气,努力把堆积在体内如恶脓般的劳累全吐出来。我重复几次这样的动作后,僵硬的四肢回到放松的状态。
长濑看到我恢复冷静,于是开口:
「看到透没事就好了。」
长濑透都叫我「透」,而妹妹长濑一树也学姊姊叫我「透」。从我们开始玩起交换名字的游戏到现在,她们似乎都没改变这个习惯。
××和透,这不适合彼此的名字,是打破僵局的关键。
「你听一树说的?」
「嗯」,长濑点头。
长濑的妹妹长濑一树(这家伙很喜欢自己的名字)是这间医院的常客,不过她并不是一个身体虚弱的小孩。她学习多种运动以及空手道等,所以经常在练习中骨折或扭伤,现在也为了治疗左手伤势而住院。因为我们彼此认识,所以我住院后也和她见过好几次面。
明年就升五年级,所以和浩太同年。
那两个孩子不知道有没有开心地上学?
「对了,你是怎么受伤的呀?」
长濑看着随风飘扬的床单和毛巾发问。
「我想空手打破夜晚校舍的玻璃却失败,连脚也踩到玻璃碎片。」
「逊毙了——」
那是一点也不相信,毫不亲切的冷淡语气。
微风迎面吹来,长濑身上的香水味让我的鼻子微微发痒。
「那么,找我什么事?」
干燥粗糙的嘴唇和紧缩的喉咙阻碍我发出声音,这句话不知道有没有被风吹散,有没有好好传到她耳里呢?
「什么事?我只是来探望你的啦。」
长濑不争强也不畏缩,只是这样回答我。
「现在这个时候才来?」
「现在才来?透好像是一个多月前住院的吧,我太晚来了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指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啦。」
只有我一个人感到尴尬吗?
「一年左右……」「一年一个月又十二天。」长濑有严守正确的怪毛病,一找到机会就要纠正我。「……应该有隔那这么久没见了吧?甚至都已经没有通简讯或电话,完全断绝联系的你竟然突然出现在这里,我当然会起疑心啊。」
「是喔,你希望我打电话给你?」
长濑似乎觉得很有趣的观察着我的表情,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还喜欢长濑的时候或许是这么想过。」
要是现在让麻由的水果刀刀尖从苹果转移到我身上,那我受这些伤的意义不就没了?也没脸站在对我伸出援手的妹妹的母亲面前。我对身为阿道的意义、命运以及必定的偶然所做出的大吹大擂也会难以收拾,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说谎。
开朗的神情从长濑的脸上流逝,我不禁想到这是不是就是人际关系所谓的「踩到地雷」,我十分担心地雷会不会爆炸。
不过长濑却只是用低声,但不是自言自语的音调呢喃着「用的全都是过去式吗?」表面上地雷并没有爆炸。
「可是,我们有好好谈过分手吗?」
长濑凑了过来,表情突然从郁闷转为开朗,挂着调皮笑容的她身上的香味逐渐接近,让我的内心有点纷乱。
「记忆中我们并没有没谈分手。」
「你讲话还是一样拐弯抹角耶。」
「……你现在这样讲也无济于事。」
长濑说了句「我知道」,缩回身体,接着因寒风而发抖。
「我想回室内啦。」
「走吧。」
为什么非得待在这种寒风中呢?真是的,去会客室不就好了。
为了消除彼此心中相同的不满,我们逃离了顶楼。
说起来,顶楼——我和一名年轻女性待在顶楼啊——
「喔?你的脸色又变差了,你在玩红绿灯游戏喔?」
「还是小鸡时的记忆突然闪过我的脑海。」
「啥……透真是个难懂的男人。」
长濑在阶梯平台上说出这句不负责任的感想。
「又要谈分手的事?」
「才不要,我不是说我知道了吗?」
她嘴上虽这么说,但是口吻和嘴角都老实地透露出她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即使现在也好像随时会踢飞我的丁字杖解闷似地,焦躁的表情毫不掩饰地表现在脸上。
当平安走下楼梯时,我因安心而放松肩膀。
长濑从原本和我保持的微妙距离向前跨了一步。
「要回去了吗?」
「我也得去一树那里啊,毕竟现在有点不安。」
「不安?不安什么?」
「你不知道吗?和一树同病房的人失踪了。」
……啊啊,就是昨天护士说的那个行踪不明的人吗?
「那家伙虽然早就习惯住院,却还是会怕,到现在晚上还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呢。」
「人至少都有一件害怕的事呀,像我就很怕欠钱。」
「没有梦想的恐怖吗……」
这时长濑终于对我露出酷似往昔的笑容。
我和长濑之间凝重的空气终于缓和了一些。
长濑用郑重其事的姿势面对我。
「如果你那么不喜欢,我就不会再来了啦。反正我主要是来看一树。」
「……并没有非常不喜欢。」
「那我说不定会再来。」
她露出天真烂漫的微笑,其实根本不想让我拒绝吧?
「帮我和小麻打声招呼。」
长濑说完,便三步并两步地走下楼梯。
我目送她离开时才惊觉。
小麻?
「……她从哪听来的?」
那句话到底有什么意思?
回到病房,看到麻由睡眼惺忪地望着窗外,隔壁病床的度会先生说身体不适,却不接受检查只盖着棉被睡觉,这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入院的呢?
「啊……你上哪去了?」
大概因为才刚起床,说起话有些精神不济,我在椅子而不是在床上坐下,编造了一个「去厕所」这种可能马上会露出马脚的谎言,不过却没看到麻由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口中喃喃念着听不懂的话语。
「小麻差不多能出院了吧?」
我触摸麻由的绷带及发丝,她总是抱怨着一定要洗头,所以每晚都会擅自拆下绷带,洗完头以后再由我帮她重新把绷带绑回去。老实说,她的头发就算是拍马屁也没有美到能被当作世界遗产般美丽。
「阿道好之前不能出院。」「别逞强啊。」「在那之前不出院。」
她鼓起腮帮子,毫不掩饰地闹起别扭,接着还把棉被拉到头顶盖住全身,像个小孩子一样拒绝继续说下去。
「小麻,这是我的床耶。」
就算摇晃麻由的肩膀,她也毫不理会。
我开玩笑地将手伸进棉被搔她的脚底,麻由对这动作十分敏感,不断跺脚呻吟。我的渔业魂被她的新鲜度和活力感化,把其他的远大志向全都燃烧殆尽,不过我很难联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个志向而从事远洋渔业,所以并不觉得这有帮到什么大忙。现在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判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
我继续搔痒,同时想着长濑。
和她之间的回忆并不全是痛苦的。
几天后,麻由头上的绷带由医生拆下。
然后又裹上多了一倍的绷带。
麻由住的病房是单人房,备有专用浴室,连电磁炉都是病房附属设备之一。住房费用和住院费分开计算,一晚的费用是日币一万五千圆左右,我认为是十分不合理的价格。之所以设定这个价格,是为了让人们感慨原来世上真的有这种有钱人,不过没想到那种价格的房间竟然真的有人会使用,让我不禁为世界的深奥难解感到讶异和惊叹。
我就在那间一辈子也不可能住进去的病房里独自发呆。
病房内被暖色系的色彩环绕,和以浅白色为基调的医院宛如礼拜一和礼拜五般天差地远。暖气的运作声撼动耳膜,勾起人的睡意。
我在床尾坐下,伸长双脚打发无聊时间,而住在这间病房的患者麻由,被警察以被害者的身分半强迫地接受警方的询问,我就像只忠犬焦急地等待她的归来。骗你的。
「……………………………………」
今天早上,麻由的头部再次遇上花瓶,她竟然大白天的在这间寝室里因伤满身是血,不过这次依旧没有昏厥,自己步行寻找医生接受治疗。
不过有一点和上次不同。
这次的伤是他人造成的,为我说明情况的医生是这么说的。
我还没碰到头上多了一道新伤的麻由。
而我就像只讨食物吃的忠狗般等待她的归来。
我用丁字杖敲打地板,撞击声并没有大到能在病房内回响。
第一道伤是她用自己的手,拿没有花的花瓶砸伤自己头部所造成。
不过这次却是别人的手,拿着插有盛开龙爪花的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