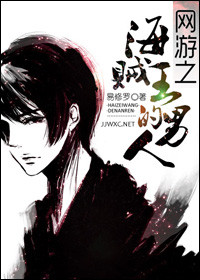说谎的男孩与坏掉的女孩-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是喜欢漂亮的大姊姊啦,不过要说是喜欢熟女就有点……」
「好想赶快变老喔——」
医生要是听到,大概会在丑时三刻于神社后徘徊,说出内心深藏的愿望吧!
「我为什么会跟阿道同年呢——为什么会这么年轻呢——为什么是麻由呢——我为什么是我呢——?我是……我嗯嗯,嗯嗯——?」
吟唱童谣般地重复着哲学性的问题,麻由突然蹙起眉头。眼睛往左移动,就像是要窥伺自我内面般恍惚了眼神。那是危险的,眯得细细的眼神,但似乎又和因为问题过于困难而发生运算错误的状况不同。把脸整个埋进枕头,除了脸颊靠过来之外,感受到一点过去和她无缘的理性。
「唔——……噫——啊——!」
非常认真地由嘴里发出怪异的声音。敲一敲会不会修好呢?不过万一被咬怎么办?
把身体拉开了一点,继续观察为怪电波所苦的麻由。
麻由持续散发了大约五分钟充满苦恼的怪声,然后终于像是除灵成功般一动也不动,整个脸埋在枕头里。刚刚那个是不为一般人所知的仪式吗?
咕噜噜地转了一圈,麻由转过来注视我。
「阿道。」
「什么事?」
「我啊,很讨厌我自己。」
没有抑扬顿挫的语调。就像和教室里的麻由调和了一般,不知为何有种粗糙的感觉。
「……怎么了,突然这样说。」
麻由做了个没有表情也没有表达意思的脸。
「我也不知道,就突然这么想。」
「……哦,我可是很喜欢呢。」
自己,还是麻由。到底是指哪一边?还是另一个谎言?
真正的想法根本无所谓,只要能够模糊焦点就好。
「为什么我会讨厌我,阿道知道原因吗?」
没有效果。麻由的目光摇曳,寻求着解答。
「不知道耶?我并不讨厌小麻啊!」
撒了个大谎。麻由喔了一声,把头往反方向转去。
发丝流泄,薄薄地盖在肌肤外露的肩膀上。麻由的肩膀和手不同,没有一点伤痕。就像盐湖般散发着炫目而冷清——一片的白。脆弱到如果用指腹去触压,说不定就会因此破裂。
抱紧麻由。即使算不上大个头的我,也能轻易地将她纳在怀中。
「喂」,她唤了一声,转过来面对我,甜甜地冲着我一笑。
「你在做什么——?啾——?」
啊,回复了。正好。
「小麻喜欢我吗?」
麻由想睡似地,以暧昧的笑容点头。
「最喜欢阿道了喔!」
「这样啊,嗯,是吗——」
可恶,感动到眼睛都快飙出卤汁(代理泪水)来了。
「阿道呢?」
在我胸前缩成一球,麻由反问。
想都不用想。「隔壁班的小口同学好可爱。」有必要说这种欺负人的话吗,脊髓!
「喜欢啊!」
「咦——不是最喜欢啊?」
「喜欢到要死的程度喔!」
「啊——我也是——」
放松地笑了。真要说的话是喜欢麻由,喜欢到想杀了她的地步才对。
「阿道道。」
不清楚到底算升格还是降级,总之被叫了个很屈辱的名字。不服输地加以对抗。
「什么事,小麻麻。」
说完之后的羞耻心狠狠地刺伤了自己,内伤到需要准备遗书的地步。
麻由磨蹭着我。是想跟我同化吗?身躯贴得死紧,喷在锁骨上的气息搔得人痒痒的。
从肌肤上的触觉,察觉麻由张开了双唇。
「笑一个。」
「……嗯——」
虽然理解关于这件事的重大程度,也经过深思熟虑的检讨,因此现在意识里对案情有两种不同解释。即使知道必须早日得出结论但也无法立刻决定,日本人连「不」也说不出口的民族气质正在作祟——「幸福的话,就笑一个。」
「……什……」
喉咙、脑浆和胸口彷佛同时被人捏紧。
御园麻由,对我询问了幸福。
就像那个人带来的连锁一般。
这必定是命运等级的恶作剧。
眼球像是要变成碎片一般被向后拉扯,因焦躁而烧炙着。
窗外的景色混入在医院看到的情景,像晕开的水彩画一般形成异质性的世界。
「我啊——只要这样就觉得很舒服,有阿道的味道,好幸福——」
语尾拖长,眼睛眨呀眨地,呵欠的时候眼泪顺着流下。麻由的意识已与梦境融合在一起,失去了明显的分界线。
「唔——好想睡喔……」
我在和她一起度过的时间里,到底记住了什么?
「那就睡吧!小麻果然还是睡着的时候最像小麻。」
心已经成为尼特族的我,无法将被给予的,类似感情的东西分类吐露出来。
「但是——小麻已经不是小孩了,所以要晚睡……」
「会说这种话的人才是小孩子喔!」
把心整个埋住的感情垃圾山,喜怒哀乐,到底哪一种比较突出呢?
「唔——又把我当小孩……」
有除了我之外的谁能够分辨吗?
「好了,出发去梦的世界旅行吧!」
……我能。现在的我一定能分辨。
先把解答的这道手续留待日后。
反正漫长的牢狱时间就在不久的将来等着我。
「笑一下嘛——」
「……啊啊,嗯。」
由于不是在镜子前面,对成果没有把握。
麻由没有睁开眼睛,就那样消失了意识。
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理所当然的睡脸。
我把这个状况视为当然,视为日常来看待。
「……那么……」
对她使用安眠药的机会,可能就只有这一次。偷偷让她吃下药这件事,比其他任何行为都还要刺激。感想是、就算有人因此迷上下药这件事也无可厚非。内心暗自推测,过去设计毒杀他人的犯人,心中应该也是像上瘾般无法自拔吧!
把麻由用床单裹了一圈完成白色的春卷之后,我下了床。
没有立刻移动,而是看了一会儿她的睡脸。
静静地凝视,企图就这样烙印在海马体里。
为了成为永久的回忆。
「……抱歉对你说了谎。」
最诚心地向她告解。
离开寝室,关上门。
通过微暗的起居室,如同早上预告的一般前往和室解除脚镣。
和两人身体脏污的程度成反比,无比清洁的双眼睁得老大,眼睑退到最底线,对我的行为投以疑问的眼神。放两人自由之后,站起身独白似地这么回答:
「要让你们回家了。」
然后,让一切都结束。
首先,虽然没什么意义,不过还是让他们先把身上的脏污洗净。
「来,浴巾。你们的衣服正在洗,洗完澡后先穿这件衬衫等一下吧,拿着。」
迅速递给浩太他们衣服和浴巾。两人似乎还不能理解我的行动,歪了歪头问道:
「那个,大哥哥。我们,那个……」
「怎么,该不会是不好意思吧?兄妹从六岁一直到十二岁为止,可都是被允许一起洗澡喔,挺起胸膛啦!」
接二连三用快言快语打断他,将两人送往浴室。在犹豫着不动的两人背后推了一把,让他们进入澡间——「请在一小时以内洗完喔!」说完便关上门。
「等一下,你听人把话说完啊!」
「我拒——绝——去给我把头冷静一下。」
「这可是热水澡啊——!」
明明不是说搞笑相声的场合。
把两人关进浴室之后,我坐在连接玄关和起居室的小走廊。
没有点灯,就只是蹲坐在黑暗里,被黑色的空间吸入。仅仅如此,高昂的心便获得平静。所谓抽烟的感觉,大概就是像这样吧!
眼睑重复几次不规则的开阖,享受内侧的黑暗与周围的黑暗之间的微小差异。比起外侧,内侧的黑暗要显得更浓。或许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总觉得相当适合拿来作为自我表现。
眼睛终于习惯了黑暗,两种黑暗的性质差异加深。因为觉得变得无趣,我闭上双眼,就像吐出嚼到无味的口香糖一般,将外界自眼睑里逐出。
为了补足被遮蔽的视觉,不论内、外的触觉都变得更敏锐。
地板的冰冷。空气的单调。喉咙里的烧灼。
「……………………」
回想机能自动开启。
出生在极其平凡的家庭。因为家里是乡下大地主,所以房子的坪数大到可说是浪费。总是得醉醺醺的老爸即使常带一起喝酒的老头回家住,房间也多到用不完,二层楼甚至还有B1的建筑物,一家五口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哥哥大我两岁,从小就染金发。和抢眼外表相反的是,他是个成天埋首书堆的书虫,甚至睡在藏书的书房,在餐桌上的话题也永远离不开书。妹妹则小我四岁,和我们不同母亲。因为患有严重癫痫,总是被家里当作隐形人。通常只有我会去照顾她,不过却总是被回以暴力,从来不曾对我笑过。母亲有两人。最初的母亲生下我三年后便过世,原因已经不记得了。只隐约记得她总是背对着我横躺着的身影,再加上手和脚的关节很不自然。而在那两年后有个大肚子的女性住进我们家。没有举行典礼只成立婚姻关系的女性,在三个月后产下妹妹。哥哥不曾对妹妹及妹妹的母亲讲过一句话,在家里愈来愈孤立。然后就在暑假前的结业典礼,从体育馆屋顶往下跳自杀了。丧礼只有我和父亲参加。妹妹和妹妹的母亲也开始写意地在家里生活。哥哥死时正好五岁的妹妹当时每天都在外面玩,带了一身泥土与擦伤回家。妹妹当时很热衷于杀死山里的动物,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这样再也没回来,只有我和妹妹的母亲偷偷为她办了超渡。然后家里只剩下我、父亲,以及妹妹的母亲。
八年后,只剩下我。
「骗你的。」
一如往常的谎言。本文纯属虚构,很明显的与任何现实无关,请不要当真。
「……骗你的。」
为了纠正谎言而说谎,实在不怎么愉快。
不过,我也有无法说谎的事。
即使本人再怎么改窜、想要奉捏造出的事实为尊——
以当事者的立场来看也不过是一大谎言。
例如,她与我。
「我啊,很讨厌我自己。」
浑身不舒服地模仿了那个语调。真的,很恶心。
「我想也是吧,御园麻由。」
毕竟你最讨厌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本身。
御园麻由是杀人者。
过去发生的绑架事件,就是麻由把犯人及其他关系者以杀人事件解决的。
一开始是,麻由自己的双亲。
绑架犯老爸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呢?不,应该说,从他踏上绑架小孩这条路,除了他本人以外就没人能理解缘由了。唯有一件事,是我看到那样的犯人之后理解到的。
人类全心全意享受某件事时展现的笑容,实在只有一个词能形容——丑陋。
为期将近一年的监禁,以伤害人为前提的各种游戏都试过一遍。或许是腻了吧,讽刺的是绑架案的犯人与麻由的双亲颇有交情。为了将感情濒临坏死的麻由玩个透彻,犯人或许认为这是个相当适合的刺激。
于是邀请了麻由善良的双亲,将两人束缚,然后强迫麻由杀害自己的双亲。他威胁如果不照做,就要杀死我和麻由。麻由展现许久未见的高昂情感哭着抗拒,而她的表现也如预期地煽动了犯人的兴奋感。但是才十秒就感到烦闷,踢飞麻由肿胀的脸,用自己准备的切肉菜刀在麻由的大腿划下一道红线。比起麻由,她双亲发出的悲鸣声更响彻了我的耳膜。
复活的情感回想起痛楚的感觉,麻由只能遵循犯人的指示以求保身。绑架犯的妻子基于良心遮住了我的眼睛,悄声说:「不要看。」但是她遮蔽得不完全,从指缝中隐约看得到面前发生的光景。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