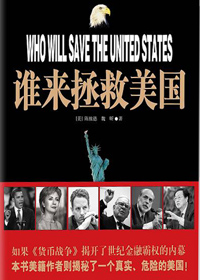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5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智根本无法理解有一个上帝存在这回事。这样一来,问题就不是何为真实的上帝,而是人的理智与上帝不兼容。就虚无主义的最终理由而言,后一个问题才是真的。正因为人的理智不能容忍有一个上帝存在,任何想要区分真假上帝形象的努力才毫无意义。伊凡已经明确声称,只有三度空间的思维头脑无法理解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把这一理由看得太轻,人们随之一同关注没有上帝的后果,忘了询问“如果上帝不存在”的理由。如今,我们必须询问,“如果没有上帝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没有荒诞反而不能生存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上帝死了……”这一前提的前提是什么。我们马上就着手来处理这一问题。
在康德哲学中,人的理性被确立为经验知识的唯一合法权威,逾越了它,经验认识就会步入幻象。一方面,人的理性的僭越运用不合法,另一方面,人类生活世界的一切可能的经验真理又都得自于主体的理性认识;主体的理知虽然有限制,但这恰恰是经验真理可能的条件,是作为有限存在的主体的认识前提。这样,康德就赋予了有限的人的主体心智一种近似造物主的能力,经验理性成了个体自主性的开始、依赖性的结束,个体存在弃绝上帝的开始,与超自然的关联的结束。人的生存一旦进入理性主体的位置一切都依赖于他的理性自决,原初的、无论希腊人还是犹太人的精神根基便丧失了,一切都聚集在主体性这个中心点:认知的主体、实践的主体、历史的主体。
康德并不是确立理性主体性的优先地位的第一人,只需提到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就够了。但当我们考虑到,现代虚无主义拒斥上帝,乃是由这主体的理知造成的,就应该认识到,康德在理性主体的上升中的决定性作用。加缪明确表示,荒诞信念的根据,首先在于人的理性与荒诞的存在事实的冲突,同时,理性又不相信理性之外还有别的。用理性之外的精神力量来超越荒诞的事实,不过是逃避荒诞的跳跃:“对一种荒诞的精神来说,理性是徒劳的,而在理性之外则一无所有”(《西西弗斯神话》。页337)。理性无法理解存在事实的非理性(荒诞),而人唯一所有的,又只有理性,于是,理性告诫人们必须承认、并接受存在事实的荒诞。在这里,对理性的颂扬显然与康德乃至之前的唯理主义者的口气不同,在荒诞人的悲观理性中有明显的乐观情绪,在唯理主义者的乐观理性中,却有深隐的悲观。这种倩绪的转换,隐藏在康德充满矛盾的哲学之中。
由于经验理性的确立,人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主体性的建立),以至于要僭取上帝的地位。荒诞人的信念看起来悲观之极,其实充满了一种人性自豪感,这种感觉与经验理性的优先地位的确立似乎有一种逻辑的内在联系。康德之前的唯理思想家在推进经验理性时,有一种惶惶忧心,最终都要给上帝安排一个毫无疑问的位置(笛卡尔的终极实体、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康德之后,现代虚无主义用经验理性取消上帝时,在废墟之中有一种毅然的决心,果敢承担康德从经验理性的优先地位引导出来的后果。当康德把上帝的存在推拒到经验理性之外的世界,阻断了唯理思想家设定的人的理智与上帝的智慧的关联,荒诞就成了人之为人的首要条件。因此,特别从康德以来,理性的人愈来愈感到需要为自己的欠缺辩护。
在笛卡尔看来,人的理性作为被造的理智有其局限性,但这种局限反而是人的一种优越,通过这被造的理性,天赋观念给予有限的个体以绝对力量,即便我怀疑,也恰恰证明了被造的理智的确实性。理智的本性实际上被看作是没有限制的,它表象着上帝的观念,有限制的只是那种对于一个天使或一个人的灵魂的观念。这样,笛卡尔借助天赋观念及其理性的作用,就让人在上帝的智慧中忘记了人的理性的局限性真正是一种局限。人的理智当然不能与上帝的智慧相比,但这不可比拟性,正好可以用来勾销人的局限性;然而,人的理智的局限性是在上帝的智慧中消失的。倘若有一天,人的理智不要上帝,这被勾销了局限性的人的理智便成了一个确实可靠的立脚点。因此,站在笛卡尔的这一立脚点上,人虽然现在还不能拒斥上帝,总有一天可以拒斥上帝;在理智面前,上帝与人近于平等。借助上帝赐于的理智,人可以造上帝的理智的反。
人现在已不再被规定为ens creatum(被创造物)或上帝之子,而是被规定为主体。笛卡尔的有限性没有就无限实体的观点而言的本体论意义,这恰恰使他能采取一种就人和就这种主要的“反叛”观点而言的意义。从笛卡尔到尼采以及在上帝之死中,这种“反叛”构成了“存在”的新面貌,这就是“主体性”的面貌。①
①皮罗:《海德格尔和关于有限性的思想》,见《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1962年第2-3期,第30页。
在斯宾诺莎那里,作为理智的实体以重新聚合为上帝的实体为前提,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这种主体性。主体性的精神实体在成为上帝存在的样态时,已经取得了与上帝相同的位置。主体性的理智与上帝的理智的内在关联使人在自身之内与上帝、“产生自然的自然”同格,有形的实体(有限存在)就是无限的实体,主观性的理智无需求助于自身之外的东西便禀有一种内在的自由。随之,莱布尼茨为了满足最终不可分的点的要求,让实体分裂为无限的个别单子。这形而上学的点依据其主观的理智而拥有了绝对的自在性,它没有窗户,拒斥任何不是出于理智的内在原则的东西。这样,有限的个体性作为单子便成为不可取消、不可置换的存在,在其内部,潜伏着自身运功的根源——力的动力学趋向,这趋向的目的乃是通过自身的力量,使从知觉发展而来的理智与上帝的最高理智相同。在笛卡尔那里出现的比理智更大、更像上帝的意志,现在反过来为理智更像上帝效劳。理智才是人最高贵的东西,即便它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上帝即是最高的理智。这不是在说,人的有限局限的理性冲动就是要成为上帝的理智,又是什么呢?人同然除了上帝之外,谁也不依赖,但上帝也要遵从逻辑定律,上帝的创造也不能随心所欲,照样不能违反逻辑必然性,上帝不受逻辑强制只是说他能做从逻辑上讲可能的任何事情。人天生具有理智的力量,也就可能与上帝等同了,上帝与人都服从一个永恒的必然真理——理性的确实性。
个体主体性成为不可置换、不可勾销的自为存在,就是靠这理性的确实性,它可以据此宣称不要上帝,因为上帝也不过是一个理智的全能存在。人在理性之外一无所有,就可以被说成人的理性无所不能。当康德把上帝推拒到实践的领域,复又使之依赖于实践理性的公设,主体性的理智就有机会开始指控上帝。康德不就根据纯粹理性的权能摧毁了种种传统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么?既然在实践领域里价值行为也得依赖理性公设,上帝的设定又有什么必要?一方面认定在理智之外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又迫于康德的批判承认理性的限制,人就得准备背负理性的欠缺。一旦把理性的欠缺担起来,欠缺就成为自足。当人从实践理性的公设出发,依然找不到上帝,当人发现,人的价值行为依然得凭据理性的普遍法则,上帝的存在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应该被判为虚妄。
主观性的理科作为形而上学的点,成了真实的终极实体,人要超逾它是不可能的。现代虚无主义并不打算推翻这一形而上学的点。而是要借助这个终极实体来找到另外的东西,这另外的东西据说被唯理思想家隐藏在主观性的理智下面:
萨特力图借助现象学方法来找到这主观性的理智下面的东西;如果理智的发展是由一种欲望或感知的力推动知觉成为理智的,那么,欲望或感知的力,是不是潜隐在主观性的理智下面的东西呢?
据萨特说,要逾越人的主观性理智不可能,笛卡尔的Cogito(我思)依然是一切真理的出发点、唯一绝对真实的自我意识,离开这个绝对不可再分解的终极实存,人不可能达到真理。只是,“我思”还不那么明晰,还有另外的东西附着在它下面,这就是作为非实体的无化意识或者说前反省的意识。无化的意识先于思的自我,意识不过是意识到思的自我;必须先有意识,才会有意识的形式化自我,因而,我思不过是我的意识的实存。
这前反省的思被萨特表述得十分晦涩。不过,据萨特说,我们可以感觉、体验到它。说到底,前反省的思乃是一种实存的情绪,无法描述的本然性之生欲。它没有什么规定性,不过是实存的偶在所采取的偶在形式。
不是一个实体,不等于不是一个不可再分的实在。如果莱布尼茨成功地勾销了笛卡尔实体的广延性,在一种既是精神(因此不可再分)、又是实在的意义上,重新规定形而上学的根本实在,萨特又为何不能勾销传统的我思实体性,在一种既是情绪(当然也就不可再分解)、又是实在的意义上,重新来规定形而上学的根本实在?实存的情绪或本然性欲求乃是本体论的绝对,它早就且总是在那里。这非实体的绝对、实存的情绪,正是我思意识的支撑点——主体性。实存的情绪不得不成为我思的意识,而我思作为一种意向性不过要把那非实体的绝对(实存的情绪)带出来。我思不能完全反省自己的存在,只能在前反省的实存情绪中将自己作为一种活动着的关联显示出来,没有这意向性的活动,前反省的意识就会归于浑沌,这样,前反省的意识、实存的情绪就自发地、本己地成为主体性本身的意识,成为意识的能动特性和无化本性。由此,萨特得到了两个富有成效的结果:我思不可勾销,它是形而上学的根本实在(非实体的绝对或实存的情绪)的本己显现,另一方面,我思可谓落叶归根,有了自己实存的基础,无需再像传统唯理思想家那样,总要安排一个全知的上帝作为我思的最终依靠。我思的形而上学基础不在上帝,而在实存的情绪,在同样是形而上的欲望感觉。通过这种现象学还原,我思就不再是在上帝那里,而是在作为主体性的生存情绪中找到了自己的形而上学根据。
现代虚无主义对传统唯理论的批判,绝非要勾销我思,削弱理性本己的力量,而是要勾销我思的超验根据(笛卡尔的绝对实体,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使之有一个生存性的、同时又不失形而上学位置的牢固基础。把我思的基础置换为个体实存的情绪,我思的力量得到了超常的加强。这置换得力于康德,只有在康德哲学之后,这种置换才可能。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中所蕴含的意志力、欲求感已经拥有了合法力量,使得后来的思想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功夫来谈论这意志力和欲求感的地位,重新为有局限性的理性找到一个形而上学的点:费希特把意志置于实在的领域,随之。谢林堂堂正正把意志当作所有存在判断的最终基础,在叔本华那里,意志已有萨特所谓盲目的甚至邪恶的性质,以至于尼采可以说,一切价值判断都以生命意志力为根据,理性以生命力、意志力或者说实存的情绪为根据,理性的地位不是